- +1
“你要走得遠遠的”,然后呢?|翻翻書·書評

在完成小說《鳳凰籽》書稿那一日,青年作家東來說,自己仿佛卸下了背負多年的行囊。
這部長篇小說是“遷徙一代”年輕人的自我書寫,具有私密卻普遍的心語意義。故事中,一次偶然的“互換人生”機遇,小鎮(zhèn)少年通過一檔綜藝節(jié)目,與在城市生活的同齡人相遇,自此,他們的生活有了交集。可是,難以逾越的壁壘,從未設(shè)想過的彷徨,都隨著這段不可復(fù)制的城市生活,在少年的心頭升起。他似乎從小鎮(zhèn)那穩(wěn)固庸常的日常中抬起了頭,看見一種陌生的可能,但他卻無法真的將之抓住,對未來的茫然,也在節(jié)目結(jié)束后籠罩在少年心間。
熟悉的故鄉(xiāng),還是流動的都市?這是當代青年的遷徙困局,而每個人的答案,都蕩漾著私人記憶的痕跡,也決定著自己的人生走向。我們注定帶著這道印記前行,在走入新生活的某個時刻,它也提醒我們,回頭看看自己的來處。
此前,我們發(fā)起了「從小鎮(zhèn)到都市:我們注定帶著裂痕生活,但這就是生命的厚度|翻翻書·送書」的征集活動,最后選出三位讀者寄送了這本書。如何安放我們的記憶?如何回望我們的來處?如何完成自己的敘事?關(guān)于這些追問,三位書評人給出了各自的看法。
以下是他們的書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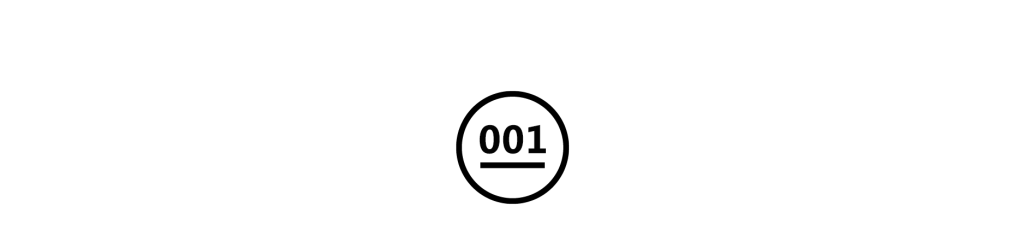
若將無處可退的凄苦轉(zhuǎn)過向來
文|拉普
這本書讓我錯覺自己已重拾學生時代的閱讀能力,在火車、飛機、高原和雨季的切割下,每次打開都能夠順暢地續(xù)讀,并在某個深夜直抵尾聲。我想這種順暢感并非來自共鳴,而是由語言的能力造就,字順文從——流暢、清脆,玻璃一般通透,似要碎掉,實則堅不可摧——是我的第一印象。
在第一人稱的視角下,這段被《變形計》式的短暫交換攪動的人生竟讓我想到了雷普利,一個被動的、消極的、早慧但溫情的、內(nèi)斂而面目不清的“中式雷普利”。跟著他涉過人生之河,不會有刺激腎上腺素的驚險橋段,多的是叫人喉頭發(fā)緊的所謂“人性世情”,被凝練起來的人物立在河道之中,緊盯著你,又看不見你,張張嘴,風吹過的話里皆是腐朽的新鮮,教人成長又打得人措手不及,從被遺忘之處、從邊緣之外向上、向心的攀爬之路,只有方向,沒有目的,數(shù)十上百年來或許都是如此。我想或許只有國勝接近了掌控命運。
高度概括的人物也帶來了一些臉譜化的弊端,大部分角色的復(fù)雜性被簡化,人物的對話之中也似乎能讀出同一個底層聲部,我并不介意作者的聲音出現(xiàn),或許處理上還可以更自然些。

而故事本身的流動,與情、景的流轉(zhuǎn)一道,在精妙的文字之中迂回向前,也正如一條蜿蜒河流,有急有緩,有窄有寬,濃郁的不至于郁結(jié),稀薄的不至于窒息,行至尾聲,咚——地,山霧里,似夢似真之處,草籽長出一棵來,無根之河終以自己為原點。
我想這又暗合了周作人寫“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xiāng)”。我常想,無處可退的凄苦若是轉(zhuǎn)過向來,也可以是處處可去。我們的來處是我們的記憶,我們的記憶卻也是時時刻刻在生長,斬不斷的就不斬它,我們胚胎時的形狀,吃的第一口飯,走的第一步路,說的第一句土語,看過的第一回四季,不復(fù)存在的燕子窠也永遠在那霧中,如同在人夢中。
讀畢,依然更喜歡《涉過岐流》這個名字,我注意到英文書名是A Fork in the River,也很喜歡。在河流分岔之處,是岐流鎮(zhèn),也是苦行人,是綿延的進行時,是過去又未過去的,是將來又未來的,是時代的眾聲里有時會被當作噪音的,流徙之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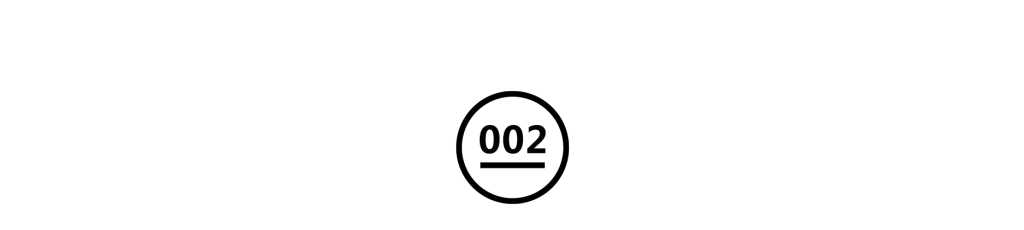
“你要有點骨氣,走得遠遠的”
文|假我
《鳳凰籽》中的故事相較于像我一樣的“遷徙者”的人生軌跡來說,可謂極具傳奇色彩。在生命的前二十年里,我既沒有經(jīng)歷大風大浪,也不曾成為“天選之子”,絕大多數(shù)時間,像嚴格遵循節(jié)律的動物,上課、考試、遠走他鄉(xiāng),在十八歲那年得到沉甸甸的自由。東來筆下的少年是特別的一個,但也是典型的一個。
從我的燕子窠來到北京,我見識到了城市包容的一面。現(xiàn)代化都市是真正的原始森林,當陽光灑下來的時候,每一棵樹只需自在地、自足地、自立地汲取。只是草籽生長出的根系上,一定帶著家鄉(xiāng)的黃土。更何況,比起能夠扎根的草籽,我更覺得自己是一頭被放歸山林的家畜,不敢忘情撒歡,總是一邊小心翼翼地試探前路,一邊不斷磕磕絆絆地登上山頂,回望來處的炊煙。

“我唯一的疑惑是,我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割舍什么,留存什么,對自己要成為怎樣的人依然意識模糊。”從前,我是賽道上的運動員,聽見發(fā)令槍響就跑,跑到終點,闖過那條白線。可是,闖過去之后,卻發(fā)現(xiàn)世界上根本沒有白線,也沒有人為誰畫白線。我碰上了一個解構(gòu)的時代,一個毀滅與新生持續(xù)發(fā)生的時代,這在大城市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
一些事物的分崩離析令人狂歡,可當我看著一些完整的軀殼被擊成碎片時,痛快之余,總有些感傷。標簽一個個剝落,我心頭會浮起荒謬的想法——多想撿幾個,貼在自己身上:我想成為“城里人”,我想成為“鄉(xiāng)下人”,我想成為“工人”,我想成為“知識分子”,我想成為“農(nóng)民”,想成為一個身份穩(wěn)固的人。我知道,這是逆時代車轍而行,也并不符合我所向往的自由精神。可是不確定性如影隨形,讓人不安,書中的少年說,“安迪是怎么一開始就確定自己要扮演的角色,對我而言,這始終是一個謎團”,我的心聲也是如此。
嚴格來說,我不是家里的第一位“遷徙者”。一九四二年大旱災(zāi),爺爺?shù)母赣H帶著一家人一路乞討到了山西,給人種地謀生。熬過最艱難的歲月,他們就立刻啟程,不遠萬里回到了魯中的小村落,他們從沒覺得可以在別處扎根。后來爺爺進城當工人,實現(xiàn)了階級的“跨越”,可家族中最親近的老人卻接連離開,讓年輕的爺爺不得不擔起頂梁柱的責任,帶著遺憾再次回村。提起當年事,爺爺仍然唏噓感嘆,他曾眼含淚水看著我,說出了我以為不可能從這個三年級文化的老頭口中聽到的話:“你要有點骨氣,有點志氣,走得遠遠的。”我想這話他同時也說給自己。如今我真的走遠了,卻發(fā)現(xiàn),單憑“骨氣”與“志氣”根本無法自處。
也許等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我能夠想起《鳳凰籽》中月龍的話,帶著別樣的心態(tài)回到“原點”,找到自己那時的坐標;最終“原點”消失,我這只家畜會變成一只無腳鳥,“向前,向前,無路可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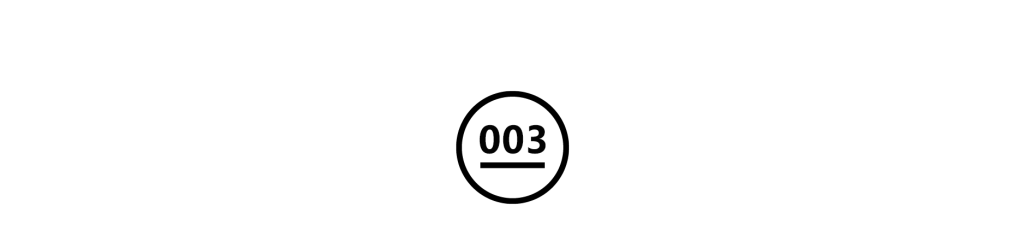
在歧流中尋找平湖闊海
文|大壩誰修哈
《鳳凰籽》以一場“城鄉(xiāng)互換”的真人秀為切口,撕開了當代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隱秘的精神創(chuàng)傷。主人公無名無姓的設(shè)定恰如一代“小鎮(zhèn)做題家”的集體縮影——他們像被連根拔起的植物,在都市的混凝土縫隙中艱難抽芽,卻始終帶著方言、記憶與身份的“錯位感”。東來通過咖啡師安迪、大學教授等群像,揭露了遷徙者的共同困境:模仿城市口音與消費符號的“自我改造”,實則是精神上的一場慢性自殺。這種撕裂感在書中被具象化為“兩個我”——逃離故鄉(xiāng)的“舊我”與回望來路的“新我”,作者對“優(yōu)績主義”陷阱叩問,就通過這兩者之間的對話來實現(xiàn)。
小說中真人秀節(jié)目的設(shè)定極具諷喻性,鄉(xiāng)村少年的困頓被剪輯成獵奇景觀,“逆襲”敘事也在這個節(jié)目中淪為流量密碼,我認為,東來這樣的處理,是對某種現(xiàn)實的借鑒,實際上,現(xiàn)代媒介已經(jīng)成為了階層固化的某種隱形共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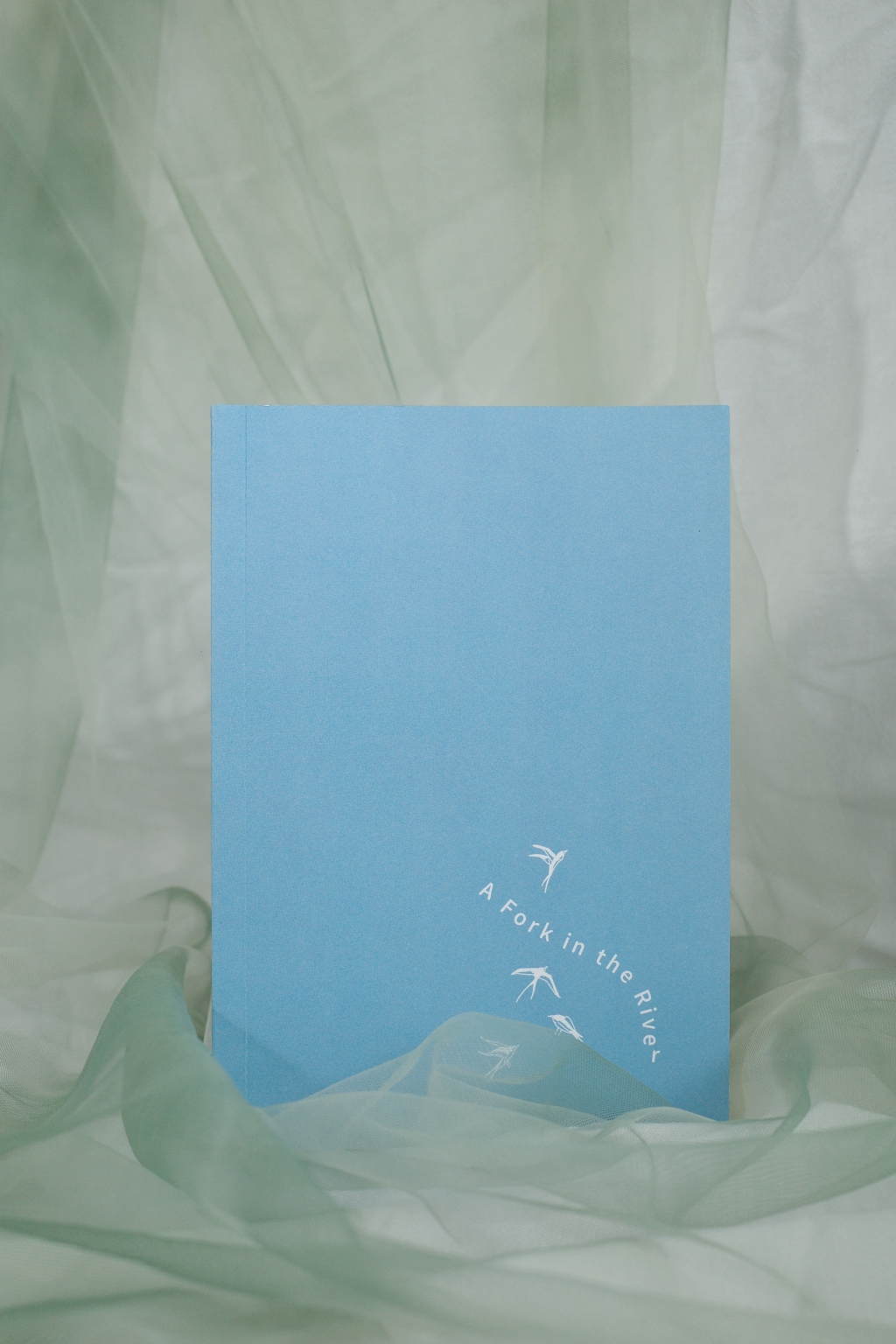
主人公養(yǎng)父母家掛著“水晶吊燈與土耳其掛毯”,但是,在他的故鄉(xiāng)小街上,只有被撤銷的鄉(xiāng)村中學。
東來的突破在于,她并不只是簡單地展示苦難。小說采用了狄更斯式“回溯”手法,主人公在三十歲時,重新回到故鄉(xiāng),與啟蒙老師月龍重逢。這一設(shè)計超越了《遠大前程》的成長敘事,呈現(xiàn)出一種可能的反思,唯有直面“被丟棄的來處”,才能修復(fù)流浪的年輕人割裂的身份認同。書中月龍與大學室友那段關(guān)于“外交官夢想”的對話,讓人感覺尤為震撼,精英階層的薛輕蔑質(zhì)疑“家教是浪費能力”,東來借月龍之口戳破了她的傲慢——“你以為這一切只靠自己的能力?”。這種憤怒并非仇恨,更是一種對結(jié)構(gòu)性不公的清醒認知。
東來的寫作本身即是一場精神考古。她打撈起“固守家園的農(nóng)民”“改名換姓的咖啡師”等微末個體,讓被時代碾過的足跡重獲尊嚴。正如她坦言,這部小說藏著“對逃離者的嫉妒、對留守者的愧疚、對都市精致主義的疏離”。這種復(fù)雜性使《鳳凰籽》超越了簡單的城鄉(xiāng)二元對立,成為奈保爾式“移民文學”的中國注腳——無論是《大河灣》中的非洲漂泊者,還是本書里的小鎮(zhèn)青年,都在證明:裂痕不是恥辱,而是生命的厚度。
《鳳凰籽》并不只是提供“逆襲的想象”那種廉價的安慰,她將遷徙視為一代人必須背負的宿命。
當主人公最終明白“我沒有原點可以回去”時,這種絕望反而成了自由的起點。唯有承認裂痕的存在,才能在流動中建構(gòu)真實的自我。東來的這種努力,封存了那些“未被看見的足跡”。幾乎每個年輕讀者都能在其中照見自己的影子,我們之中,有些人像是困在鏡像中的“桑丘”,或是掙扎著破繭的“鳳凰”,但我們終究都是在歧流中尋找平湖闊海的同路人。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gòu)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