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劉志偉:白銀與明朝國家的轉(zhuǎn)型
本文原題《白銀與明朝國家的轉(zhuǎn)型——在北京論壇(2017年)上的演講》,收入《貢賦體制與市場:明清社會經(jīng)濟(jì)史論稿》,劉志偉著,中華書局2019年版。
近年來,經(jīng)過許多學(xué)者的努力,人們對全球化的歷史對中國社會的近代轉(zhuǎn)型產(chǎn)生重大影響已經(jīng)有了很多認(rèn)識,時間上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紀(jì)。新大陸發(fā)現(xiàn)以后的世界體系的運轉(zhuǎn),對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恐怕是來自世界市場的白銀大量流進(jìn)中國。明代后期從各種渠道流進(jìn)中國的白銀數(shù)量,很多學(xué)者的估算出入很大,我想大約在一萬萬兩上下的規(guī)模。這樣大量的白銀流入中國,對中國社會帶來的影響,已經(jīng)有很多學(xué)者主要從市場經(jīng)濟(jì)的視角做了深入的討論。不過我認(rèn)為,16世紀(jì)這些白銀流入對中國社會轉(zhuǎn)型的影響,更深層的還不只是在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而是在國家體制和社會結(jié)構(gòu)上。
關(guān)于這個問題,我想先從很多學(xué)者都已經(jīng)提出過的兩個問題入手:第一,中國社會如此強(qiáng)的白銀吸納力是怎樣產(chǎn)生的?第二,這樣大量的白銀流入中國,為何沒有引起明顯的通貨膨脹?這兩點,在王國斌先生為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一書寫的序言中是這樣提出的:
(弗蘭克)關(guān)于世界經(jīng)濟(jì)聯(lián)系的基本觀點是十分簡單的。歐洲人渴望獲得中國的手工業(yè)品、加工后的農(nóng)產(chǎn)品、絲期、陶瓷和茶葉,但是沒有任何可以向中國出售的手工業(yè)品或農(nóng)產(chǎn)品。而中國在商業(yè)經(jīng)濟(jì)的擴(kuò)張中,似乎對白銀有一種無限渴求。16世紀(jì)和18世紀(jì)大量白銀流入中國照理會引起通貨膨脹,但實際上卻沒有出現(xiàn)這種情況。這就意味著,中國經(jīng)濟(jì)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銀,擴(kuò)大手工業(yè)者和農(nóng)民的就業(yè)和生產(chǎn)。

關(guān)于這個問題,我想首先要了解的是,王朝時期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在性質(zhì)上是一個“食貨體制”,這個體制是由“賦入貢棐,懋遷有無”構(gòu)成的,而其有效運行的關(guān)鍵在“事役均”。這個社會體制的基本原理對我們認(rèn)識中國王朝時期社會結(jié)構(gòu)至為關(guān)鍵,但在這里我們不能詳細(xì)討論,只能指出,這樣一個體制,內(nèi)在地以貨幣流通為貢賦經(jīng)濟(jì)和國家管治的運作手段。明朝立國時,以畫地為牢的里甲賦役制度和缺乏相應(yīng)金融制度的大明寶鈔為基礎(chǔ)建立起來的社會和行政體制,不到幾十年就破綻百出,隨之開始了一個以追求“事役均”為目標(biāo)的一系列制度變革過程。
這個轉(zhuǎn)變就是所謂的“一條鞭法”的發(fā)展。這里也許需要特別指出的,學(xué)界有一個大家以為是常識性的說法,說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其實是不對的。一條鞭法是一個從明宣德正統(tǒng)年間開始、自下而上的變革過程。一條鞭法的發(fā)展,代表了一種新的制度、新的國家、新的社會、新的經(jīng)濟(jì)體系形成的轉(zhuǎn)型過程。所謂國家或社會的轉(zhuǎn)型,具體而言,就是王朝國家怎樣去控制社會中的人,王朝統(tǒng)治格局如何影響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組織方式。
要在這十多分鐘內(nèi)講清楚白銀在明代國家與社會轉(zhuǎn)型中的角色是不太現(xiàn)實的,這里只能嘗試簡單概括地說明。
在剛才說的王朝汲取財富資源的非財政性方式下,明朝各級政府運作的資源,主要來自差役(人力和物力)征調(diào),而差役征調(diào)的體制是建立在一個以家戶為單位的承當(dāng)差役的社會組織系統(tǒng)(里甲)之上的,各級政府根據(jù)這個體系中各個家戶的人丁事產(chǎn)多寡(即是承當(dāng)能力的大小)征調(diào)和派辦人力和物質(zhì)。根據(jù)“事役均”的原則(朱元璋具體表述為“凡賦役必驗民之丁糧多寡,產(chǎn)業(yè)厚薄,以均其力”),大戶負(fù)擔(dān)重,小戶負(fù)擔(dān)輕,其輕重的差距不是按比例派,而是以類似累進(jìn)的方式,重者賠累或至傾家,輕者或悠游免役。這種體制造成的結(jié)果,第一是由于戶的規(guī)模盡可能減小,可以讓賦役負(fù)擔(dān)最小化,因此,作為差役供應(yīng)單位的戶的規(guī)模,總是趨向于以小家庭為單位立戶;第二是政府與編戶齊民的關(guān)系,通過戶籍體系直接控制家戶中的個人;第三是負(fù)擔(dān)的輕重,即不可預(yù)算,也難以做到均平合理;第四是各級政府及其官員的開支來源,是一種無定額的推派,總的趨勢是不斷增加。這些特點造成了第五,社會上大量的人口,脫離國家統(tǒng)治體系,以無籍之徒的社會身份存在;而這樣的狀況造成的后果是第六,明朝國家的統(tǒng)治模式和社會秩序發(fā)生動搖,而中央各衙門和各地的地方官員陸續(xù)采用各種變通的方法來獲得行政資源。
各級衙門采用的辦法有一個共同的趨勢,就是借助可以預(yù)算定額和可以按比例攤征的一般等價物作為計算和支付的手段,取代原來的無定額、無比例的索取,而這種手段最有效也最能夠被接受的就是白銀貨幣。這樣一來,明朝立國建立的體制下,國家政治與行政運行的資源,大部分都來自非財政性的機(jī)制,即差役征調(diào),到明代中期,這種資源汲取的機(jī)制,轉(zhuǎn)變?yōu)樵絹碓揭蕾囉冒足y貨幣作為核算和支付手段,來達(dá)到“事役均”的社會管治目標(biāo),結(jié)果是非財政性的差役轉(zhuǎn)變?yōu)樨泿呕⒍~化的比例賦稅化的財政性收入。由于原來通過差役獲取社會資源的規(guī)模相當(dāng)巨大,由差役轉(zhuǎn)化形成的財政性貨幣收入的規(guī)模也相當(dāng)可觀,隨著白銀貨幣作為計量和收支的手段,構(gòu)成明代國家?guī)觳氐闹饕问剑纬闪司薮蟮陌足y需求。我粗略估算,明代中后期由原來的各種征派改折形成的白銀財政規(guī)模大約為1500—2000萬兩左右,加上同時帶動起來的田賦折銀,白銀財政的規(guī)模估計達(dá)到3000萬兩的規(guī)模。如果我們估算當(dāng)時最大宗的商品運銷規(guī)模一般都在百萬兩級的規(guī)模,就可以知道這種財政性的貨幣流通,是非常巨大的。這種以貢賦體制主導(dǎo)的貨幣需求,以及由此帶動起來的商品交換與流通,是中國市場吸納大量白銀的秘密所在。
白銀成為賦役繳納手段后,改變了整個賦稅財政體系的運作機(jī)制。明中期開始越來越重要的白銀,更多不是作為流通手段在市場上發(fā)揮職能,而是作為支付手段,被用于處理權(quán)力和資源的再分配。白銀確實被廣泛應(yīng)用,但流通的結(jié)果是白銀大量流入權(quán)力運作的體系。在這種情況下,白銀流通就不必然伴隨著市場發(fā)育,甚至可能導(dǎo)致市場的萎縮。當(dāng)然,長期來看,白銀作為支付手段進(jìn)入政府資源運用領(lǐng)域,最終還是一定會拉動市場的擴(kuò)大。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白銀為運作手段的國家與依賴控制關(guān)系來運作的帝國是不一樣的,國家權(quán)力與老百姓的關(guān)系以及整體的社會結(jié)構(gòu)都發(fā)生了轉(zhuǎn)變。
所以,在我的理解上,白銀流通的意義就不是主要在市場和商業(yè)領(lǐng)域體現(xiàn)出來,而是體現(xiàn)在社會和國家結(jié)構(gòu)層面。此前帝國運轉(zhuǎn)的資源是以國家權(quán)力對具體人戶的控制為基礎(chǔ)的,但是這種控制又不是國家基層政權(quán)州縣對民眾個人的直接控制,而是通過里甲制實現(xiàn)的。納銀之后,老百姓與州縣的關(guān)系轉(zhuǎn)變成為類似納稅人和現(xiàn)代國家的關(guān)系,國家可以不控制具體實在的家戶,而通過控制一個納稅賬戶來實現(xiàn),這就提供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產(chǎn)生各種中介力量的空間,以及社會成員之間交往和組織的新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代替里甲制度,新的賦役攤派征發(fā)的組織和機(jī)制成為必要、成為可能,并有可能普遍化起來。
我們很難用簡單的國家控制加強(qiáng)或者削弱來描述這個變化,這是一個國家與社會以及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方式的結(jié)構(gòu)性轉(zhuǎn)型,王朝國家跟鄉(xiāng)村基層社會、跟一般的編戶齊民老百姓的關(guān)系發(fā)生了根本的改變。一個國家或一個王朝,它不可能不控制人,當(dāng)它控制不了的時候,白銀的運用使它實現(xiàn)控制的時候,可以靠社會上的中間這一層力量。正因為國家有了這個轉(zhuǎn)變,鄉(xiāng)村就可以自治,就可以有所謂的自治化。從這個角度來看,自治化不是國家的削弱,而是國家的轉(zhuǎn)型。如果沒有自治化,王朝國家就會失控。從明代中期到清初,我們似乎看到國家有些失控。但實際上,社會永遠(yuǎn)處在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中,在失控的同時,它總有一些辦法使得控制能夠再度建立。問題是,這個再建立的方式,不是政府再去抓里甲戶應(yīng)卯聽差,而是在鄉(xiāng)村中大量出現(xiàn)了各種中介的力量,宗族或士紳什么的,去控制地方的秩序,保證國家運作的資源獲取與調(diào)動,使得地方秩序可以按照國家所期待的那個樣子去運行。
這里面當(dāng)然會有無數(shù)沖突,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不過,如果我們從一個比較長的時段來看,例如五百年這樣的時段來看,其實是幾個不同的結(jié)構(gòu)一直在或者緩慢地或者激烈地發(fā)生變化,變出了一個新的結(jié)構(gòu),變出一個我們看到的,在清代至遲到雍正、乾隆以后成型的那樣一個社會。嘉道以后的動亂,是在這個結(jié)構(gòu)下面的動亂,它跟明代的動亂完全不一樣。明代的動亂是以逃戶的方式來表現(xiàn),它針對的是政府對個人、對編戶齊民的控制體制,一直到李自成都還是,李自成的口號就是“不納糧,不當(dāng)差”。但清代嘉道以后叛亂,則是一種政治上的敵對勢力,背后還有宗教等因素,不再見以抗拒“納糧當(dāng)差”為口號的了,這實際上是社會轉(zhuǎn)型的結(jié)果。因此,從明到清,無論是從國家形態(tài)、地方社會組織還是動亂,你都可以看出社會的轉(zhuǎn)型。
這樣一種格局,簡單地概括的話,可以在弗蘭克所說的“全球性市場的輪子是用白銀的世界性流動來潤滑的”這句話之后,再加多一句:“中華帝國的社會轉(zhuǎn)型和國家的新運轉(zhuǎn)機(jī)制,是用主要來自世界市場的白銀來驅(qū)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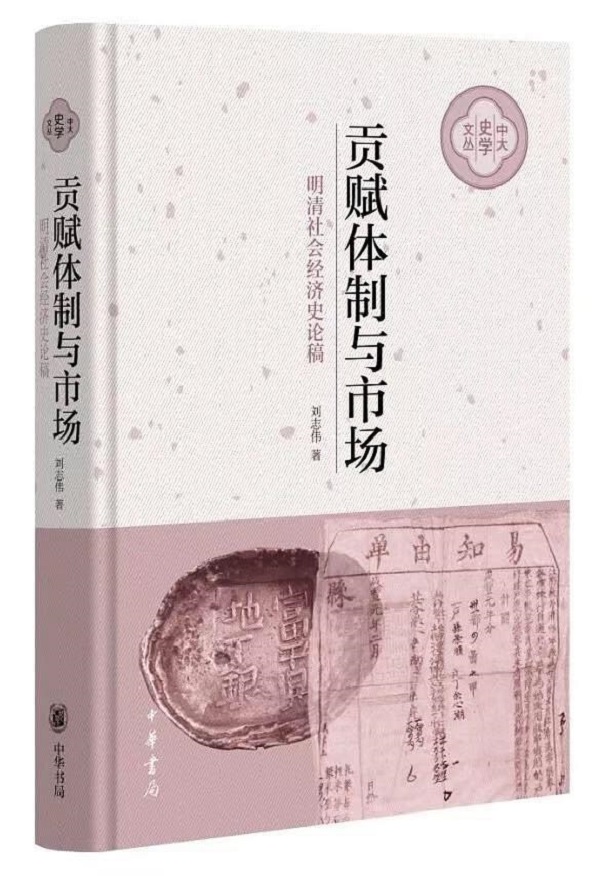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