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劇變中的永恒——《科學》百年主題及其變奏
作者按:今年是中國科學社成立和《科學》創刊110周年,特選編《科學》上“泛論科學性質”成《科學通論——〈科學〉百年文萃》以為紀念。本文為“文萃”前言,特發表以饗讀者,也以志懷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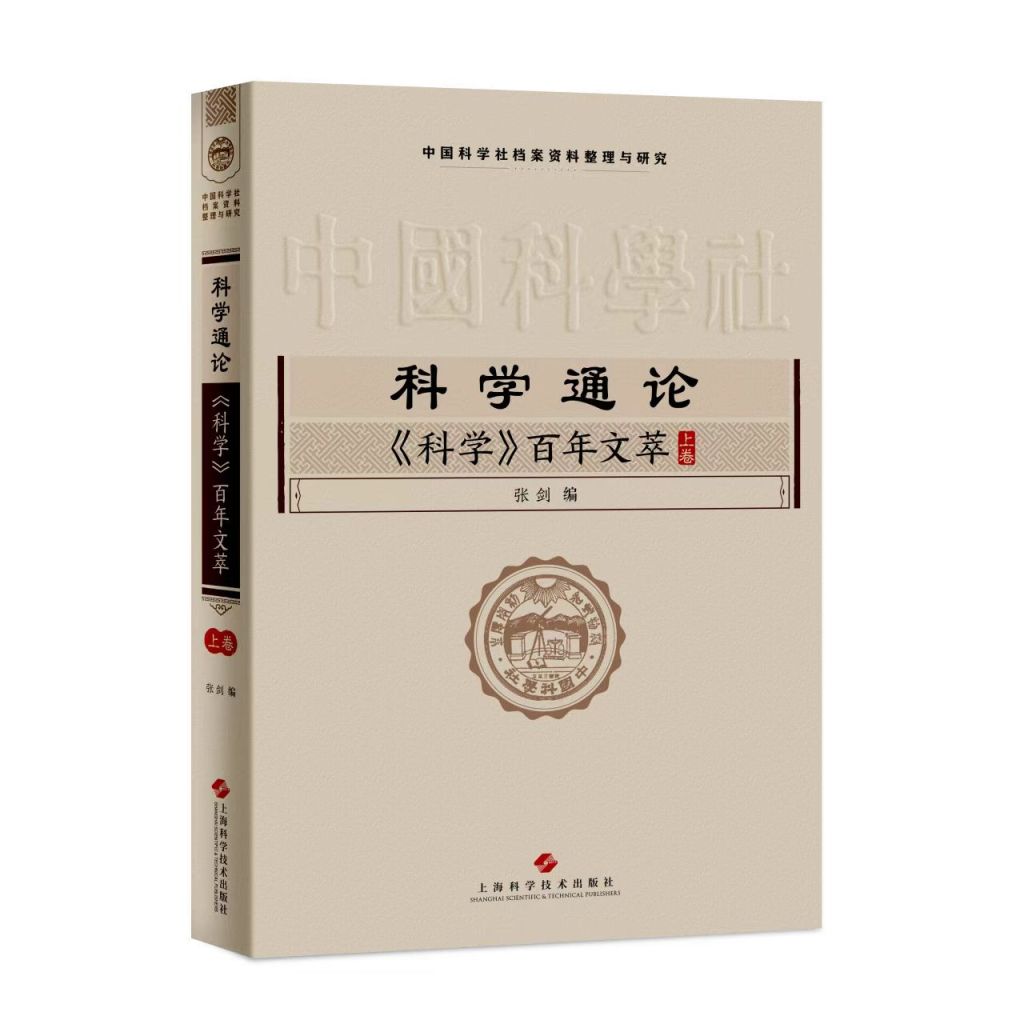
《科學通論——〈科學〉百年文萃》,張劍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25年10月版
20世紀以來,世界政治風云突變、動蕩不居,科學技術狂突猛進、革舊鼎新——這是一個劇變的時代。自1915年創刊以來,《科學》百年記載了人類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演化、中國科學技術的萌芽與本土化,也見證了這個劇變時代。雖在不同的時代,《科學》關注點不一樣,如創刊初期以宣揚科學與傳播科學知識為主,后來逐步轉向宣揚科學研究與如何發展中國科學;二戰結束后面臨核武器,主張國際科學合作、科學的合理利用與規劃科學;改革開放復刊后更矚目于國家科學發展戰略、科學發展與人類生存環境、科學與人文關系探討等;但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科學》百年來的主題及其變奏沒有改變,討論“什么是科學”“科學的社會功用”“如何發展中國科學”“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協調發展”等一直貫穿。
一、科學是什么
《科學》在《發刊詞》試圖定義科學:“科學者,縷析以見理,會歸以立例,有?理可尋,可應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其后,通過發表一系列的文章,對什么是科學有一個比較全面而透徹的認識。第一,科學首先是人類認識自然的一種系統的知識體系。任鴻雋說:“科學者,智識而有統系者之大名”。“就廣義言之,凡智識之分別部居,以類相從,井然獨繹一事物者,皆得謂之科學。自狹義言之,則智識之關于某一現象,其推理重實驗,其察物有條貫,而又能分別關聯抽舉其大例者謂之科學”。因此,歷史、美術、文學、哲理、神學等不是科學。(《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第1卷第1期)他指出科學并非當時朝野上下所認知的“奇制、實業”,而是“非物質的,非功利的”,對科學“當于理性上學術上求”。(《科學精神論》,第2卷第1期)
第二,科學有獨特的方法。科學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學問,就是因為它有獨特的方法,即演繹法、歸納法和實驗。胡明復說:“演繹者,自一事或一理推及他事或他理,……歸納則反是。先觀察事變,審其同違,比較而審察之,分析而類別之,求其變之常理之通,然后綜合會通而成律,反以釋明事變之真理。”當然,歸納法也有其局限,“科學之方法,乃兼合歸納與演繹二者。先作觀測,微有所得,乃設想一理以推演之,然后復作實驗,以視其合否。不合則重創一新理,合而不盡精切則修補之,然后更試以實驗,再演繹之,如是往返于歸納演繹之間”。(《科學方法論》,第2卷第7期)任鴻雋也特別看重歸納法,他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科學,就是因為沒有歸納法。他們都特別注重“實驗”,認為離開實驗無論如何宣稱“科學”都不是科學:“嚴格言之,惟應用科學方法之事物乃為科學。然此僅科學之名而非科學之實也。抵掌而談,執筆而書,條理井然,邏輯周密,其言非不科學,進叩其思想所從出,則所根據者皆他人之陳言而已。此于科學之名則得之矣,循此道以求科學,造其極,舉國淪為鈔胥稗販,其去科學之實且日以遠也。”(楊銓《科學與研究》,第5卷第7期)
第三,科學具有獨特的求真的“理性精神”。胡明復說:“科學方法之惟一精神曰‘求真’。取廣義言之,凡方法之可以致真者,皆得謂之科學的方法;凡理說之合于事變者,皆得謂之科學的理說。”(《科學方法論》)任鴻雋說所謂科學精神,“求真理是已”:
真理之為物,無不在也。科學家之所知者,以事實為基,以試驗為稽,以推用為表,以證念為決,而無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又不特無容心已也,茍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與吾所見之真理相背者,則雖艱難其身,赴湯蹈火以與之戰,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謂之科學精神。(《科學精神論》)
一個人要具備科學精神,必須具備崇實、貴確、察微、慎斷、存疑等特質。“求真”是科學的本質屬性,秉志以為“科學以發見真理為唯一目的”。(《科學與國力》,第16卷第7期)對此求真、存疑的“科學精神”,1990年陳光曾予以擴展,以為包括諸如“對權威的懷疑態度,描述現象的不動情感,假設構架可被驗證,數據可靠性可被測定,其理論結果可作出預言等等”。(《Scientist一詞的社會承認》,第42卷第3期)
當然,要全面理解科學,還包括“科學能擴展生活”和“科學的社會組織”兩個方面。改革開放新時期,《科學》也曾討論“什么是科學”,幾乎完全重復了當年《科學》理解科學的各個層面。廖正衡以為科學是知識體系,是“關于自然、社會、思維的知識體系”,是發展著的知識體系和知識管理活動;科學具有“觀念上的財富”或精神財富上的價值,主要表現為科學精神,“即客觀的、實事求是的、進取的、勇于創新的精神”,“是同主觀的、迷信的、盲從的、保守的、落后的思想針鋒相對的,從而也就必然可以成為反對舊思想、舊文化的思想武器”。科學的價值更重要的還在于它是“物質上的財富”,主要是表現為生產力的價值,具有不滅性、再生性、饋贈性和多層次性,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占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科學是什么?》,第42卷第2期)時東陸認為科學研究“對象是宇宙,手段是假說、實驗、推理和質疑,特征是唯一,目的是解譯自然和社會。科學里沒有權威,只有真理”。(《關于科學的定義》,第59卷第3期)
周光召說:“科學是人類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形成的正確反映客觀世界的現象、內部結構和運動規律的系統理論知識。科學還提供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態度和方法,提供科學的世界觀和處世的科學精神。”科學精神可以概括為幾個方面,諸如“科學追求的是對客觀世界運動規律的認識,因此客觀、求實是科學精神的首要要求。這表現在對待事物的態度上,就是嚴肅認真、一絲不茍、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科學認為世界的發展、變化是無窮盡的,認識的任務也是無窮盡的。因此,不斷求知也是科學精神的要求”;“科學要追求真理,不盲從潮流,不迷信權威,不把偶然性當做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整體。……科學的懷疑精神也是科學精神的組成部分”;“科學是有組織的社會群體活動,因此團隊精神、民主作風、百家爭鳴都是科學精神的組成部分”;“科學已成為社會三大實踐活動之一,不僅要認識客觀規律,創造新技術和新知識,完成發現真理的飛躍;而且要參與社會變革,促進社會進步,完成從理性認識到變革實踐的飛躍”;等等。(《科學技術和它對社會的作用》,第48卷第4期)
二、科學的社會功用
《科學》發刊伊始,就十分關注科學的社會功用,認識到科學能擴展人類生活,提高物質生活水平而外,而且能陶冶情操,提高我們的精神境界,完善人格,并由此促進世界和平。《發刊詞》說科學通過交通工具、生產工具等改變我們的物質生活;也可以通過抗災、治病救人,提高人類的平均壽命;還可以通過祛魅宗教迷信,促進人類智識進步;更為重要的是,“科學與道德,又有不可離之關系焉”;等等。此后,《科學》發表《科學與工業》《科學與教育》《科學與商業》《科學與農業》《科學與林業》《科學與實業》《科學應用論》《科學與和平》《科學與知行》《理論科學與工程》《近代科學與文明》《科學的態度》《科學與國難》《科學與民族復興》《科學戰爭與戰爭科學》等等眾多文章,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而透徹的討論。
科學最重要的社會功用是能富國強兵從而達到“科學救國”,這是中國科學社發刊《科學》的原初目標,當時形成了影響極大的“科學救國”思潮。秉志說,“吾國貧弱,至今已極,談救國者,不能不訴諸科學”,“科學造福人生,稍有知識者,類能言之,世界各國之富強,何者不由科學所致,舉凡文明民族所需者,何者不由科學而來”。中國“急需科學以為起死回生之計”,通過發展科學,“人民之知識、技能、生活、體格、思想、道德均將之而日有起色,由衰老之民族,變為鼎盛之民族”。既然歐洲科學家能將“黑暗之歐洲,改為文化燦爛之歐洲”,中國科學家也能將“將老大之民族,改為精壯之民族”。(《科學與民族復興》,第19卷第3期)發展實業是富國強兵的第一要義。任鴻雋以為科學是實業之母,實業進步有賴于科學進步,實業的推廣也有賴于科學的發展。科學家應與實業家建立良好的互通關系,他很羨慕美國實業家們在公司所創立的研究機構和實業家們與大學科研人員的合作研究。(《科學與實業之關系》,第5卷第6期)
對于科學促進人類道德發展的功用,唐鉞說:“科學固無直接進德之效,然其陶冶性靈培養德慧之功,以視美術,未遑多讓。”“科學之潛移默化,能使恃氣傲物之意泯滅于無形”;科學可以使“為善者知其方,施政者探其本,去頭痛治頭腳痛治腳之勞,收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之效”;“科學精神磅礴郁積,故能寶貴真理以忘其身,為近世文明之先導”;科學可以使“個人服公之心切,社會團結之力強”;科學可以“絕茍得幸免之心,而養躬行實踐之德”等等。(《科學與德行》,第3卷第4期)何魯討論科學與世界和平的關系也注重道德建設的重要性。他以為科學能促進世界和平有兩個原因,一是“科學為入德之門”,二是“科學能使人得幸福”,最終“科學無國界,無種族界,無意識界,一歸于真理。夫有據,故無爭,無爭即和平”。他從科學是追求真理的事業,“凡在科學上,立論必有根據,推演必本條理,不能臆造盲從”來論證“科學能使人誠,能使人耐苦,能使有秩,能使人無欲,能使人自樂,能使人愛物愛群”,因此“科學為入德之門”。(《科學與和平》,第5卷第2期)
當然,由于科學發展導致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戰爭中的使用、過度開發導致人類生存環境的惡化等,對于科學的合理利用,也成為《科學》討論的永恒主題之一。《科學》第1卷第4期為“戰爭專號”,楊銓發表文章指出科學使武器越來越精密,殺傷性越來越大,促使人們更加慎重開戰,這是科學促進世界和平的功能之一,科學是“戰爭之友”,戰爭則是“科學之敵”:“吾人之有近世文明,實科學、共和和寡戰三物之功。科學與吾人以共和,而寡戰乃得實行。……科學雖未嘗明減戰爭,然使世界知戰爭非兒戲,因而慎重其事,不敢輕試,其功亦不可沒也。……故科學者戰爭之友,而戰爭則科學之敵也。”(《戰爭與科學》,第1卷第4期)
竺可楨宣稱:“科學可以為善,可以為惡,我們利用科學來祛除迷信,延長壽命,便利交通,減免災荒,是于人類有益的。但軍事家利用以制毒氣槍炮殺人,就是作惡。一般商人政客不顧世界的需求,只圖目前的利益,無限制的利用科學來生產,亦是有弊的。”(《科學研究的精神》,第18卷第1期)對于托爾斯泰指責科學家的發明是為他人做嫁衣,“科學發達,發明愈多,是使資本家愈富,勞工愈困苦”,楊銓指稱“須知資本、勞動階級之相懸殊者,由于社會分配之不均,政治之不良,非科學之咎也”。(《科學的人生觀》,第6卷第11期)他還專文辨析托爾斯泰對科學的責難,最后說:“吾國科學尚無其物,物質文明更夢所未及,居今而言科學之弊與物質文明之流毒,誠太早計矣。然歐美物質勢力集中于資本家,社會結構因以不穩,此又吾國習應用科學者所當引為前車,勿使未來之托爾斯泰復哀吾國也。”(《托爾斯泰與科學》,第5卷第5期)對于科學的不合理利用造成一戰結束后的“科學破產論”“反科學”思潮,《科學》也曾有論辯:
歐洲大戰既興,全球震動,論者推原禍始,因國際資本主義之沖突而致怨于物質文明之過量發達,因物質文明而遷怒于科學,于是十九世紀托爾斯泰、尼采輩詛咒科學之論調復為當代救世之福音。昔之因物質文明而崇拜科學者,今則因同一之物質文明而詆毀之。潮流所被,中國亦沐其余波,此中國思想界之所以于今日學術荒蕪民生凋敝之際而忽有反科學之運動也。……夫科學之為科學,自有其本身之價值,不因物質文明之有無而增減。即物質文明之本身,亦但知利用厚生,造福人類,未嘗教人以奪地殺人也。人自無良,何預科學,因噎廢食,竊為國人所不取也。(《科學與反科學》,第9卷第1期)
原子彈爆炸使人類面臨被其制造物全面毀滅的境地,對科學的合理利用成為戰后輿論與世界科學界的共同呼聲。《科學》先后發表《原子能與科學界的責任》《科學工作者亟需社會意識》《科學與世界和平》《今日自由之危機》《科學與政治》《科學家的社會責任》等文章予以討論,并在1947年年會專題討論《原子能與和平》,會后形成宣言發表:
吾人以為科學研究,應以增進人類福利為目的,原子能之研究亦非例外。原子核可以分裂之發現,適值民主與獨裁國家進行生死奮斗之時,科學家乃將原子能用之于戰爭武器,原子能之不幸,亦科學研究之不幸也。今大戰既已告終,民主國家正在努力合作,吾人主張此種研究,應為公開的、自由的,向世界和平及人類福利之前途邁進;不愿見此可為人類造幸福之發明作成殘酷之武器,更不愿見因原子能武器競賽,或保守原子彈制造秘密之故,破壞民主國之團結或危及科學研究之自由。為此,吾人對于愛因斯坦教授所倡導的原子能教育委員會,及美國原子科學家所組織的同盟,愿予以支持。(《七科學團體聯合年會宣言》,第29卷第10期)
當然,對于科學的誤用,特別是科學借助政治而造成“非科學甚至反科學”大行其道,《科學》也有一定的警醒。早在1949年張孟聞就發表文章說李森科事件是“在科學真理之外”“帶上了政治的意義”,“科學的真理,不能以政治主張來歪曲、曲解”,“無論你是資本家也好,勞動者也好,也不論你信仰的是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或是三民主義,都得承認這個真確的事實”。因此他提出,“還真理于科學,讓事實來證明是非,不要將政治主張或宗教信仰以及其他人事糾紛涂抹上去”。(《科學真理與政治教條》,第31卷第2期)當然,他們更警覺政客們對科學的濫用,張孟聞說:“照現狀來說,與其由不懂科學也無科學素養的政客們來替世界人類謀取政治的安全,無寧是請科學家們犧牲一部分研究的時間精力來協助政治,以解決人類社會的各種困難,譬如防疫,救饑與水旱之災”。(《科學與政治》,第30卷第5期)
至于改革開放時期因濫用科學技術造成的生態危機等討論與論說,這里就不贅述。
三、如何發展中國科學
“聯絡同志,研究學術,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為中國科學社成立宗旨,科學既然具有如此強大的社會功用,如何發展中國近代科學?鑒于鴉片戰爭以來科學在中國的發展歷史,中國科學社充分意識到僅僅依靠技術引進與粗淺科技知識的普及傳播無濟于事,只有全面整體移植西方科學,才可能使近代科學在中國生根發芽。
任鴻雋連續發表《發明與研究》《科學研究之又一法》等文章,鼓吹科學研究。他指出科學成果并不是偶然所得,而需要科學家嘔心瀝血的研究,所以“發明有待于研究,而研究又有待于歷久之積力”。他介紹國外的研究機構有大學及專門學校之研究科、政府建立之局所、私家建設之研究所、制造家之試驗場,但這四類研究機構各有其優點和缺點,他心儀的是像法國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和鐳學研究所那樣“以科學上之大發明為中心,為研究特別問題而設立之研究所”。他總結說:“科學之發展與繼續,必以研究所為之樞紐,無研究所則科學之研究蓋不可能。反之,欲圖科學之發達者,當以設立研究所為第一義。”(《發展科學之又一法:法國人之好模范》,第7卷第6期)
楊銓也為文鼓吹科學研究是發展中國科學唯一正途。他說:“科學非空談可以興也。吾既喜國人能重科學,又深懼夫提倡科學之流為清談也,因進而言科學與研究。”呼吁提倡科學“當自提倡研究始”。他將西方科學研究機構從創建主體分由政府、工廠、私人、學校和學會創辦五類,以之比對國內現狀,認為上述五類機關,“政府工廠非旦夕可改良,私人亦困于環境不易實行。求其性質最近而又有改良機會者,厥惟學校與會社”。他認為當時國家正處于軍閥混戰,政府設立研究機構不可能,工廠由于自身發展缺乏設立研究機關的動力,私人更是沒有傳統,因而給當時中國科學研究指出了一條道路:大學和各科學社團聯合起來組建研究所。中國科學社生物所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這一道路的產兒——東南大學與中國科學社在人力資源上聯合創建。(《科學與研究》,第5卷第7期)
創建研究機構實實在在從事研究而外,還有不少其他可以促進中國科學發展的途徑。劉咸也有其方略,其中最為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要確立國家科學政策——“樹立科學國策,如科學教育應如何推行,國民科學常識應如何灌輸,科學工業應如何建設,科學研究應如何施展,科學專才應如何培植,科學勛功應如何懋獎,以及作科學事業之經費,應如何固定,皆須放大眼光,通盤籌算,視國家之需要,作審慎之決定”。(《科學與國難》,第19卷第2期)他與盧于道更在1936年提出“政治科學化”、推行“科學年”和設立“科學實業研究部”三大政府科學政策主張。其中關于設立“科學實業研究部”理由值得注意,他們以為當時中國最急切需要是“解除國難”與“建設國民經濟”,而“科學實業之研究”是“二者之基本”:“亟宜參考歐美各國過程,考量國家‘此時此地’之需要,于現有研究機關外,添設大規模、有計劃、有目的、組織統一、指揮若定之科學實業研究部,專門擔任復興民族、保全領土、富國裕民之研究”。他們認為1936年是中國“非常時期中之非常時期”,是“民族國家生死存亡之關鍵”,只有采取“最有效應之科學”才能自救。作為救國工具的科學至此有了更為具體的目標與更為清晰的救國途徑,利用科學的理性精神,使國家政治科學化,使政治走上科學化道路,同時利用科學研究成果,促進實業發展。(《迎民國二十五年》,第20卷第1期)
設立科學實業研究部的提議,深受當時蘇聯計劃科學體制影響。劉咸呼吁政府學習蘇聯,建立一個像蘇聯科學院一樣的機構:“所望吾國政府,對于科學事業,應效蘇聯作大規模之建置,使之負起改造國家之重任,非徒為時代之裝飾品;全國國民,應對于科學事業,尤應寄以極大之同情心與期待心,則十年之后,科學建設漸生效驗,國家前途,有厚望焉。”(《蘇聯科學院》,第20卷第8期)這種計劃科學或規劃科學的吁求,隨著大科學時代的到來,在戰后形成了一定的輿論,并一直延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科學》先后發表《關于發展科學計劃的我見》《科學研究計劃之商討》《前無止境的科學》《科學社團的效能》《工業與科學:座談會記錄》《歐洲研究組織的新動向:座談會記錄》《科學與社會》《全國科學會議》《中國科學的新方向》等。任鴻雋指出,由政府邀集專家制定的計劃,要切實可行,切忌“少數人之私見,外行建議與官樣文章”。計劃應確立純理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界限;充分考慮科學發展的總體關系、各門科學之間的關系、現存研究機構的利用與聯系、未來發展等;限定每一研究機關的研究范圍,以分工合作而避免疊床架屋等。要確保計劃實施,除獨立科學事業財政預算與科學管理人員專門化(避免使科研機關成為政府部門附屬機構,科研人員成為政府要人附屬品)外,高薪延請外國權威學者來華指導,并繼續派遣優秀青年人才留學,以期中國科學的真正獨立。(《關于發展科學計劃的我見》,第28卷第6期)
當然,中國科學社作為一個綜合性民間社團,也深知學術社團在科學發展中的作用。楊銓以為學生畢業離開學校,“科學事業告終,入而家庭,出而社會,舉非無與于科學問之事”。學術社團是養成學者的平臺,“培養訓誘而使為有用之大器,則有賴乎師友;學會,師友也”。因此,創建科學社團是發展中國科學的重要途徑之一,“憂世之士欲圖學術之昌明者,其以學會為當務之急乎”。(《學會與科學》,第1卷第7期)
要使科學在中國真正發展起來,需要社會對科學家社會角色有正確的認知,對科學家的尊崇是其表征之一。竺可楨說:“明太祖、唐太宗、漢武帝,開疆拓土,征服夷族,是暫時的,不是永遠的,是一方的,不是普遍的。至于發明家之有功于人類,是永久的,是普遍的。所以自古以來,一部人類的進化史,就是一部發明家的歷史。”(《近代科學與發明》,第15卷第4期)葛利普更是宣稱:
只有科學家得到一般人的注意,承認他在任何進步的社會中占天然領袖的地位,那科學和國家才能發達。……世界上的事業,還有什么比推進智識的疆界,增加智識的總和再要光榮的嗎?征服人民和土地的英雄,亞力山大、拿破侖、成吉思汗、塔嗎侖,若和征服自然的科學家相比較,真是可憐得很。他們的名字,容許在歷史小說上暫時存留,但他們的事業,卻早已彼此相消了。但一個蓋利略、一個牛頓、一個達爾文同其余無數的為真理及智識的進步而工作的科學家是不朽的,他們智識的勢利,是人類進步的界碑。(《中國科學的前途》,第14卷第6期)
周光召也以為,“在一些對整個地球公民都有影響作用的全球性問題上,科學家群體通常比政治家有著更客觀、更全面、更負責的觀點。科學家依靠的不是權力、不是金錢,科學家依靠的是獨立客觀的觀察與研究,是科學的分析和嚴謹的判斷,進而達成在同行內經反復討論和辯論過的共識”。(《科學家的責任》,第56卷第4期)
提出發展中國科學方略的同時,《科學》也深度反思中國為何沒有產生近代科學,從第一卷第一期任鴻雋《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中間經過竺可楨《為什么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到改革開放時期席澤宗《關于“李約瑟難題”和近代科學源于希臘的對話》、楊玉良《也談李約瑟難題》等等。具體討論這里不贅言,值得提及的是王琎以為中國科學不發達原因之一是中國的“學術之專制”。學術專制有“政府之專制,與學者之專制”,“因有政府之專制,然后有學者之專制”。因此他總結洋務運動的失敗,“在社會與學者之心理,皆不視科學為研究真理之學問,不知其自身有獨立之資格,固不必依賴富強之號召為其存在之保護人也”。他以為科學有獨立之資格,“其職務為搜求天然真理,維持人類文明,其自身之價值,固不在道德宗教政治下也”。(《中國之科學思想》,第7卷第10期)
四、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之關系
中國科學發展過程中,如何協調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科學工作者十分關注而幾乎一直無法解決的問題,也一直困擾著中國科學的發展。
1918年任鴻雋發表《發明與研究》,將科學研究分為“發現”(discovery)和發明(invention)兩類,前者曰“科學之研究”,“其目的在啟辟天然之秘奧”;后者曰“工藝之研究”,其目的在駕馭天然以收物質上之便利”。于此他清晰地區分了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也指出其本質上的差別,并進而指出發現是發明的基礎。鄒秉文發表《科學與農業》宣稱科學是農業改良的基礎,“農業非科學莫由振興”。侯德榜在中國科學社第三次年會演說《科學與工業》,指稱“工業者應用科學學理之事業也”,從開辦工業的六要素原料、資本、人才、器材、管理、銷售方面論證了工業與科學關系密切,結論是科學是工業的基礎,兩者相輔相成:“無科學不能振興工業,無工業無以促進科學,科學工業兩者輔車相依,莫能脫彼此而獨立”。其他人也相繼發表一系列文章對此予以討論,基本確立了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之間的關系,即純粹科學是應用科學的基礎,應用科學的發展也會反作用于純粹科學。
作為后發展國家,因科學的巨大社會功用,往往注重科學的實用性即應用科學,而忽視純粹科學的發展,并因而對中國科學發展造成相當的困窘。《科學》不斷發文指出僅重實用不利于中國科學的發展,呼吁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并重。翁文灝發文反對一味追求科學的實用:
試想中國自咸同以來,即重洋物,即講西學,也就是現在所謂科學。設局印書,出洋留學,提倡甚是出力,但所謂西學者,僅視為做機器造槍炮之學。惟其只知實用不知科學真義,故其結果不但真正科學并未學到,而且因根本不立,即做機器造槍炮之實用亦并未真正學好。(《為何科學研究 如何科學研究》,第10卷第11期)
秉志說:“無論研求科學與提倡科學,宜本末兼顧也。純粹科學與實用科學,二者并重,無純粹科學之根基,只求實用,難免落后。……有純粹科學,而后實用科學乃得發展,吾國今日對此二者,宜雙管齊下,不能因急切需要實用科學,視純粹科學若等閑,亦不能只知純粹科學,而毫不注意于實用。”(《科學在中國之將來》,第18卷第3期)
學者們的呼吁在現實面前自然乏力,抗戰期間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的關系已成畸形狀態。1940年同濟大學、四川大學、中山大學、重慶大學和西北大學等五所大學招生竟不能招到一名理科學生,而“所取全國學生至六千之多,工院竟占三千以上”,竺可楨“甚以基本科學即物理、化學在大學中之被蔑視為慮”,“則吾國科學前途大可悲觀矣”。(樊洪業主編《竺可楨全集》第7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5年,第465頁)因此,1943年7月由中國科學社發起的六科學團體年會中,專題討論“如何發展國內科學”時,任鴻雋作為大會主席提出:“純理科學為應用科學之基本,凡是深謀遠慮要想把國家放在現代國家之林的未有不重視純理科學的,至少純理科學與應用科學應該同時并重。但近幾年來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在大學入學考試中……理學院科系幾有無人問津之感。由國家之需要與未來之趨勢而言,應用科學較易發展,似乎不須我輩特別擔心,而純理科學則必須于此時注意提倡以免將來科學進步受到影響。提倡之法,如請政府派選留學生時增加純理科學研究之學額與政府設置大學獎學金中,明列攻讀純理科學之學額。”會議決議“政府派遣留學生時,應用科學與純理科學厲行兼顧”。最終在六團體致國防最高委員會、行政院、立法院、國民參政會電文中指稱“純理科學為應用科學之本,亦不宜顯分軒輊”。(《社友》[中國科學社第二十三屆年會特刊號(下)](1943年7月18-20日),第5-6、9-10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竺可楨在《中國科學的新方向》指明了三條發展道路,其中第一條“理論聯系實際”:“必得使理論與實際配合,使科學真能為農工大眾服務”;第二條“群策群力用集體的力量來解決眼前最迫切而最重大的問題”。這樣,計劃科學的發展與普及“呼之欲出”。計劃體制下幾十年科學的發展,“在集中力量完成國家任務、特別是國防科研方面發揮了良好作用”,但也存在一系列弊病,需要進行科技體制改革,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關系的討論又再一次掀起高潮。(周光召《中國科學和技術發展的歷史、現狀和展望》,第41卷第1期)
新時期的科學研究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周光召認為基礎研究“以認識客觀世界的物質結構、各種基本運動形態和運動規律為己任”;應用研究目的“是為了進一步發展某門技術,提高生產效率,拓寬應用領域”,其中一部分“也要從認識規律出發”,屬于“應用基礎研究”;技術開發“是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主要環節”,主要“從事生產的技術改造、工藝革新、產品更新等”。(《科學技術和它對社會的作用》,第48卷第4期)李政道以水、魚、魚市場來比喻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的關系,“沒有水,就沒有魚;沒有魚,也就不會有魚市場”。美國、日本因歷史背景不同,其科學技術發展道路也不一樣,但基礎、應用和開發研究經費的比例,基本上都保持在15%、25%、60%左右。因此,他的結論是:
中國的歷史和美國與日本都不一樣,應該走自己的路,……根據中國的歷史、中國的發展和中國的國情,來制訂科技發展戰略。美國和日本從完全不同的歷史,發展到差不多的狀況,這里面有一些共同的規律性的東西。我們可以把人家的經驗借過來,加以研究,為我所用。關鍵是要處理好基礎、應用、開發三方面研究的關系。經費的投入大致保持一定比例,才能協調地發展。(《水-魚-魚市場——關于基礎、應用、開發三類研究的若干資料和思考》,第49卷第6期)
張存浩認為基礎研究有四個方面的巨大作用: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科技與經濟發展的源泉和后盾,新技術、新發明的先導,培養和造就高層次科技人才的搖籃。因此國家要重視基礎研究,其運作要貫徹“競爭、擇優、交流、協作、開放的原則,大力提倡創新,鼓勵前沿意識并正確對待跟蹤”,確定三個層次的目標:“應用基礎研究一般應有明確的國家目標;純基礎研究開展到一定階段,常常也可有明確的國家目標,應善于捕捉這些目標;廣義地說,取得高水平成果、培養高層次科技人才也是一項重要的國家目標。”(《關于中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若干思考》,第51卷第1期)
隨著時代發展,相關純粹科學(基礎研究)、應用科學(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協調發展的討論將會繼續。同樣地,“什么是科學”“科學的社會功用”與“如何發展中國科學”,也將是未來永恒的話題。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