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不卷不喪:1200年前的INFP如何找到自洽活法
兒子在看歷史書,對于三尺童蒙而言,歷史上的人事物需要放在排行榜里論座次,方能滿足讀書人的愿望。于是“哪個朝代是最強大的?”“誰是最偉大的君主?”又或者“白起和關羽誰更能打?”……人生識字煩惱始,但是回答這些“主觀”問題時,總能令人回到書前,通過故事的再次講述,做出一次評價,確認一種價值,同時獲得新的體會。
“最偉大的詩人”——這一頭銜怕是眾說紛紜,王維大約離這頂冠冕很遠,近人不提李杜,遠者有屈子,大概是及上的。但是摩詰的詩卻是兒子張口就來的,什么“紅豆生南國”“獨坐幽篁里”,王維的詩沒有那么多情緒的流露,多的是事實、環境的直給描寫,在孟浩然、李白那里信手拈來的恣肆情緒極少顯露,也難尋杜甫后期詩歌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責任感。雖然被尊為“詩佛”,與“詩仙”“詩圣”并列,像是暗合了釋道的隱遁,熟悉又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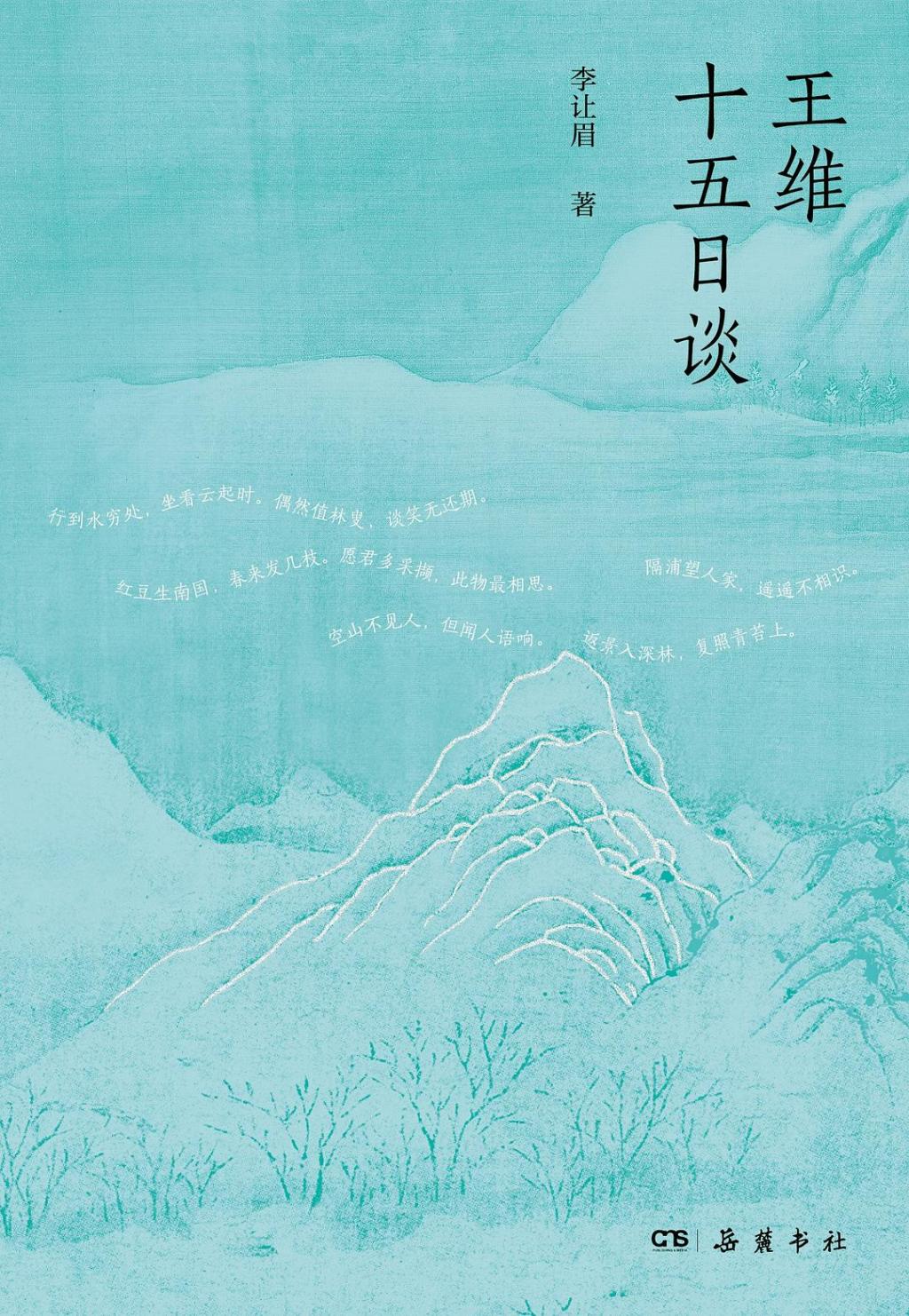
《王維十五日談》李讓眉著,浦睿文化|岳麓書社 2025年9月版
李讓眉的新書《王維十五日談》是獻給愛詩人的一幅別致畫卷,作者不僅細心整理、鉤沉了王維的生平,并且同時利用“詩史互證”的手段,盡可能地為讀者還原、揭露歷史中的詩人形象。這樣說或許有些唐突,但是詩人寫詩人真是頗得一種玄妙的快意,此書尤其適合在萬籟俱寂的夜里細細品讀,時而嗟嘆,轉身輕啟窗扉,是古今同此時的一輪明月,雖有陰晴,亙古不變。
相信不少讀者聽過王維“高臥南山”的八卦,認為我們的詩人希圖“終南捷徑”,似是一位取巧的功利主義者。隨著李讓眉的筆觸,我們得以窺見詩人少時的生平。這一部分,作者將其名為“我們對王維的誤解”,在這里,作者并沒有陷入為傳主(尊者)諱的窠臼,相反她盡可能地用史料去佐證她的觀點,并輔以唐代典制、野史記載,讓少年王維的形象立體了起來。這一部分的“釋疑”讓我想起了仇鹿鳴所著的《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雖然是名門旁支貴為高門大族,但是父親的早逝讓王維從小背上了振興家門,提攜一眾弟弟的責任,作者坦言這是李白和杜甫不用面對的情勢。
但是客觀地來說,摩詰比李杜而言,在仕途上還是更為成功一些,從早年入仕太常寺作協律郎,而后得到貴人張九齡的賞識出任京官,他的弟弟王縉更是在代宗時期官至宰輔。如果按照前文說的,王維過早地肩負起家族使命,那從結果來看他完成得十分出眾。但是作者的提問旋即而至,緣何這位生命與開元盛世高度重合的詩人,并沒有參與這一黃金時代的建構,反而在這段后世無比艷羨的時間里選擇了“半隱”,以至于他的身影在詩作之余顯得如此模糊?
書中的一段對比故事,讓人見到了作者李讓眉對于格律詩的高妙造詣。在“王維的詩交”一章中,她找出了王維與儲光羲一組應和詩,此處不再贅言。同是寫老翁耕作,儲詩更像是“實際耕作過的人寫出來的;而王詩則帶有一種“不屬于農人的灑脫”,儲光羲的詩作中田壟中老農是具體存在的客體,實實在在的他者,而王維筆下的農人則是他制造的幻象,“他在用客體替代主體的方式體面地包裹自己的表達。”作者用“體面”“幻象”凝練地概括了王維詩在讀者這里的反饋,事實上,你很少能找到王詩中“情緒失衡”的范例,他好似一個情緒穩定的現代人,這種反差感在一種情緒能量爆棚的盛唐詩人中顯得如此奇妙。除了應和詩歌,我們還能找到王維社交的畫面感,即便在詩歌的理念上不同,他和儲光羲仍舊相處融洽,各自施展彼此尊重。王維和弟弟王縉的處世風格也大相徑庭,書中提及一段時間里王縉熱衷給各色人等寫墓志銘賺“外快”,其實摩詰心中不喜,但他也沒有擺出長兄的架子去訓誡弟弟。
王維的難得或許正如同他初入官場所得的協律郎一職,盛大輝煌的時代,不缺飲馬瀚海拓土攘夷的邊塞從軍行,也不會少了糞土萬戶侯貂裘換酒的游俠豪情。在編組這一曲長歌的時候,協律郎王摩詰偏偏是那個間奏中獨一無二的存在,因為他的存在唐朝的高峰與低谷間有了一絲禪意的“預兆”,因為他在安史之亂中遭際,也能顯出一位士人、知識分子在巨大歷史變革中的掙扎、困苦與彷徨。
都說王維的詩“無我”,李讓眉說摩詰在輞川別業中洞悉到“無”,父親很早撒手人寰,發妻也早亡,王維在官場遭遇困頓之后,選擇了隱退,在輞川侍奉母親。作者無不感慨道,在摩詰母親在世的日子里,王維的詩歌難得一見地可以捕捉到詩人的真情,然而隨著母親的離世他的再次轉向空的彼岸。李讓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王維詩中的“無我”做出了如下判語,并且將李杜王三者詩歌的物我關系給出了十分恰切的闡釋——“以電影作比,李白像一條第一視角的長鏡頭,氣息凝集而順暢;杜甫似能作全景深構圖的深焦鏡頭,視野廣遠而確鑿;王維則更像一組不同機位的空鏡,時空離散并消解,鏡中的‘我’始終是可有也可無的,也就不必陷入話語權的自證。”精妙的比喻仿佛醍醐灌頂之姿,末了補上一句,也正應了古來萬千讀者對王維詩的感言——“王維的詩不搶著說話,但當你讀進去時,會覺得自己自然有千言萬語流過——不知是他的,還是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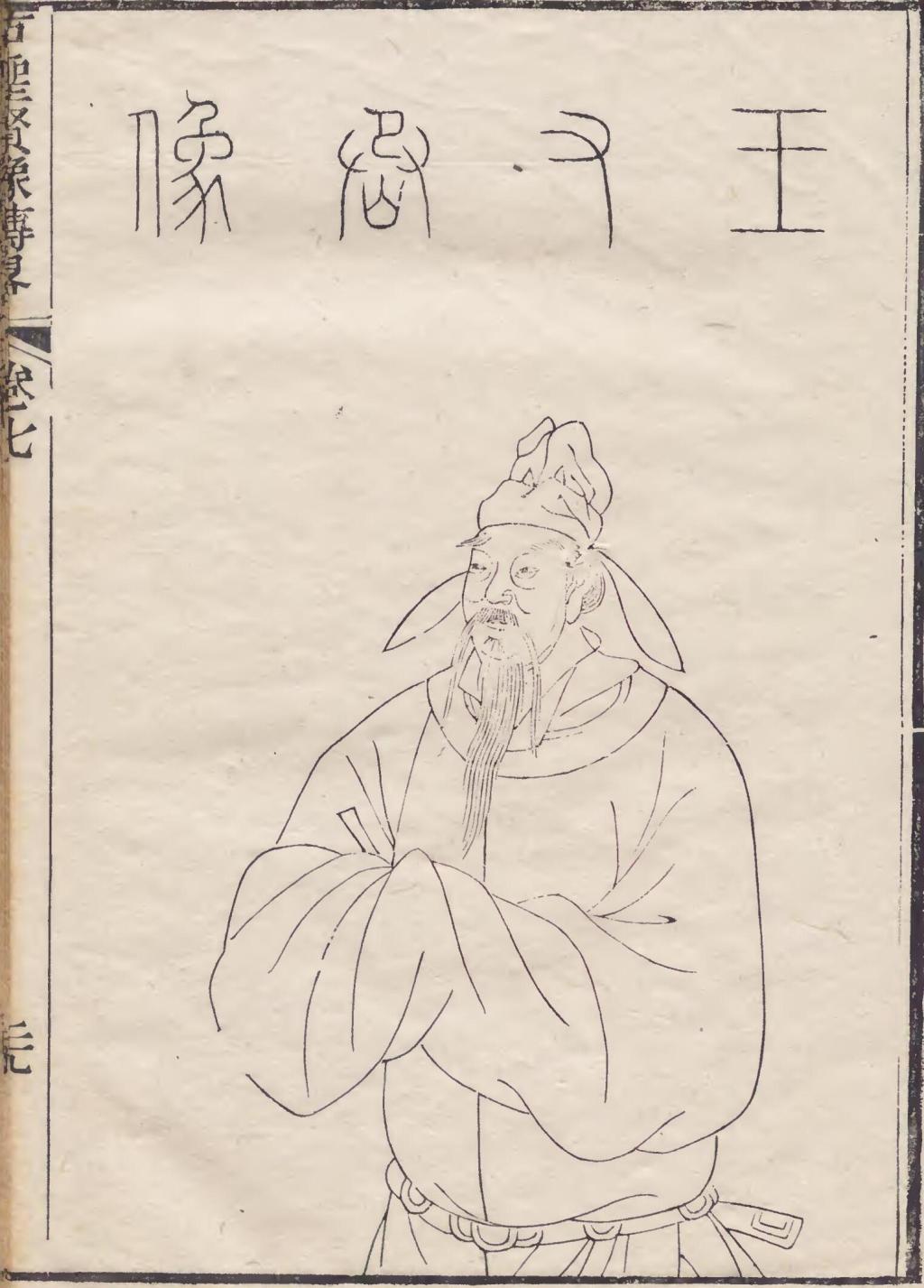
王維像
漁陽鼙鼓動地來。
并不算高官顯貴的王維被叛軍所擄,他不肯投降,一度采用吃瀉藥的方式企圖從中脫逃,當仍舊未獲成功,被迫出任偽職。即便日后克復兩京,這段暗淡的經歷仍舊是王維自認的生涯污點,此時他的弟弟王縉用官職降序換得朝廷對兄長的寬恕。但是,從李讓眉書中的講述來看,我們的詩人在后續不長的人生中再未原諒自己,而是陷入深深的自責,一如幼時背負家族重擔的那種責任感。
王維的人生不如李白那般傳奇,也未曾像杜甫那般經歷超額的磨難,更多的,在閱讀完《王維十五日談》之后,是一種可以稱作為“慶幸”的平實感,似與那想象中的盛唐景象格格不入。李讓眉輕描淡寫地表述,對更多的人來說詩歌是酒,而對于王維來說詩歌是藥,酒需要精進,而藥則用來回歸,信然。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