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專訪|何襪皮:小區保安的主要工作并不是維護安全,而是……
因在公眾號“沒藥花園”剖析真實罪案而被讀者熟知的何襪皮有著前記者、懸疑小說作家、人類學博士等多重身份。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讀人類學博士時,何襪皮將中國小區保安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于2017年在上海一個大型中產小區里展開了為期數月的田野調查,以物業公司實習生、小區居民和群租房客三重身份對該小區保安群體的日常實踐進行參與觀察。最近出版的民族志《大門口的陌生人》就是這項研究的成果。
保安在今日的都市生活中隨處可見,而正如“大門口的陌生人”這個書名所指出的那樣,對于絕大多數居民而言,他們始終是生活中的他者。“為什么保安會成為中國都市生活的必需品”是何襪皮試圖通過這項研究回答的一個核心問題,她得出的結論是,這種現象的癥結在于“恐懼”,但并非中產業主們常常宣之于口的對犯罪的恐懼,而是社會劇烈變化帶來的經濟不安全感。
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近日對何襪皮進行了專訪,訪談圍繞美國公寓門衛和中國小區保安的異同、小區保安由正式工作向非正式工作的轉變、中產小區業主對年輕高大的保安的癡迷、擁有表達恐懼特權的中產和身為被恐懼階層的保安之間的張力、保安如何面對工作中的種種不公平待遇以及他們的勞動權益能否得到更好的保障等問題展開。以下為訪談全文:
澎湃新聞:相較于人類學者,您更為人熟知的身份是真實犯罪案件寫作者,本書正文部分即以發生在大地小區的一場兇殺案開篇,書里也明確提到您最初挑選大地小區作為田野調查的地點是因為它有著混亂、危險的名聲。能否談談您為什么對犯罪、危險感興趣?
何襪皮:我在讀人類學博士之前,也是在做公眾號之前,更早做的一件事情是寫偵探小說。我一直都對犯罪解謎題材很感興趣,也讀了很多偵探小說,我覺得兇殺案是矛盾沖突、利益沖突發展到極致的一個表現形式,里面包含很多普遍卻又激烈的情感內核,所以出于個人興趣,我寫的虛構類故事基本上也是圍繞這個主題展開的。
當時我在上海做記者,報道過社會新聞,算是一種非虛構寫作,也看了很多案件的報道。后來在做公眾號初期,也給雜志做過“冰柜藏尸案”等案件的深度報道,也會用到以前做記者時的采訪、寫作經驗。另外,對于有爭議的案件或者懸案,我會很想要尋求答案,也算是一種對解謎的興趣。
在博士論文選題的時候,我最初選的是做金三角賭場的題目,同樣是出于對犯罪的興趣,但后來因為種種個人原因沒能去做,我就想在當下我們自己的社會中找一個貼近犯罪主題的選題,考慮到可操作性等各方面因素,就決定研究小區保安這個群體。
澎湃新聞:當發現大地小區事實上是一個相當安全的城市空間之后,您對研究方向進行了怎樣的調整?
何襪皮:其實沒有做太多調整。雖然我盡量挑了一個大家認知中比較混亂的小區,但我自己實際上也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我也知道這個城市空間整體上是比較安全的,所以這個發現其實也是符合我的某些設想的,而從這個發現出發,我反而可以更好地去觀察保安究竟在維護一線城市的空間安全當中扮演了多重要的角色,他每天到底在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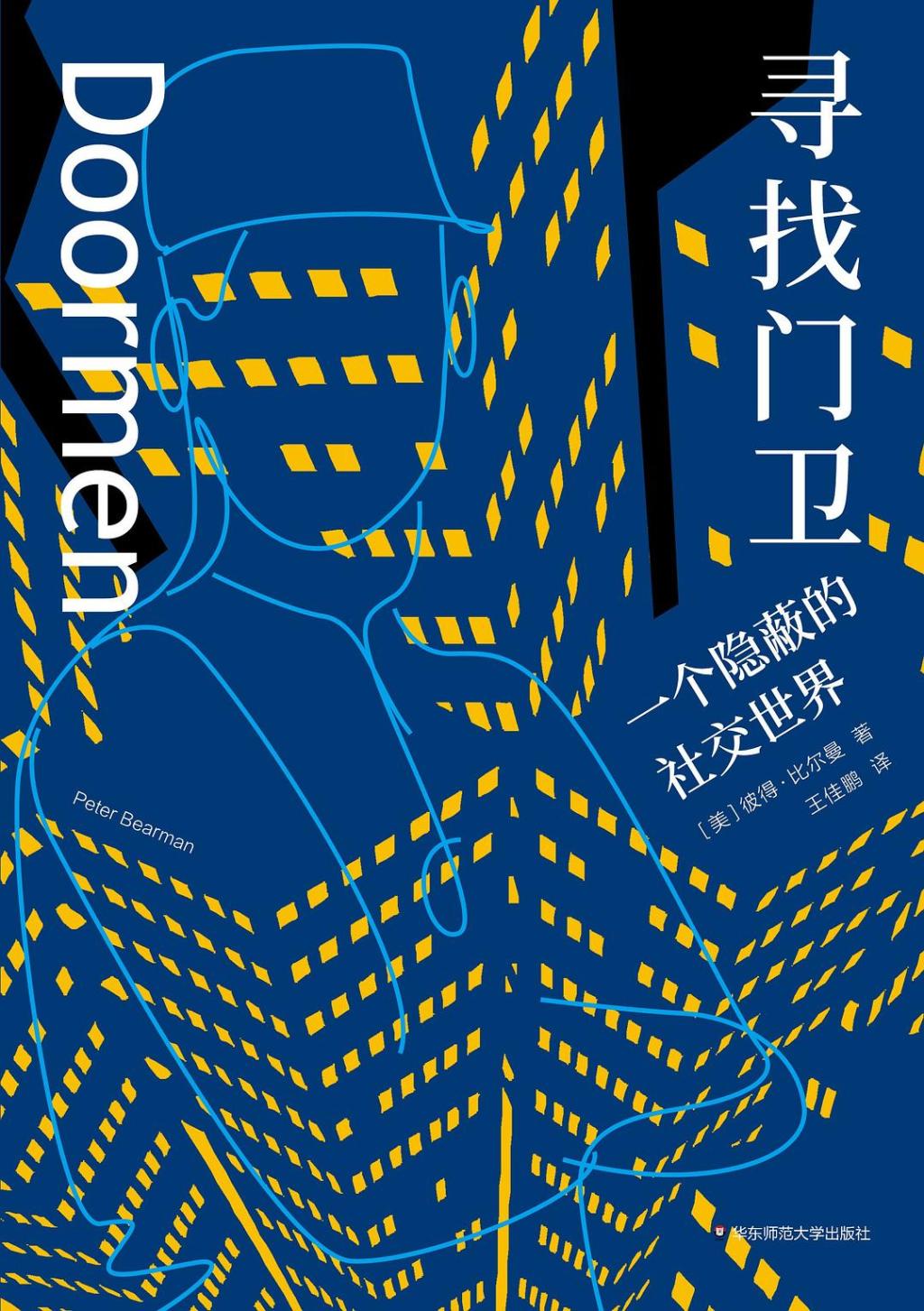
澎湃新聞:這本書很容易讓人聯想起美國社會學家彼得·比爾曼前幾年被翻譯成中文的《尋找門衛》(Doormen),他筆下的美國公寓大樓的門衛和您研究的中國小區保安是否具有一定的可比較性?
何襪皮:在美國,比爾曼所寫的門衛通常只在紐約這樣的大城市才有的。僅從職責上來說,這種公寓大樓的門衛在功能上有點像中國以前計劃經濟時代職工公房的門衛。但他寫的門衛和現在的小區保安有一個相似點,就是他們在社會經濟地位上和業主相差比較大,但在物理空間上又十分接近,這是由從事這份職業的人所屬的階層和職業的性質決定的。但是,這兩份工作整體上有很大區別。美國的門衛和中國以前的老公房的門衛,他們的工作性質都比較單純,主要就是給居民登記、開門或者收發郵件,甚至連停車都不用管,而中國現在的商品房小區里的保安,他們的職責通常是很繁雜的,特別是規模比較大的住戶多的商品房小區里面,有很多日常維護的體力活、雜活,都是保安來做的。除了門衛,美國少數封閉高檔小區會雇傭二十四小時執勤的保安,這些保安是真正的專業安保人士,通常接受過擒拿、急救和使用緊急設備的培訓,會攜帶警棍、胡椒噴霧、手銬甚至配備槍支,專門負責巡邏和守門。中國小區保安有點像把美國的門衛和保安結合起來,但又缺乏后者的專業性。
澎湃新聞:比爾曼的書中有很多篇幅是關于門衛如何處理和不同住戶之間的關系,但您的書中似乎很少涉及保安和小區居民/業主之間的互動,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何襪皮:因為比爾曼寫的門衛在空間上是離居民更近的,他負責的是那一棟樓,他每天坐在里面,替居民開門,傳遞郵件,與居民有日常接觸和交流,彼此之間的互動也比較密切。而中國的小區保安其實主要是站在小區的門口或者在公共空間巡邏,而不是一棟樓的門口,物理空間上首先要遠一些,其次保安一般也沒有日常近距離服務業主的機會,很多時候這種功能是由物業的人來行使的。如果沒有突發事件,保安甚至不會進入到樓棟里面,跟業主的互動都是在小區的大門口發生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在管理停車的時候,和作為車主的業主發生某種簡單互動。不過,有時候業主有特別的需求,比如要搬東西找不到人,他可能會找保安,但這不是日常性的,而是偶發性的。另外,現在國內一些高端的小區還有管家,他們更像是物業工作人員,會承擔收發郵件、給忘帶鑰匙的業主開門等非體力的工作,與居民的互動更多。我的研究主要觀察的是一個保安服務外包給保安公司的小區,保安全都是外來人口。但我的書中也提到那種依然由物業雇傭本地人的老小區,譬如我父母住的地方,那些保安和我父親這類老居民的互動就比較多,他們經常會在飯后一起抽煙聊天。
澎湃新聞:您在田野調查期間,見證了大地小區西區正式雇傭的本地保安被非正式雇傭的外地保安取代的過程。這項變化導致居民和保安之間本就十分脆弱的平等關系徹底崩坍,外地保安面臨著低薪、嚴重超時工作、沒有社會保險、拖欠工資、隨意解雇等種種不公平待遇。從表面上看,這一改變是物業公司出于規避風險、節約成本的目的做出的,但這顯然不是故事的全貌,保安工作由正式工作向非正式工作的轉變是由哪些因素共同促成的?
何襪皮:對于整個小區來說,變化是在很多方面同時發生的,包括園林外包、保潔外包以及保安外包。這種變化跟整個行業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以前只有公安局才能成立保安公司,所有保安公司都是有國資在里面的,201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保安服務管理條例》默認市場向民營資本開放,此后出現了大量私營的保安公司,整個行業蓬勃發展,而私營的保安公司又沒法跟國有的保安公司競爭,像銀行、政府大樓這類場所他們是拿不下來的,所以就主要針對小區,會進行大量的市場推廣。一方面,他們會降低成本,用更低的價格去競標;另一方面,他們也會制造需求,以前的本地保安可能就坐在小區門口看看門,那么保安公司會宣傳自己的保安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提供更好的服務。對于物業公司來說,最重要的當然是經濟方面的考慮,我的書里也算了一筆賬,外包后他們節省了大量的成本,以及擺脫了對保安意外傷亡的賠付責任。但也不僅是經濟,還在于外包以后在管理上更省心,他們只需要向保安公司下達命令就可以了。所以市場上的小區保安服務紛紛被外包了。
對于業主來說,尤其是很多的年輕業主,他們也更喜歡保安公司的新保安,并不是說他們在維護安全的專業性方面有多強,而是他們是更有紀律性的,比如大地小區更換的新保安在工作的時候是不能看手機、不能抽煙的,而這些都是原來的老保安做不到的,這兩種保安提供的服務質量是不一樣的,所以業主也會督促物業去換掉老保安。總之,這種變化是幾方的需求共同促成的。

老公房的門衛崗亭。
澎湃新聞:吊詭之處還在于,保安一方面似乎并沒有在履行保衛安全的職責,保障安全的功能更多是靠攝像頭等技術手段來達成的,另一方面他們又承擔了大量體力的、繁雜的、牽涉大量情緒勞動的小區工作,那么小區保安究竟是一種形式主義,還是一種沒有得到正確命名的必要工作?
何襪皮:小區保安這個工作有一部分確實是作為形式存在的,我在炫耀性消費這一章節里重點介紹了為什么這個市場癡迷于年輕高大的保安,因為在老齡化的社會中,在這個社會地位不高的行業中,年輕和高大都是稀缺資源,擁有它們的小區可以和其他小區制造階層差異。小區門口站的保安代表了小區的臉面,有點像古代官邸門口的石獅,可以彰顯這個宅子的身份和地位。
但小區保安并不完全是形式主義,它也有實際的功用。我在書里也寫到了,我覺得這個工作有點像雜役,什么都干一點,主要是一些不算累的體力活,因此中老年、低學歷者都能勝任。當然不同類型的小區情況可能也不太一樣,對于高檔小區,因為有更強的保潔團隊、園林團隊、維修團隊,很多雜活可能就由各個專業團隊消化掉了,而老公房小區可能沒有特別多的東西要維護,但像大地這樣的規模特別大但又沒那么高端的小區,很多雜活就都落到了保安的身上。沒有了他們,還真難說那些大大小小的雜事該由誰來完成。
對于這樣一份職業,有沒有比保安更好的命名?這個工作的主要功能還是守門。這個守門的意義更主要的是指管理車輛的進出、停放(從本地保安換成外地保安的潮流和中國汽車行業的大發展是差不多同步的),但除了守門又附加了很多其他職責,有一部分保安是巡邏崗,并不站在門口,因此叫門衛也不合適。對于保安行業來說,他們肯定更希望這種服務叫保安,而不是雜役,因為保安聽起來更專業,也更迎合中產對安全的焦慮。我也想不出還能有什么稱呼更正確的命名。
澎湃新聞:書中一項有意思的發現是,中產小區業主對于年輕高大的保安有著強烈的渴望,甚至于保安公司提供的服務標準本身就是按照保安的年齡來劃分的(A級別35歲以下,B級別35-45歲,C級別45-55歲)。年輕人在勞動力市場上受到青睞往往是因為成本較低、可塑性強等原因,而在保安工作當中,被看重的似乎更多是年輕的身體(書中小亮的例子很值得玩味,他在做保安之前的工作是夜店男公關),能否談談這個現象在當下社會中意味著什么?
何襪皮:一方面是大城市老齡化,另一方面伴隨著房價和生活成本的升高,大約是從2014年開始,城市里的流動人口就開始下降了,這兩者導致年輕、高大、外形好的年輕人在保安這個行業中更加稀缺。再加上從事體力勞動的外來民工往往出生在比較低的階層,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可能也沒有充足的營養,他們當中許多人身材偏矮小。書里也寫到,大地小區的另一個保安團隊想提拔隊友為隊長,要求是1米72以上、30歲以下的隊員報名,或許這聽上去并不是很高的要求,但是整個大地保安團隊里面除了已經是隊長的那個人,沒有一個人符合。
現在的年輕人特別不愿意進入缺乏體面的、低社會地位的職業。這也跟大學的擴招有關,每個家庭都希望子女能夠有一個大學文憑,因此很多年輕人有了一個含金量并不高的大學文憑之后,他們就很少會愿意從事純體力的工作了,他們不會去當保安。現在很多需要技術的體力活,比如裝修工、建筑工人,都是中老年人在做,而年輕人都在競爭低月薪的所謂白領工作,這導致保安行業較難招到年輕人,更別說外形好、高個子的年輕男性。而當一種資源越是稀少的時候,它就越是珍貴,若有年輕高大、像退伍軍人一樣的保安站在小區門口,大家普遍會默認這個小區的物業費比較高,這個小區的房價不便宜,中上產業主們渴望這樣的保安形象,也體現了炫耀性消費的需求。
澎湃新聞:年輕人在保安行業中能夠獲得更好的崗位,也有更多的晉升機會,這是否意味著和同樣是非正規工作的騎手工作,保安是一份更有未來的職業?
何襪皮:這不一定,如果你能在年輕的時候把握機會,那20多歲時很可能可以當上班長隊長,但也僅僅是隊長而已,如果保安公司失去了這個物業的合同,他換一個項目,可能就失去隊長的職位了。僅僅在我在大地的那幾個月,就有兩個隊長、多個班長被撤,有的去送外賣了,有的當回了普通保安。但一個隊長若要繼續往上走,當上項目經理,可能性就不是很大了,而且在這個行業里,一旦過了30歲,你的優勢就急劇下降了。在晉升到像區域經理這樣的管理層崗位之前,你的明面工資是固定的,是沒有多少主觀能動性可以發揮的,你整日就是一個等待被安排的角色。而騎手至少對自己的工作時間、收入是有一定的靈活掌控度,而且在外賣行業剛興起的那幾年,騎手的收入比保安是要高很多的。但這兩年進入外賣行業的人太多了,騎手收入有所下降。我去年也問過書中提到的小亮,現在他是一個高檔小區的保安隊長,有沒有想過去送外賣,他說兩者收入差不多,但他的工作清閑多了,所以他不會去。但總體而言,即使是具有身高優勢的年輕人進入保安行業,未來的前景也不是一定有所保障的。

澎湃新聞:小區業主對年輕高大保安的偏好,是否說明人的身體對于這份工作而言不可或缺,因此也不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何襪皮:從炫耀性消費的層面來講,小區保安的潮流和趨勢都是由高檔小區所引領的。上海在1998年房改之后,一開始是只有高檔小區才有這種彬彬有禮地為你服務的保安,后來中檔小區也有了,再后來公房、里弄也都有了。我覺得之后的趨勢還是會像奢侈品一樣,如果人工智能更昂貴、更稀缺,那么可能會先在高檔小區推廣,然后再逐步流行開來。但現在其實很多高檔小區已經有門禁、梯禁,進小區、進樓棟、坐電梯都要刷卡,新的小區還有人臉識別、眼球識別等等,這已經比保安守門守得嚴多了,但這些具備高科技的高檔小區還是請人在小區門口站著,反而有更大的保安團隊,這或許說明,不管是因為人的靈活性也好,還是因為雇人更昂貴所帶來的階層“區隔”(布迪厄)也罷,目前人還是有不可取代的地方。
澎湃新聞:本書構建了“恐懼金字塔”理論來探討政府、中產階層業主、被恐懼階層各自的擔憂以及這些擔憂如何互相作用:政府對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的關切推動了保安行業的創立和發展;中產階層的真實恐懼是房產貶值和經濟地位跌落,但他們熱衷于將這種恐懼表述為對于犯罪的恐懼;保安身處的被恐懼階層則往往無從表達自己對于失去尊嚴、安全和最低生存空間的恐懼。書中也談到,中產階層的“恐懼”是一種特權,是一種會員制,由此通過保障被恐懼階層、接納他們成為社群的一部分是不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理想?
何襪皮:我在書里介紹了關于恐懼的理論,1990年代有兩個學者做了這方面的研究,發現好萊塢恐怖片里的主人公都是中產,他們在自己的房子里或者在度假屋里,遇到了很恐怖的事情。而被恐懼的人很多都是來自底層的流浪者,或者是像鬼怪這樣被異化的人或物。制造恐懼的這一方因為沒有什么可以失去,處于一種瘋狂的絕望之中,所以他們讓那些有家庭和財產要保護的人感受到害怕自己被傷害的這樣一種恐懼。類似的,中產在日常敘事中講到他們的擔憂或者對于外來保安的不信任時,他們很多時候也會提到保安的收入太低了,沒有什么保障,從而認為他們可能會抵抗不了財產的誘惑。他們意識到這些外來打工者的生活陷入了一種令人絕望的困境當中,這種困境在特定情況下可能激發他們做出一些違法的事情,這是業主產生擔憂的一個根源。
所以我覺得,如果雙方都處于一個同樣的經濟地位,或者有很好的社會福利,這些人沒有面臨巨大的物質差距的時候,業主也就可以放下心來。在歐美的很多國家,藍領收入和白領收入已經很接近了,像在美國,一個水管工或者園林工人,每個月可以賺到5000多美元,長途大巴司機有的每年有十幾萬美元收入,跟一般的坐辦公室的中產收入相差不大,基本的生存需求能夠得到很好的滿足,這種情況下可能一方就不會認為另一方會覬覦自己的財產,藍領不會有非常強烈的相對剝奪感。但這種改變不是單獨某個小區可以改變的,而是整個行業發展到一定程度,自然會出現的一個趨勢。當愿意做藍領工作的人越來越少,這些工作的收入自然就會提高,工作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樣和所謂的職業體面性或者說社會地位成正比了。現在上海很多裝修工人其實一個月可以賺到一兩萬,和白領工作的差距變小甚至超越了。譬如我之前刷到有個叫阿燕的女子在香港從事樓梯的泥瓦工程,每天工作8小時,月收入達到了10萬港元左右,因為在香港,建筑行業的泥瓦工等技術工人由于需求量較大,且工作強度和技術要求較高,所以薪資水平相對較高。當然,一旦經濟進入下行期,這種趨勢就有可能被擾亂。
澎湃新聞:書中也寫到了保安的日常抵抗,例如偷懶不巡邏,晚上打瞌睡,例如被奉為拾金不昧楷模的保安實際上同時也將撿拾無主財物作為生財之道,保安隊長可以通過“吃空頭”等手段獲得額外的收入等等。從一個人類學家的視角,您如何看待和理解這些行為?
何襪皮:“everyday resistance”(日常抵抗)是由美國人類學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提出的概念,是指 “在不易被觀察和控制的場域中,弱者所進行的持續、微觀的反抗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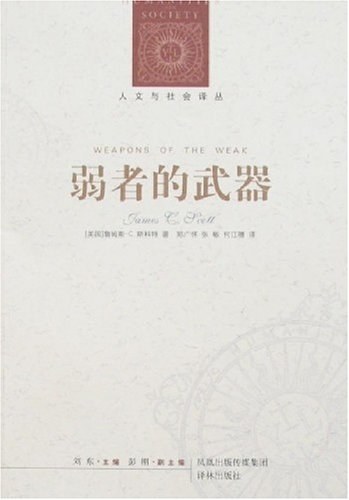
這種現象是很正常的。一方面是保安收入低,另一方面是這份工作本身的意義比較匱乏,他們并不能從中獲得一種強烈的精神滿足,或者說覺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這種情況下人很容易懈怠。特別是晚上物業都下班了,隊長可能也睡覺了,很多保安也會打瞌睡,在寒冷的冬夜也會躲在崗亭里不去巡邏,因為反正也不會有人來檢查。而白天的時候,有一套非常明確的懲罰制度被用來管理他們,如果抽煙或者看手機被物業發現,就會罰款,所以他們不得不保持一種紀律性,雖然他們可能也沒有真正打起精神來留意進出的人,而是在神游或者發呆。當一份工作無法提供足夠的激勵,也無法讓人從中獲得精神滿足時,那么一旦外部的監督減弱,把任何人放在這個位置,可能都會有一樣的日常抵抗的舉動。和這種情況形成對比的就是送外賣,對于騎手來說,一旦有所懈怠當天的收入就會下降,而是送外賣需要集中注意力,走神會影響效率甚至還可能出車禍。一些保安會說自己不想去送外賣,因為太累太耗神,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他已經習慣了保安這種精神渙散的工作狀態,已經沒有辦法再集中起注意力,專注地去做更有挑戰性的事情了。
至于偷拿停車費以及吃空餉,這些行為顯然是不正確的,也超出了日常抵抗的范疇,但在這個職業的設定和制度下面,這些都是很容易出現的“鉆空子”行為,在這個行業里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澎湃新聞:“階層的空間化”也是本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但在“大地小區”的案例當中,可以看到階層的流動和模糊:大地的前身是上海最大的棚戶區,2000年以前有超過一萬戶低收入群體居住于此;在展開田野工作的2017年,該小區的房價在500萬-2000萬,小區居民包括靠房價飆升積累財富的本地人、在限購政策出臺之前來此投資房產的其他省份的富人和有體面工作的高收入精英移民;在群租房被整治之前,租客的經濟情況大相徑庭,以年輕的小白領居多,而小區里的保安宿舍事實上也是一種群租房……這些情況是否說明,至少在當時,階層的空間化并沒有徹底完成?今天這種流動和模糊是否仍然存在?
何襪皮:中產階層本身是一個很大的概念,在美國從月薪3000到月薪幾萬都屬于中產。國外的中產有一個發展的歷史,他們一般有類似的教育水平或者職業地位,而中國的中產階層沒有明確的定義,因為中國所有的階層都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才逐漸形成的,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中產階層就是有產階層,或者說有房階層,但不同房產的價值差異又是巨大的,所以說這個概念非常模糊。但總體而言,大地小區的業主,不管是老上海人還是新上海人,或者是租房的人,包括租住條件相對好的群租房的很多人,都是屬于大的中產概念。商品房的發展就是階層空間化的過程,把具有相同資產水平的人歸類到了一個小區,也就是一個空間。但是那種將一套房分割成很多隔間、每個隔間的租金在800-1000的群租,它就違反了那個空間的階層準入條件,租住在這些房間的保安和其他低收入者確實是這個空間的異類。
和十年前相比,通過房產來累積資本的渠道應該說已經不再對大多數人開放了,但社會上也有很多新興產業在興起,比如互聯網或者網紅經濟等等,這些新產業還是有很多制造新財富的機會。
澎湃新聞:在本書臨近結尾時,大地的業委會表決解聘了信澤物業公司,2021年信澤連同兩家保安公司從這個服務了20年的小區黯然離場。本書記錄的是這個行業和群體的一個階段,保安行業在當下是否迎來了新的變化?例如今年9月1日開始施行的《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中“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或者勞動者向用人單位承諾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該約定或者承諾無效”的規定,是否會對保安行業產生影響?
何襪皮:其實勞動法之前就規定了必須要給員工繳納社保,但落實到基層有很多渠道來規避,其中確實包括通過讓保安寫承諾書證明他們在農村有新農合,用來出示給檢查人員以避免罰款。我當時問過保安公司的區域經理,他就說私營保安公司如果要給保安交社保的話,上海沒有一家保安公司能夠生存下去。但是據我所知,像萬科這樣的小區,保安都是物業自雇而不是外包的,保安的工資會比較高,而且都會交社保,那么人力成本就必然要提高。而那些保安工資只有4000的小區,如果開始交社保,必然要有人對額外的經濟支出買單,要么物業降低利潤率,要么削減保安人數或者用已經到退休年齡的保安,這些成本最終都會以某種方式轉嫁到業主身上。
對于保安來說,過去很多人不愿意交社保,是因為他們覺得必須要連續繳納15年這個要求太難達到了,自己不可能領到退休工資,他們對這份工作的穩定性是沒有期待的,而且當下對他們來說拿到足夠的錢養家糊口更重要,無暇考慮太多未來的事情,但如果能夠形成一個穩定的政策,如果政府能夠許諾無論之后做什么工作都會有社保,他們能夠滿足交滿15年這個領退休金的必要條件,那么我想大多數人應該是愿意交的,長期來說對他們自己肯定是有益的。

澎湃新聞:您是一個有多重分身的寫作者,在您看來寫作真實案件、虛構懸疑小說和民族志時有什么不同和共通之處?這些不同的分身之間又是如何相互影響的?
何襪皮:民族志的寫作跟我早期寫的新聞報道包括公眾號上的非虛構文章,我覺得還是有一定的共通性的,它們都是對一個事實的陳述,然后會有理論化的提煉,要把文章寫得吸引人,就不能單單是堆砌事實或者平鋪直敘地講述,肯定是需要一些敘述技巧的,在尊重事實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鑒小說的敘事技巧。和大眾關注度很高的真實熱點案件相比,寫小說能夠在不激起輿論雙方爭論的情況下,通過一個虛擬的故事來表達自己的主張和立場,這是另外一種滿足。這部民族志讓我對保安群體有了深入的了解,所以我接下來的小說里有一個主人公就是一個保安,而恐懼理論我之前在一篇關于陰謀論的論文里就有涉及,在之后的虛構創作當中可能也會有所體現。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