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她的宇宙”| 繳蕊:歐洲電影中的身體“起義”與女性解放
UCCA尤倫斯當(dāng)代藝術(shù)中心正在呈現(xiàn)瑞士空間影像藝術(shù)先驅(qū)皮皮樂(lè)迪·里思特(Pipilotti Rist)的大型個(gè)展“掌心宇宙”。受此啟發(fā),UCCA特別策劃展覽平行系列對(duì)話“她的宇宙:女性在文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和電影學(xué)中的位置”,希望通過(guò)文學(xué)、社會(huì)學(xué)與電影學(xué)三個(gè)領(lǐng)域的交叉碰撞,更深入地展現(xiàn)女性在文化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中所扮演的多元角色及其主動(dòng)創(chuàng)造的能量。9月20日,該系列第三場(chǎng)對(duì)話在UCCA報(bào)告廳舉行,由電影學(xué)博士、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文學(xué)院講師繳蕊主講。

講座中,繳蕊梳理了歐洲電影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導(dǎo)演與作品,介紹她們?nèi)绾瓮ㄟ^(guò)影像美學(xué)與敘事策略發(fā)起關(guān)于身體的自我解放,即如何爭(zhēng)取與展現(xiàn)女性身體自主權(quán)、欲望表達(dá)權(quán)及社會(huì)可見(jiàn)性。今天,關(guān)于身體的個(gè)體記憶在公共場(chǎng)域中不斷被各種語(yǔ)言講述,而電影讓身體得以在跨越時(shí)空的影像中相遇。從電影誕生之初,女性身體就是重要的被觀看對(duì)象;然而這門在“男性凝視”下成長(zhǎng)的藝術(shù),也記錄了女性從客體位置逃逸的路徑,并逐漸成為女性自我解放的武器。銀幕上自由的身體召喚著解放的目光,而這樣的目光也引領(lǐng)我們看見(jiàn)更多被解放的女性,在影像的對(duì)視中分享流動(dòng)的生命。
電影史中的“男凝”機(jī)制

身體“起義”:歐洲電影中的女性解放史”公共活動(dòng)現(xiàn)場(chǎng),2025年9月20日,北京UCCA尤倫斯當(dāng)代藝術(shù)中心
在講座開篇,繳蕊分享了自己觀看“掌心宇宙”展覽的感受。她談到,皮皮樂(lè)迪·里思特的作品為身體賦予了全新的感知方式:觀眾可以“用眼睛去觸摸”和“用身體去觀看”,在沉浸的環(huán)境中擺脫他人的注視,獲得一種久違的自由。她認(rèn)為那種可以隨意躺下、翻滾、回到童年般自在狀態(tài)的體驗(yàn)非常值得享受。在這種自由感的啟發(fā)下,繳蕊提出問(wèn)題:“皮皮樂(lè)迪·里思特所呈現(xiàn)的身體解放,究竟是對(duì)人類本能的自然回歸,還是與20世紀(jì)女性運(yùn)動(dòng)的遺產(chǎn)緊密相關(guān)?”帶著這一思考,她引出了講座的主題——回顧電影藝術(shù)發(fā)展脈絡(luò)中女性身體的歷史,探討女性導(dǎo)演如何通過(guò)影像回應(yīng)身體、自由與解放。
從展廳中對(duì)身體自由的沉浸式體驗(yàn)出發(fā),繳蕊進(jìn)一步追問(wèn):“這種自由的感受背后,隱藏著怎樣的視覺(jué)文化傳統(tǒng)?尤其是電影——這門長(zhǎng)期被‘男性凝視’所環(huán)繞的藝術(shù)——是否能夠真正擺脫目光的桎梏,并與社會(huì)思潮產(chǎn)生同頻的振動(dòng),進(jìn)而成為女性身體解放的記錄者與引領(lǐng)者?”她以勞拉·穆爾維在1975年發(fā)表的論文《視覺(jué)快感與敘事電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為切入點(diǎn),解釋了“男凝”這一概念:經(jīng)典敘事電影制造視覺(jué)快感的機(jī)制,往往依賴于將女性塑造成欲望客體,以滿足觀眾的窺視沖動(dòng)。
然而電影并非天生受制于“男凝”。雖然電影史的主導(dǎo)敘事常由男性書寫,但在電影史上,女性導(dǎo)演早已以獨(dú)特的生命經(jīng)驗(yàn)與身體意識(shí)開辟了另一條影像道路。
愛(ài)麗絲·蓋伊:被遺忘的第一位女性導(dǎo)演
翻開任何一本世界電影史,總會(huì)看到許多人爭(zhēng)奪“世界電影之父”的名號(hào),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世界上第一部虛構(gòu)劇情片,誕生在一位女性導(dǎo)演——愛(ài)麗絲·蓋伊-布拉切(Alice Guy-Blaché,以下簡(jiǎn)稱愛(ài)麗絲·蓋伊、蓋伊)的手中。

愛(ài)麗絲·蓋伊
愛(ài)麗絲·蓋伊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導(dǎo)演,并且在她最初近十年的創(chuàng)作里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女性導(dǎo)演,對(duì)電影藝術(shù)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xiàn)。然而,她的貢獻(xiàn)在很長(zhǎng)時(shí)間里被遺忘,甚至她的孫女也在她自己的紀(jì)錄片《愛(ài)麗絲·蓋伊·布拉切不為人知的故事》里坦言,自己從未意識(shí)到祖母竟是拍出世界上第一部故事片的電影人。
像當(dāng)時(shí)許多女孩一樣,受社會(huì)性別角色限制,蓋伊進(jìn)入社會(huì)所能從事的工作不外乎秘書、文員等崗位。21歲時(shí),她進(jìn)入高蒙公司擔(dān)任秘書,開始接觸電影行業(yè)。1895年,她隨老板萊昂·高蒙觀看了盧米埃爾兄弟的內(nèi)部放映后,萌生了自己拍片的念頭。她創(chuàng)作的第一個(gè)作品《甘藍(lán)仙子》(La Fée aux choux,1896)源自法國(guó)民間童話:一位仙女從巨大的、用紙板做的卷心菜里“變”出一個(gè)又一個(gè)嬰兒,為渴望孩子的年輕夫妻實(shí)現(xiàn)愿望。這部短片被視為世界上第一部虛構(gòu)劇情短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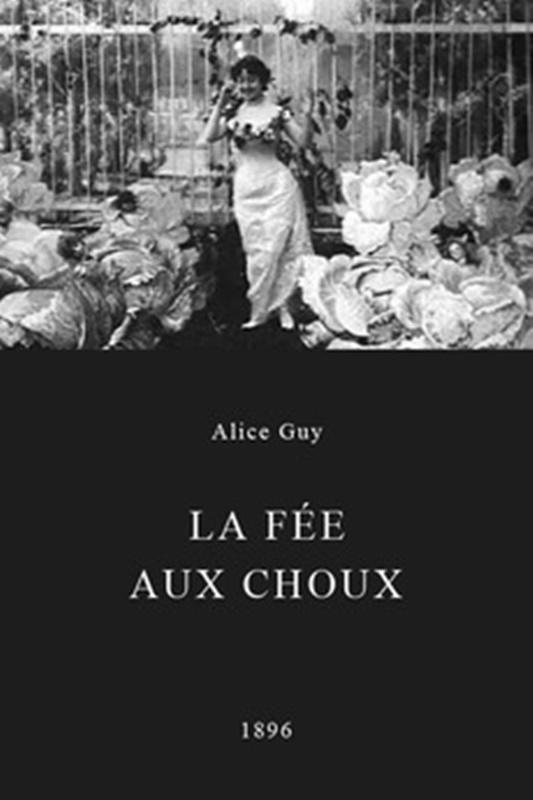
《甘藍(lán)仙子》電影海報(bào)
影片的成功使她延續(xù)了這一主題,隨后蓋伊又推出了幾個(gè)重制的版本,都與生育的主題有關(guān)。比如《上流社會(huì)的接生婆》(Sage-femme de premièreclasse,1902)用幽默喜劇的方式表現(xiàn)生育與家庭生活。她十分擅長(zhǎng)將輕松俏皮的劇情與女性視角結(jié)合,既吸引觀眾,又傳遞了女性對(duì)身體與生命經(jīng)驗(yàn)的獨(dú)特感受。
蓋伊的創(chuàng)作并不限于對(duì)生育的描繪,她的另一部代表作《女性主義的成果》(Les Résultats du féminisme,1906)更是一次性別角色的顛覆實(shí)驗(yàn)。影片設(shè)想了一個(gè)性別倒置的社會(huì):男性困在家中,照顧孩子、操持家務(wù);女性則自由外出,聚會(huì)、抽煙、社交。這部輕松的喜劇沒(méi)有刻意宣稱政治立場(chǎng),卻在無(wú)意間挑戰(zhàn)了性別秩序的合理性。
作為世界上第一位女性導(dǎo)演,愛(ài)麗絲·蓋伊不僅在高蒙公司時(shí)期創(chuàng)作了大量開創(chuàng)性的作品,還在美國(guó)成立電影公司,拍攝了數(shù)百部影片。除此之外她還參與了公司的藝術(shù)指導(dǎo)、技術(shù)革新(包括早期的彩色與錄音實(shí)驗(yàn))以及人才培養(yǎng)。
繳蕊表示,令人遺憾的是,愛(ài)麗絲·蓋伊因?yàn)殡娪肮I(yè)化后的結(jié)構(gòu)性排斥而被遺忘。蓋伊不僅才華橫溢,還積極鼓勵(lì)其他女性投身電影創(chuàng)作,并堅(jiān)信這是一個(gè)女性可以大放異彩的領(lǐng)域。然而,隨著電影逐漸發(fā)展成有利可圖的產(chǎn)業(yè),女性的創(chuàng)作空間被迅速壓縮,原本的自由被剝奪,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女性不適合從事電影”的社會(huì)灌輸。從愛(ài)麗絲·蓋伊的經(jīng)歷中可以看到女性在文化產(chǎn)業(yè)中從被允許、被歡迎,到被系統(tǒng)性洗出局的全部過(guò)程。
直到二十世紀(jì)五十年代,隨著女性主義的興起,年邁的蓋伊才開始重新為自己發(fā)聲,試圖找回她在電影史中的位置。紀(jì)錄片《愛(ài)麗絲·蓋伊·布拉切不為人知的故事》讓她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曉。2024年巴黎奧運(yùn)會(huì)開幕式,蓋伊的雕像與其他九位女性一起被升起,終于讓全世界共同銘記她作為世界上第一位女性導(dǎo)演的身份。蓋伊的一生,既象征了早期電影里的女性創(chuàng)造力,也是女性如何在電影工業(yè)化過(guò)程中被系統(tǒng)性邊緣化的縮影。她的作品向我們證明,在“男性凝視”之外,影像完全可以孕育出另一種美學(xué)傳統(tǒng):充滿樂(lè)趣、身體感知與女性視角。最后,繳蕊說(shuō),“盡管愛(ài)麗絲·蓋伊的一生有遺憾,但女性在電影行業(yè)的熱情一直在延續(xù)和燃燒;同時(shí)她的經(jīng)歷也提醒我們?nèi)A聽那些被歷史壓抑的聲音。”
熱爾梅娜·迪拉克:歐洲電影中的現(xiàn)代主義先鋒

熱爾梅娜·迪拉克
繼愛(ài)麗絲·蓋伊之后,繳蕊為我們介紹了法國(guó)電影另一位具有先鋒意義的女性導(dǎo)演——熱爾梅娜·迪拉克(Germaine Dulac,以下簡(jiǎn)稱迪拉克),她在1920年代開辟了與愛(ài)麗絲·蓋伊不同的道路,她不僅推動(dòng)法國(guó)電影的現(xiàn)代主義轉(zhuǎn)型,還積極推動(dòng)女性在社會(huì)中的影響力,也為女性導(dǎo)演在影像藝術(shù)中提供了獨(dú)特視角。當(dāng)時(shí)法國(guó)電影不再主導(dǎo)世界潮流,要想重回巔峰,必須尋找一條與美國(guó)電影迥異的現(xiàn)代主義路線。
1920年,迪拉克與路易·德呂克合作拍攝了《西班牙嘉年華》(La fête espagnole, 1920),開創(chuàng)了法國(guó)印象派電影的先河。1923年,她獨(dú)立執(zhí)導(dǎo)的《微笑的布迪夫人》(The Smiling Madame Beudet, 1923)將意識(shí)流文學(xué)與印象派繪畫手法相結(jié)合,通過(guò)光影、節(jié)奏和畫面構(gòu)圖表現(xiàn)角色內(nèi)心的欲望與心理流動(dòng),成為法國(guó)印象派電影的代表作之一。1928年,她又拍攝了超現(xiàn)實(shí)主義電影《貝殼與僧侶》(The Seashell and the Clergyman, 1928),影片通過(guò)實(shí)驗(yàn)性的影像展示身體的律動(dòng)與愛(ài)欲的張力,挑戰(zhàn)了當(dāng)時(shí)的傳統(tǒng)道德與社會(huì)禁忌,呈現(xiàn)了個(gè)體情感與欲望的自由表達(d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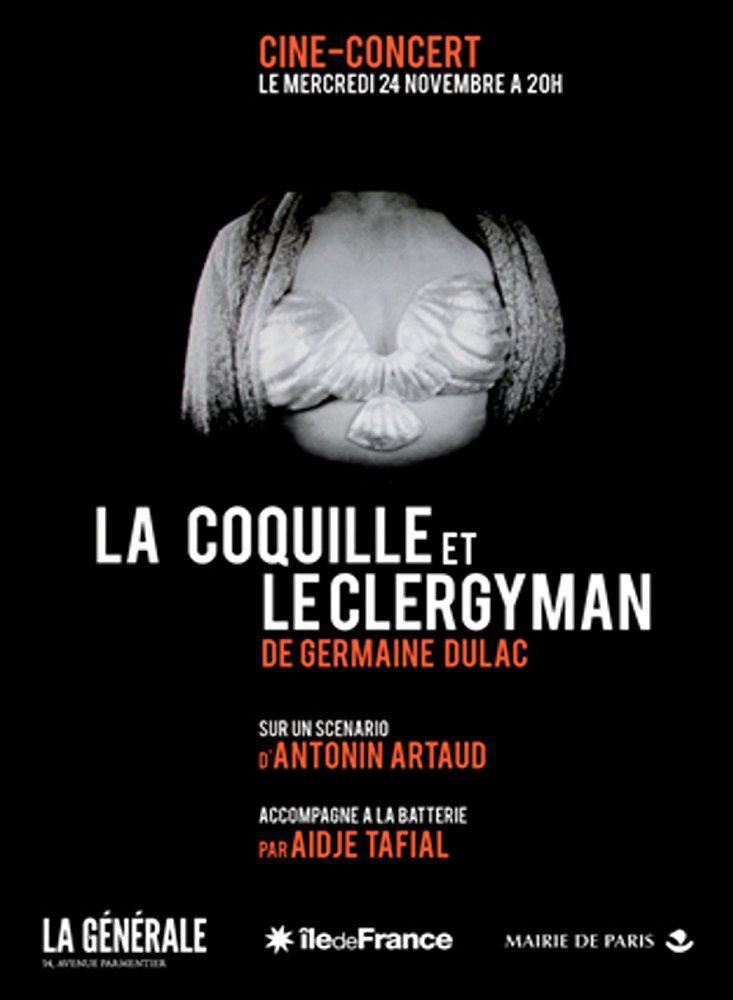
《貝殼與僧侶》海報(bào)
作為一位獨(dú)立反叛的女性導(dǎo)演,迪拉克自身的影響力在電影工業(yè)化與社會(huì)規(guī)范的雙重壓力下難以被完整呈現(xiàn)。《貝殼與僧侶》藝術(shù)價(jià)值卓絕,和作品《一條安達(dá)魯狗》一樣經(jīng)典,但卻被電影史忽視。雖然迪拉克的作品引領(lǐng)了法國(guó)乃至整個(gè)歐洲電影向現(xiàn)代主義轉(zhuǎn)變,卻因社會(huì)和行業(yè)的限制,被迫在歷史敘事中退居幕后,其貢獻(xiàn)未能得到應(yīng)有的承認(rèn)。
繳蕊說(shuō)道,“二戰(zhàn)之后很多事情都被改變了,人們的思想也被改變了,電影也被改變了。”戰(zhàn)后的人們渴望自由與解放,觀眾,無(wú)論男女,都在這些影像中尋找從戰(zhàn)爭(zhēng)陰影中走出的激情與可能性,因此女性裸露的身體在這時(shí)也成了一種自由的符號(hào)。然而,在男性導(dǎo)演凝視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女性身體在銀幕上體現(xiàn)的所謂“自由”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商品化與符號(hào)化的風(fēng)險(xiǎn),電影中的女性形象往往背離了真實(shí)。
此時(shí),戰(zhàn)后的女性主義和存在主義思潮出現(xiàn)為女性身體的呈現(xiàn)提供了新的方向。例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提出的:“女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她與同時(shí)代的存在主義者共同以“身體的實(shí)踐”來(lái)檢驗(yàn)真理。和她并肩的思想者們,如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通過(guò)工廠勞動(dòng)寫下《工廠日記》,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則進(jìn)一步提出“性差異”是當(dāng)代的根本問(wèn)題,強(qiáng)調(diào)唯有承認(rèn)差異,才能找到通向未來(lái)的路徑。她們都試圖用真實(shí)的身體經(jīng)驗(yàn),打破語(yǔ)言與理論的遮蔽。
一場(chǎng)溫柔的反叛:阿涅絲·瓦爾達(dá)
談到法國(guó)新浪潮,人們很容易想到戈達(dá)爾或特呂弗,但阿涅斯·瓦爾達(dá)(Agnès Varda)始終是其中一位最獨(dú)特的聲音。她的作品常常帶有輕快、愉悅的表面,卻在溫柔中包裹著尖銳的女性主義思考。
1958年的短片《穆府的歌劇》(L'opéra-mouffe, 1958)是瓦爾達(dá)懷孕時(shí)的創(chuàng)作。在滿街流浪漢、破敗景象的環(huán)境中,她選擇用孕婦的眼光觀察世界。影片中用切開的南瓜類比鼓起的肚子呈現(xiàn)懷孕的身體,帶著一點(diǎn)超現(xiàn)實(shí)的幽默。瓦爾達(dá)提醒觀眾,每一個(gè)無(wú)家可歸、飽受苦難的人,都曾是母親懷中的嬰兒,生育在這里被賦予了希望和力量。
1962年的《五至七時(shí)的克萊奧》(Cléo from 5 to 7, 1962)則是瓦爾達(dá)對(duì)女性主體性的深刻探索。年輕的女歌星克萊奧,在誤以為自己身患重病的時(shí)刻,才突然意識(shí)到必須擺脫被觀看的命運(yùn),學(xué)會(huì)“觀看他人”。這部影片比“男性凝視”概念廣為傳播要早,卻已清晰描繪了女性如何在凝視與被凝視之間爭(zhēng)奪主體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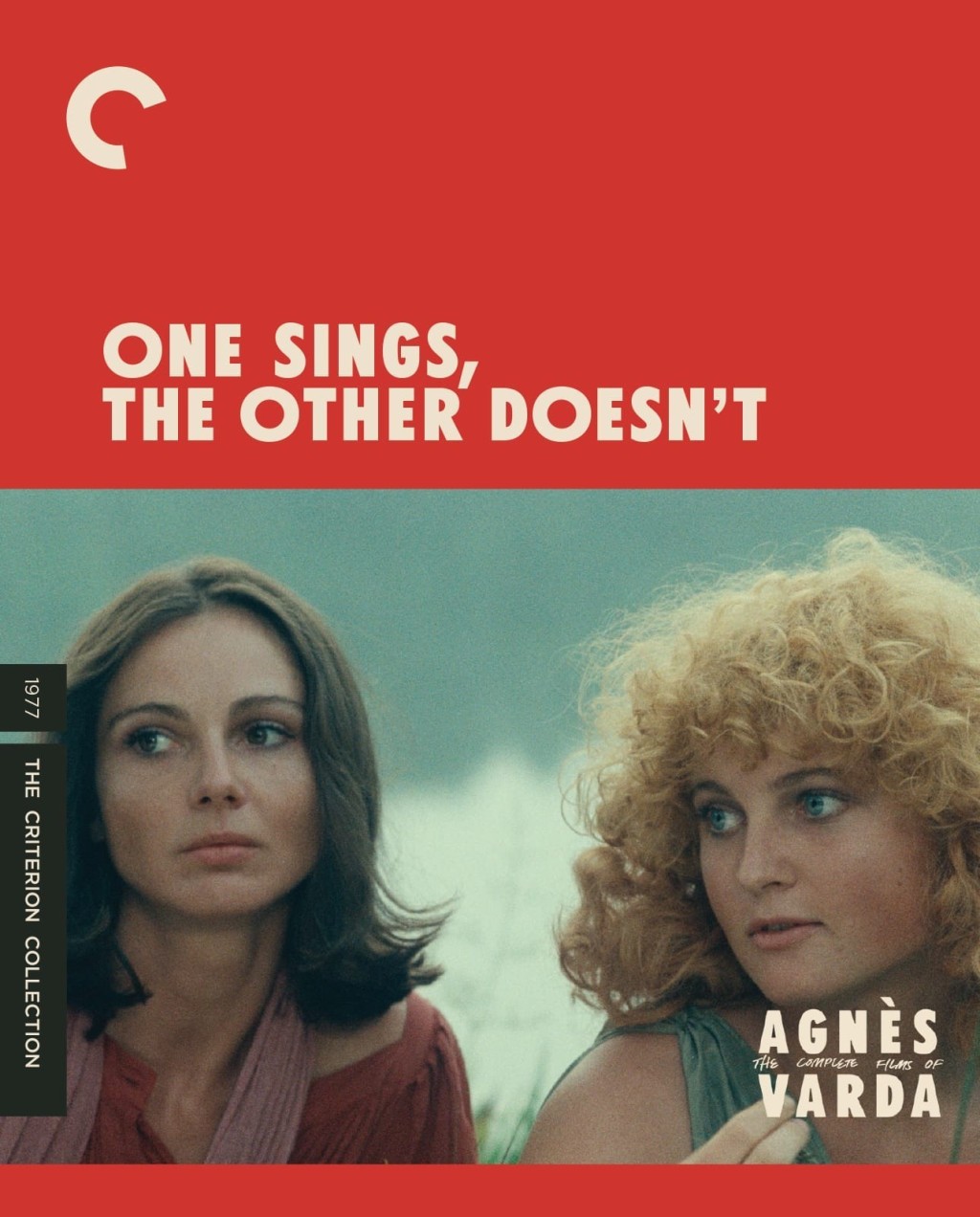
《一個(gè)唱,一個(gè)不唱》海報(bào)
到了1977年,《一個(gè)唱,一個(gè)不唱》(Unechante,l'autrepas, L', 1977)被瓦爾達(dá)稱為自己的第一部女性主義故事片。影片中的兩個(gè)女性角色,一個(gè)因意外懷孕而走向計(jì)劃生育運(yùn)動(dòng),另一個(gè)則在積極參與爭(zhēng)取墮胎權(quán)的抗?fàn)幒螅嬲\(chéng)地選擇了生育。瓦爾達(dá)借此表達(dá)了復(fù)雜卻真摯的立場(chǎng):她既支持女性擁有墮胎的自由,也認(rèn)為生育同樣是一種值得尊重的選擇。她把這些刺痛的經(jīng)驗(yàn)化作輕快的歌聲,將沉重的社會(huì)議題轉(zhuǎn)化為觀眾可以親近的影像。她希望女性主義思想能夠走向大眾,進(jìn)入更多人的生活,而不是只停留在小圈子里。她的電影在法國(guó)能吸引幾十萬(wàn)觀眾,這對(duì)她來(lái)說(shuō),比實(shí)驗(yàn)性的孤立表達(dá)更有價(jià)值。
瓦爾達(dá)的人生與作品充滿矛盾。她既是堅(jiān)定的女性主義者,又深情地?zé)釔?ài)愛(ài)情與生育;她經(jīng)歷過(guò)被拋棄的痛苦,卻依舊將懷孕視為寶貴的生命體驗(yàn)。正是這些真實(shí)的矛盾與溫柔的表達(dá),讓她成為獨(dú)一無(wú)二的電影作者,也使她的作品直到今天仍然啟發(fā)我們思考女性如何通過(guò)影像去爭(zhēng)取表達(dá)、爭(zhēng)取自由。
“其實(shí)今天依然能看到類似的情況,只是隨著社會(huì)的進(jìn)步,我們已經(jīng)在一點(diǎn)點(diǎn)抵御這些刻板印象。”繳蕊在講座最后總結(jié)道。她認(rèn)為瓦爾達(dá)的經(jīng)驗(yàn)提醒我們,獨(dú)立的女性聲音在歷史中常常被遮蔽,但她們的作品依舊提供了穿透時(shí)間的力量。
對(duì)話|影像的身體:皮皮樂(lè)迪·里思特與女性的自由表達(dá)

“身體“起義”:歐洲電影中的女性解放史”公共活動(dòng)現(xiàn)場(chǎng),2025年9月20日,北京UCCA尤倫斯當(dāng)代藝術(shù)中心
吳伊瑤:皮皮樂(lè)迪在20世紀(jì)80年代錄像藝術(shù)興起之時(shí),便大膽選擇將女性身體經(jīng)驗(yàn)置于作品的核心。從早期以自身為影像主體,到利用內(nèi)窺鏡探索身體內(nèi)部的結(jié)構(gòu),皮皮樂(lè)迪不斷用直接、坦率的方式呈現(xiàn)女性的感受與欲望。這種“自我觀看”的姿態(tài),與傳統(tǒng)電影中女性身體作為被動(dòng)客體的模式形成了鮮明對(duì)比。在皮皮樂(lè)迪早期的影像中,她曾將披頭士歌曲的歌詞改寫為第一人稱的表達(dá),從“她不是一個(gè)朝思暮想的女孩”變成“我不是那個(gè)朝思暮想的女孩”。這種由第三人稱到第一人稱的轉(zhuǎn)變,可以說(shuō)是對(duì)流行文化中男性敘述的回應(yīng),也象征了女性開始掌握屬于自己的話語(yǔ)。通過(guò)慢放、失真、故障等錄像手法,皮皮樂(lè)迪營(yíng)造出與傳統(tǒng)敘事截然不同的氛圍,讓觀眾在感官與心理層面體驗(yàn)到女性主體性的多樣形態(tài)。那么,當(dāng)我們現(xiàn)在看到《掌心宇宙》中宏大的、沉浸式的宇宙意象,再重新去觀看藝術(shù)家早期更為直接、身體化的錄像作品時(shí),該如何理解她在敘事與創(chuàng)作方式上的轉(zhuǎn)變?
繳蕊:皮皮樂(lè)迪的早期作品所展現(xiàn)出的強(qiáng)烈能量,正是那個(gè)時(shí)代藝術(shù)家對(duì)身體、自由和生命力的集中表達(dá)。她毫無(wú)保留地以自身身體作為媒介,去糾正和突破既有的禁錮,這種真誠(chéng)與勇氣并非來(lái)自“天性”,而是建立在前人努力和社會(huì)思潮的推動(dòng)之上。皮皮樂(lè)迪當(dāng)時(shí)的創(chuàng)作“很滿”,是一種時(shí)代精神的真實(shí)寫照。相比之下,如今她在《掌心宇宙》中呈現(xiàn)的則是一種更為坦然、恬靜的狀態(tài),與瓦爾達(dá)晚年創(chuàng)作中所展現(xiàn)的從容一樣。這種對(duì)比啟發(fā)我們思考女性藝術(shù)家如何在不同歷史語(yǔ)境中不斷尋找新的自由表達(dá)方式。
吳伊瑤:在皮皮樂(lè)迪的代表作《Ever is Over All》中有這樣的一個(gè)劇情,一位面帶笑容的年輕女性揮舞著一朵看似柔軟卻堅(jiān)硬的花苞,沿街砸碎汽車車窗,而一旁的女警不僅沒(méi)有阻止,反而對(duì)她報(bào)以微笑與敬禮。這種帶有戲謔和天真色彩的表達(dá),讓人聯(lián)想到女性導(dǎo)演愛(ài)麗絲·蓋伊在影片中通過(guò)性別轉(zhuǎn)換和喜劇手法展現(xiàn)欲望與身份的方式,這兩種戲謔與幽默之間是否存在聯(lián)系?
繳蕊:女性幽默本身就是一個(gè)極具研究?jī)r(jià)值的話題。在愛(ài)麗絲·蓋伊的創(chuàng)作中,幽默往往帶有“取悅觀眾”的成分,她希望觀眾能夠笑、能夠留下來(lái)看電影,因此主體意識(shí)并不完全自主。而在皮皮樂(lè)迪·里斯特的錄像藝術(shù)中,幽默感則來(lái)自更為自覺(jué)的女性主體性表達(dá)。她以“諧謔”的方式化解刻板印象和男性凝視,借由輕松和笑意讓觀眾意識(shí)到女性可以突破規(guī)范、展現(xiàn)自由與反叛。這種幽默不再是討好,而是一種獨(dú)立的姿態(tài)。皮皮樂(lè)迪的作品往往不僅僅是“我是誰(shuí)”,更是邀請(qǐng)觀眾進(jìn)入一個(gè)共享感受的世界。從早期強(qiáng)烈的自我表達(dá),到后期更具開放性和慷慨分享的創(chuàng)作,皮皮樂(lè)迪讓觀眾在輕松中被納入她所營(yíng)造的感官宇宙。如今,無(wú)論是走進(jìn)黑暗展廳還是影院,觀眾都會(huì)與陌生人共享同一種感受。在流媒體和小屏幕逐漸取代影院的今天,這種空間性的集體體驗(yàn)正在被削弱,而在展覽中重溫這種“共同的黑暗”,也能讓人重新體會(huì)到電影黃金時(shí)代所帶來(lái)的群體共振。
現(xiàn)場(chǎng)討論
觀眾一:我想問(wèn)兩個(gè)問(wèn)題。第一,近年來(lái)一些男性導(dǎo)演的作品也被稱作“女性主義電影”,但往往伴隨著爭(zhēng)議,例如蘭斯莫斯的《可憐的東西》、貝克的《安莫拉》,這些電影雖然打著女性主義旗號(hào),卻充斥大量女性裸露鏡頭。您覺(jué)得這類電影是真正的女性主義創(chuàng)作,還是另一種男性凝視?第二,男性創(chuàng)作者在拍攝女性主義題材時(shí),是否存在先天局限?如果有,該如何克服?
繳蕊:我先回答第二個(gè)問(wèn)題。男性導(dǎo)演在創(chuàng)作女性主義題材時(shí)是否有局限?我認(rèn)為局限并不來(lái)自生理結(jié)構(gòu),而在于思維方式。比如伯格曼,他的私生活充滿爭(zhēng)議,但在他的電影里,我們卻能看到深刻的女性經(jīng)驗(yàn)與情感表達(dá),《婚姻生活》中瑪麗安控訴丈夫和婆婆的場(chǎng)景,就是非常強(qiáng)烈的女性主義時(shí)刻。這讓我思考:為什么一個(gè)不合格的父親和伴侶,卻能在藝術(shù)上如此觸及女性的生命經(jīng)驗(yàn)?
瓦爾達(dá)在訪談中多次提到,她非常欣賞伯格曼,甚至覺(jué)得他對(duì)女性的理解比很多女性導(dǎo)演還要深入。我認(rèn)同這一點(diǎn)。所以問(wèn)題的關(guān)鍵不在于性別生理差異,而在于是否足夠真誠(chéng),是否愿意超越成見(jiàn)去理解生命。
至于第一點(diǎn),這類作品是否能稱為“女性主義電影”,其實(shí)并沒(méi)有統(tǒng)一答案。有人會(huì)感到冒犯,有人卻被深深打動(dòng)。比如《可憐的東西》,它是否是女性主義電影并不是最重要的問(wèn)題,重要的是它觸及了哪些關(guān)于身體和自由的經(jīng)驗(yàn),并與怎樣的觀眾產(chǎn)生共鳴。我們不能用“是不是女性主義”這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去判斷電影的價(jià)值。
在父權(quán)社會(huì)的語(yǔ)言和邏輯里,我們習(xí)慣于一切都要?jiǎng)澐譃閷?duì)立:男或女、強(qiáng)或弱、主或客。但露西·伊利格瑞指出,女性的存在其實(shí)是流動(dòng)的、柔軟的。所以,當(dāng)我們?cè)谟懻撃巢侩娪笆遣皇恰芭灾髁x電影”的時(shí)候,如果仍然用二元對(duì)立去劃線,就很可能忽略了作品更為細(xì)膩、復(fù)雜的一面。也許更重要的是,它有沒(méi)有在經(jīng)驗(yàn)層面讓觀眾感受到自由、壓迫、欲望的流動(dòng),以及女性主體性的伸展。
吳伊瑤:繳蕊老師剛剛提到導(dǎo)演的女性意識(shí)問(wèn)題,我想請(qǐng)問(wèn),這種女性意識(shí)是否有一個(gè)可以界定的起點(diǎn)?還是說(shuō),其實(shí)從她們開始以自身經(jīng)驗(yàn)、以女性視角進(jìn)行創(chuàng)作時(shí),就已經(jīng)是女性意識(shí)的表達(dá)了?
繳蕊:這是很好的問(wèn)題。我認(rèn)為女性意識(shí)的覺(jué)醒不是某個(gè)單一的瞬間,而是一種持續(xù)的過(guò)程。比如波伏娃,她在哲學(xué)寫作里也不斷追問(wèn)“作為女性意味著什么”。即便她和薩特一起構(gòu)建存在主義,她依然要面對(duì)女性在自由選擇上受到的限制。這種思考是伴隨一生不斷展開的。同樣,對(duì)于導(dǎo)演或普通人來(lái)說(shuō),女性意識(shí)會(huì)隨著生命經(jīng)驗(yàn)和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不斷流動(dòng)和發(fā)展。與其說(shuō)有一個(gè)“節(jié)點(diǎn)”,不如說(shuō)它是一種持續(xù)生長(zhǎng)的狀態(tài),而正是這種未完成性讓生命和藝術(shù)更加豐富。
觀眾二:我一直喜歡女性主義電影,但感覺(jué)近三五年沒(méi)有看到特別先鋒、尖銳并且有力量的作品。之前像《讓娜·迪爾曼》和《四月三周兩天》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它們即使放在今天也依舊鋒利。我想請(qǐng)問(wèn),您最近有沒(méi)有發(fā)現(xiàn)類似這樣足夠吸引人、同質(zhì)化不高的作品?
繳蕊:在過(guò)去幾年里,還是有不少引發(fā)廣泛討論的作品。比如《初步舉證》在舞臺(tái)和影像之間展現(xiàn)了對(duì)女性處境的反思;《還有明天》同樣提供了激烈的社會(huì)批評(píng);中國(guó)電影里像《出走的決心》等作品,也有值得關(guān)注的實(shí)踐。不過(guò)我覺(jué)得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女性主義的表達(dá)已經(jīng)不僅僅依賴電影。它大量發(fā)生在社交媒體、播客、綜藝等多元場(chǎng)域中。現(xiàn)在感受到的“片荒”,一方面確實(shí)與全世界的電影產(chǎn)業(yè)和當(dāng)下思想文化的收緊、保守回潮有關(guān);另一方面,也可能意味著女性主義表達(dá)的重心在轉(zhuǎn)移。可以繼續(xù)回看我們今天介紹的香特爾·阿克曼等導(dǎo)演的作品,很多思想資源還遠(yuǎn)未被充分發(fā)掘。
吳伊瑤:其實(shí)當(dāng)下也有作品通過(guò)回望歷史來(lái)回應(yīng)當(dāng)下的問(wèn)題。比如改編自安妮·埃爾諾自傳小說(shuō)的電影,重現(xiàn)了她年輕時(shí)非法墮胎的經(jīng)歷,呈現(xiàn)出極具沖擊力的痛感。所謂“當(dāng)代性”并不只是發(fā)生在此刻的創(chuàng)作,而是體現(xiàn)在歷史問(wèn)題持續(xù)延伸到今天的反思與討論中。
繳蕊:是的,以美國(guó)的墮胎權(quán)為例,很多人覺(jué)得直到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被推翻時(shí)才引發(fā)危機(jī)感,其實(shí)在這之前,各州內(nèi)部的保守浪潮已經(jīng)涌動(dòng)。那幾年美國(guó)出現(xiàn)了大量重新追溯1970年代羅訴韋德案判例的作品,它們通過(guò)回望歷史來(lái)回應(yīng)當(dāng)下。很多時(shí)候,我們并不是單純研究一個(gè)“過(guò)去的事件”,而是借由對(duì)歷史的再闡釋來(lái)表達(dá)對(duì)當(dāng)下的關(guān)注。這種時(shí)間的回望,本身就是今天話語(yǔ)的一部分。
觀眾三:我是美術(shù)館的工作人員,所以比較關(guān)注影像作品的展示問(wèn)題。大多數(shù)電影我們?cè)谟霸骸㈦娨暬螂娔X上看,都是矩形的畫面。皮皮樂(lè)迪·里斯特逐漸嘗試打破這種固定的矩形框架,比如像這次展覽中的雙屏裝置,或者讓影像以蔓延的方式鋪展出來(lái)。我的問(wèn)題是:在電影史或影像史中,這種展示方式有沒(méi)有流變?
繳蕊:這是一個(gè)非常前沿的問(wèn)題,在學(xué)界常被稱為“銀幕/屏幕研究”(screen studies)。從膠片電影到電腦、手機(jī)到IMAX的巨大沉浸式銀幕,不同的介質(zhì)改變了影像的呈現(xiàn)方式。我記得自己在UCCA大展廳里看她的作品時(shí),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空間的巨大與開放性。其實(shí)電影也在不斷拓展類似的實(shí)驗(yàn)。比如現(xiàn)在的VR交互電影、像游戲一樣的分支敘事電影,這些探索都在說(shuō)明,突破矩形框架、拓展感知邊界,是影像藝術(shù)的內(nèi)在沖動(dòng)。我印象深刻的一個(gè)例子是讓-呂克·戈達(dá)爾在巴黎拉德芳斯(La Défense)辦過(guò)一個(gè)展覽,名字就叫《電影史》。他把原本的電影片段分散在不同的小房間里,用老舊的方形電視機(jī)播放,甚至保留雪花和模擬信號(hào)的質(zhì)感。觀眾可以自由穿梭、停留,體驗(yàn)到影像在不同介質(zhì)和空間中所帶來(lái)的獨(dú)特感官效果。這和今天皮皮樂(lè)迪·里斯特的展示邏輯有相通之處:都是把影像和空間、身體、感官結(jié)合起來(lái),讓觀眾參與到意義的生成中。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