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元1081年:絕對優勢的戰爭為何失敗?
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節目,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081年,大宋元豐四年,大遼大康七年。
這一年的8月6號,王韶去世了。
王韶是誰?他可是大宋朝歷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論文的,他是嘉祐二年的進士,中國科舉史上最厲害的一屆進士,和蘇軾、蘇轍、張載、程顥、曾鞏是同年;論武的,他以文人身份帶兵,為大宋朝開疆拓土兩千里,史稱“熙河開邊”。這可能是北宋歷史上最輝煌的一次軍事勝利。你要是感興趣,可以出門左轉,去看我們《文明之旅》1075年那一期。你想,這樣的文武兼修的傳奇經歷,在整個大宋朝歷史上恐怕也是獨一份兒。
今年,王韶去世。他留給世人的背影,還是挺耐人尋味的。
一方面,王韶官至樞密副使,這是宰相級別的官位了。這說明立下軍功的人,在當時還是挺受尊重的。但另一方面,他死的時候,身上長了惡瘡,爛了一個大洞,死得非常痛苦。有人就說了,這都是因為王韶這輩子帶兵打仗,殺的人太多啊,這回遭報應了吧?這句閑言碎語,居然被《宋史》記在了他的傳記里。
你看看,在大宋朝當個戰爭英雄真的挺難。大家既期待有人能給國家帶來輝煌的軍事勝利,但是,那種崇文抑武的價值觀又滲透進了整個社會的骨髓里,對于王韶這種在戰場上打生打死的人,會不自覺地流露出鄙薄和不屑。這心態是不是很扭曲?
王韶是死在洪州——就是今天的南昌——知州的任上的,距離開封很遠。他是不知道,就在他撒手塵寰的同時,大宋朝廷正在發動一場規模驚人的大戰爭,歷史上叫做五路伐夏戰爭。這幾乎是北宋開國以來,調動兵力最大的一次戰爭,光第一波開拔的士兵就有30萬人,這還不算負責后勤保障的老百姓。甚至就連后來北宋滅亡之前、跟金國的生死大戰,都沒調動到這么多的兵力。宋神宗這次是打算畢其功于一役,徹底滅掉西夏。
我在想,如果王韶臨死的時候知道朝廷的這個計劃,會不會贊同呢?兩種可能性都有。
一方面,王韶當年開邊熙河,目的可不是為了熙河那片地盤啊,而是為了把熙河當做跳板,為將來有朝一日滅掉西夏做準備啊。這不,短短幾年之后,當年自己種下的因,就要結出果了。所以,他有可能贊成。
但是另一方面,你看王韶帶兵的風格:在戰略上主打一個步步為營,不會動不動就直搗黃龍;在戰術上主打一個靈活機動,不會動不動就大決戰。所以,他也有可能不贊成宋神宗這么大動靜的五路伐夏。你看,我都替他糾結。
但是,如果王韶再多活幾個月,這些糾結就沒有必要了。因為五路伐夏失敗了。
一共五路兵馬,其中有三路,因為各種各樣的問題,早期雖然有點收獲,但最終都沒能進入主戰場。還剩下的兩路大軍,就是環慶路、涇原路兩路共十三萬人,會師在靈州城下。靈州在哪里?就是今天的寧夏吳忠市,距離當時西夏的首都興慶府,就是今天的寧夏首府銀川,只剩下100公里了。但是,就這座靈州城,宋軍圍攻了十八天,也沒拿下來。最后,西夏掘開黃河,水淹宋軍,又抄了糧道,宋軍不戰而潰,大敗而歸。

如果王韶還能再多活一年,到了下一年,1082年,他還能等到另一場更悲慘的失敗。
五路伐夏失敗之后,宋神宗改變策略,開始步步為營地筑城,這就是永樂城。但是沒想到,永樂城剛剛建成,西夏就組織了傾國之力的30萬人來反撲,結果,永樂城陷落。這一仗死了多少人,我看史料上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宋史》上的估計最多,有20多萬人慘死在城中。這是下一年,1082年10月11號的事兒。
消息傳到開封,神宗皇帝難過得飯都吃不下去,對著大臣,痛哭流涕。據說身體就從此垮了下來。
今天,我們就來復盤一下這場戰爭:一場看起來幾乎是穩操勝券的戰爭,怎么最后就落到了這個地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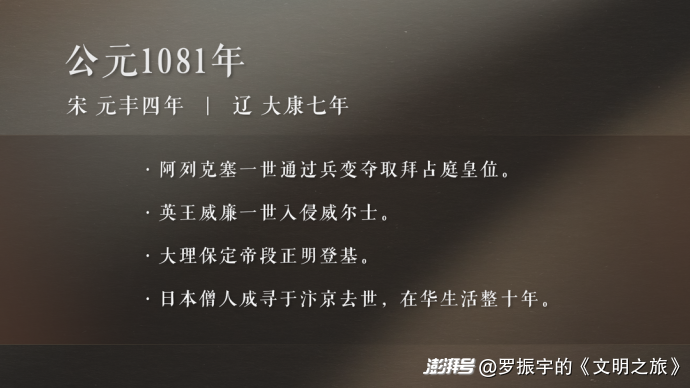
機不可失
看待歷史上的戰爭,我們得避免一種“事后諸葛亮”的傾向:不能看到宋朝在五路伐夏和永樂城之戰中大敗,所以就從戰略到戰術地把當事人數落一通,說大宋君臣這也不對,那也不對。
那我要問了:人家是傻子嗎?戰爭是一個巨大的賭臺。神宗押上去的,可是他們老趙家的江山社稷和他本人的政治威望;將士押上去的,更是自己的一條命。他們能比我們這些沒在宋朝生活過的、甚至壓根沒上過戰場的、袖手旁觀的人更輕率、更愚蠢嗎?
舉個例子,我看很多歷史研究者都在批評宋神宗,五路伐夏居然都沒有一個總指揮。這么大的軍事行動,都沒有最高統帥,軍令怎么統一?戰場怎么協同?這不胡鬧嗎?
這個指責聽著有理。但是你想,五路伐夏,指的不只是五路大軍,還真就是從大宋朝版圖上圍繞西夏的五個行政區,當時叫“路”:鄜延路、河東路、環慶路、涇原路、熙河路,從這五個大區分別出兵。你想,這可是綿延上千公里的戰線啊,每個戰區中間還隔著沙漠、高山,在那個通訊基本靠走、指揮基本靠吼的時代,即使有總指揮,又有什么用?

你可能又會說,那何必非要分五路呢?就不能集中兵力,一擊必中嗎?
集中力量,當然是一種策略,但是分進合擊也是一種有效策略啊。
你想,西夏的軍事優勢是什么?無非兩條:第一,對當地的地理更熟悉,第二,騎兵的機動性強。但是劣勢也很明顯:人口少啊。西夏的極限動員兵力大概是15萬人。如果宋朝只派一路大軍,西夏完全可以依托地形,以逸待勞。那宋朝的30萬對西夏的15萬,雖然有數量優勢,但仍然是勝負難料啊。
但是如果宋軍分五路分進合擊呢?西夏就不得不把15萬兵力拆成3-4萬的小股軍隊,分頭抵擋。宋軍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對方的機會就大大增了。
還有一點,在古代的軍事后勤條件下,30萬大軍,至少還要一比一配備相同數量的民夫,這可就是六十萬人了,擁擠在同一條進兵路線上,隊伍走不動、軍糧運不上來、被伏擊的風險大增。所以,集中兵力反而不是現實的選項。
又有人說了:五路伐夏的失敗,是因為后勤保障沒有跟上。是的,這次宋軍的后勤確實拉胯。畢竟這次戰爭動員超過了30萬軍隊,規模太大了,超過了那個時代的軍事后勤技術的極限。
你可能會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是常識啊。既然沒有準備好后勤,為啥還要匆忙出兵呢?
首先,這次不是邊境上的攻防戰,宋軍的戰略目標是徹底消滅西夏,只要打到了寧夏平原,那可是塞上江南,是產糧區,只要到了那里,完全就可以因糧于敵、以戰養戰了。
更重要的是,發動戰爭,是有最佳時間窗口的。宋神宗為什么要選擇在這個時候匆忙出兵、發動大戰?因為西夏出事了啊。
這個時候的西夏皇帝是夏惠宗李秉常,李元昊的孫子,才二十出頭,比宋神宗還年輕。但這位李秉常就是個傀儡,西夏的實權掌握在他媽媽梁太后手里。而就在今年,梁太后居然又發動了一場政變,把李秉常給關起來了。
這么一鬧,對大宋朝來說,就出現了兩個機會:第一是西夏國內亂套了。下面的那些部落酋長分成了三派,有的支持皇帝李秉常,有的支持梁太后,還有的觀望,甚至想找機會看看能不能投靠大宋這邊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機會是:皇太后把李秉常給綁架了,這就給了宋朝討伐西夏的口實啊:畢竟,西夏這個時候表面還是對大宋稱臣的,李秉常是我大宋皇帝的臣子,怎么的?你欺負我的臣子?那就不要怪我動手打你哦。這叫師出有名。
宋神宗那么快地決定五路伐夏,要一鼓作氣滅掉西夏,就是出于對戰機的判斷。要是等后勤工作完全準備好了,這個機會可能也就消失了。所以,國家統帥難啊,他往往必須在軍隊準備度和稍縱即逝的戰機之間,做出高難度的取舍。是的,哪有那么多萬能的勝利公式?戰爭往往就在于在“不確定性”中抓住稍縱即逝的戰機,而不是在“確定性”中等待完美條件的出現。
對宋神宗這次戰爭的決策,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批評,比如用人不當,任用宦官當統帥,任用不懂軍事的文人徐禧來決策修建永樂城等等。這就更是事后諸葛亮了。用宦官當統帥咋就不行?至少這次熙河路的統帥李憲,軍事才能是不錯的,也算是北宋的名將之一。用文人當統帥咋就不行?范仲淹、韓琦、還有我們前面說的王韶,不都是文人統兵嗎?不也都是一段佳話嗎?
談論歷史,咱們不能動不動就先開個上帝視角,然后來評判歷史人物的是非對錯。身在歷史現場的人,必然是在信息不足的條件下,要做性命攸關的抉擇的。你看這句克勞塞威茨《戰爭論》里的名言嘛:“戰爭帶有太多的不確定性,采取軍事行動的理由往往四分之三都隱藏在帶有或多或少不確定性的濃霧中。”
如果你切換到宋神宗的視角,這一仗也是大概率要打的。
神宗皇帝20歲登基,雄姿英發,一生的抱負就是要恢復中原帝國的“漢唐舊疆”。幽云十六州,在大遼手里,暫時沒能力,再說。但是小小的西夏,我總得先滅了吧?好歹啟動個進度條啊。所以,在宋神宗的計劃表里,滅西夏,沒有要不要打的問題,只有什么時機打的問題。否則,他為什么要支持王安石搞變法呢?不就是為了富國強兵嗎?
是的,其實這場仗早就開始準備了。
話說九年前,1072熙寧五年的時候,當時王韶的熙河開邊剛有成效,王安石和神宗就商量,要不要一鼓作氣滅掉西夏。王安石說,機不可失。神宗捧哏說,對,確實不可失。軍人在靶場上有一句話:“有意瞄準,無意擊發”。意思是,瞄準要非常用心,但是什么時候這一槍打出去,那就要看機緣了。時機一到,不用多想,反正已經瞄準了多時了,只管扣動扳機。宋神宗從1072年開始,動了要滅西夏的念頭,這都忍到1081年了,瞄準九年了,突然聽到西夏國內亂的消息,你說他還忍不忍得了?
這些年,準備也確實一直在做。
首先是錢。王安石變法即使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成果還是很顯著的,國庫里的真金白銀確實一直在增長。有個說法,宋神宗死的時候,國庫里的現金就夠大宋朝用上20年。打仗就是打錢啊,大宋朝這個時候確實有本錢打一場大仗。
然后是兵器。這個時候的大宋,軍事裝備的水平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床弩射程能達到1500米,神臂弓240步,(將近400米)的射程,而且只需要一個人就能操作。火藥武器就有十幾種:火箭、火炮、霹靂火球,等等等等。
再然后是軍隊的組織能力。經過和西夏的長期對峙,大宋朝的西軍,其實已經非常強了。甚至到了后來南宋的時候,在這次西夏戰場上練出來的西軍,也仍然還是朝廷的主力。更何況,前些年的熙河開邊,也給了大宋軍隊注入了信心和士氣。對,失敗才不是勝利之母呢,勝利才是勝利之母。贏過的軍隊才更有膽氣贏下一場。再加上這幾年在軍隊里搞的“將兵法”的改革,這時候的宋朝軍隊的戰斗力已經今非昔比了。
這個時候,你要是宋神宗,會不會趁著西夏內亂的機會發動決戰呢?你拿出一張紙,把雙方的優勢劣勢都擺一擺嘛,你會發現贏面兒實在是太大了,沒有不動的理由啊。至于后勤方面,可能確實有漏洞。但沒關系啊,沒準大軍一到,西夏內部就土崩瓦解、望風而降了呢。到那時候,后勤問題不也就不存在了嗎?
你看,在這個重大決策的關頭,宋神宗只不過是做了一個心智正常的人都可能會做的決定。換了你我在現場,也未必能做出更高明的選擇。
好了,為神宗皇帝開脫了這么多,但是有一點還是不得不承認的:就是在打仗的過程中,宋神宗確實有亂指揮的問題。
我們以前就講過,他有一個習慣,喜歡在深宮之中,通過往外批各種小紙條來指揮政務運行,甚至是直接指揮軍隊。朝廷有宰相,有專門管理軍務的樞密院,神宗一概繞過,直接下密詔給前線軍官。沈括,就是那本《夢溪筆談》的作者,曾經擔任過邊境的軍事長官,任職時間總共還不到一年半,就收到了273封來自神宗皇帝的密詔。你就想想,這位皇帝對親自指揮這件事熱愛到什么程度?
好,問題來了:五路伐夏和永樂城的戰敗,是不是就是因為神宗的這種瞎指揮的作風導致的?還真不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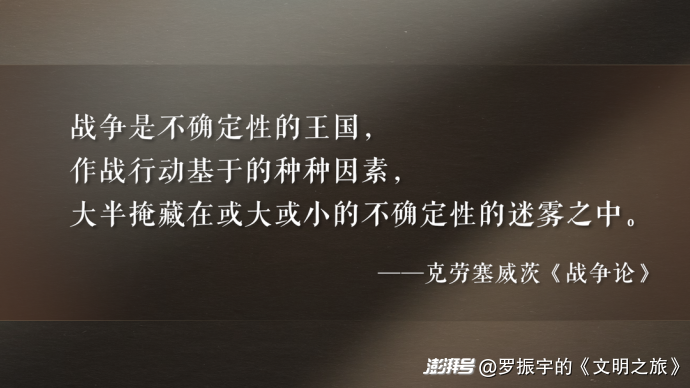
將從中御
宋神宗為什么要直接指揮前線軍官?
這是他們老趙家皇帝的傳統。打仗的時候,如果自己不能親上前線,那往往也會給一大堆指示,甚至干脆給一張陣圖:按我的方法打,不許自作主張。這還有個專有名詞,叫“將從中御”,將領的行動需要皇帝在宮中駕馭。你說什么?“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誰說的?軍人手里握的,可都是兇器,我當皇帝的不管著點兒行嗎?
宋朝脫胎于五代那個大亂世,皇帝對武裝力量的危害性有非常深刻的認識,或者說有“創傷記憶”,那是真不放心啊。可以理解。
但問題是,你指揮得了嗎?太祖太宗好歹還上過戰場,宋朝后來的這些皇帝都是在深宮里長大的,完全沒有軍事經驗,他做的軍事決策的質量能高到哪里去?
好,我就算你宋神宗是天縱奇才,武曲星下凡,但你人在開封城,軍隊遠在今天的陜西、甘肅、寧夏,在當時的通訊技術條件下,你怎么遙控指揮呢?
根據方震華老師的這本書《和戰之間的兩難》提供的資料,宋仁宗的時候,從陜西前線快馬加鞭送一封軍報到開封,需要九天。這個速度已經很快了。到了宋神宗的時候,這個速度又提了一次,可以六天送到。但是請注意:陜西可是距離開封最近的軍事前線,如果再遠,時間就沒法控制得這么好了。比如前些年,大宋和交趾開戰,紙面計算,開封到前線的軍報應該十七天送到,但實際上,山遙水遠的,各種不確定性累加在一起,30天也做不到。
你想,那可是打仗啊,戰場信息瞬息萬變。發現軍情,送到開封,等皇帝決策了,再把命令傳回前線,至少十幾天過去了,軍隊難道站著不動等圣旨?如果真要是這樣,別說打勝仗了,什么軍隊也都會葬送得干干凈凈。
就拿下一年發生的永樂城之戰來說。宋軍把城筑好,是明年9月初的事兒,9月9號,西夏大軍就來了。七天之后,9月16,神宗才得到消息,趕緊調兵遣將去救援。估計神宗也是覺得來不及,兩天后又下令守軍棄城,趕緊突圍。但是,永樂城在20號就陷落了。整個戰斗歷時11天。神宗雖然也是一通忙活,但他的圣旨對戰場形勢的發展,沒有一絲一毫的影響。
有意思的事情來了:理論上,宋神宗追求“將從中御”,皇帝指揮一切,他也是這么干的,但現實情況是,皇帝對戰事的影響,其實并不大。這就造成了一種非常有意思的情況:皇帝覺得自己是在指揮,前線將領也讓他這么覺得,但事實往往是,前線將領是先做了決定,皇帝只是事后在追認。
舉個例子。今年五路伐夏,種諤率領的鄜延路大軍,出兵之后立刻圍攻米脂,在今天陜西榆林市的一個軍事要地。神宗接到軍報之后,就直搖頭,拿起筆來寫圣旨,不對不對,用兵之法,要避實擊虛嘛,你攻打城池,萬一損兵折將,摧折士氣,就不好了呀!寫好、封口、發走!還是我高明。
可是沒過多長時間,軍報又來了,說種諤圍攻米脂,圍點打援,大破西夏援軍。神宗立刻喜滋滋了,又拿起筆來寫圣旨給種諤:我原來是擔心你急躁了,所以勸你來著,還讓你聽王中正,一個宦官的指揮,現在看,你很棒嘛,功勞很大嘛,得了,你以后不必聽王中正指揮了。
你就看這一個來回,種諤是自己打自己的,神宗也是自己指揮自己的,誰都沒耽誤,但是總體上也確實是“將從中御”了。這樣的例子,在五路伐夏的戰場上到處都是。這個狀態,讓我想起來一個場景:有個小孩,特別愛玩指揮樂隊的游戲,樂隊也愿意配合他。你要是看他們的演出,小孩有模有樣地揮動著指揮棒,確實像是現場的核心。但實際上呢?是樂隊在自主演奏,反而是小孩在跟節奏。

有時候,神宗皇帝的指示特別具體,前線將軍既無法執行,又不敢不聽,所以就發明了各種對付的辦法。比如,五路伐夏出兵之前一個月,神宗給前線部隊頒布了一套行軍打仗的陣法。神宗特別愛琢磨這些事,這套陣法應該就是他搞的發明創造。前線統帥高遵裕就說,呀,朝廷發給我的這陣圖陣法,我雖然研究了,但我還是擔心我領會領導意圖不夠深入,這樣行不行?朝廷再派一個深通這套陣法的人來前線指導工作唄?方便我有不懂的地方,隨時請教。你聽這話說的,既拖延了執行的時間,又把不執行指示的鍋甩得干干凈凈。
我自己看這段時間史料,有一個強烈的感覺:神宗皇帝在深宮之中,盡享那種“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快感。但無論是他自己,還是前線的將領,都沒有特別當真。有的時候,神宗皇帝有突發奇想,圣旨就發出去了,但是具體執行不執行,其實他也沒有那么當真。
比如,大戰之前的兩個月,神宗突然指示熙河路的主帥李憲,說你那個地方不正好在黃河上游嗎?那咱們為啥不打造一支水軍呢?運兵運糧,甚至可以搞火攻啊。甚至連哪兒砍木材,哪兒招募工匠,都幫李憲想好了。指示得特別具體。
但是你懂的,在當時大宋朝的西北邊疆,從來沒有操練水軍的傳統,只剩兩個月時間,要造船,要訓練,怎么可能?這只能是不切實際的突發奇想。但是好在,神宗皇帝也就是這么一說,后來大家黑不提白不提,就權當沒有這回事了。
我看有的書上說,神宗皇帝自從永樂城陷落之后,心神被重創,從此再也沒有發動大戰了。這個說法其實不太準確。仗確實是沒有打了,但是神宗皇帝至死都是一個沖動型選手,腦子里經常會蹦出來各種奇思妙想。
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就是元豐七年的時候,他還寫條子跟熙河路的李憲商量呢。咱們搞一次奇襲好不好?派一支人馬,在蘭州架浮橋,精兵過河,從上游突襲,直取西夏的首都。你看這話說的,“以本路預集選士健騎數萬人,一發前去,蕩除梟穴,縱不能擒戮大憝,亦足以殘破其國,使終不能自立。”你聽聽這話的氣勢。后面還加了幾句,就是當年西晉滅東吳,隋朝滅陳,曹彬滅南唐,用的都是這個方法!這個方法好啊!當然了,這個事兒還是沒有下文,也幸好沒有下文。
你應該感覺出來了:將領的心態是,只要皇帝您高興,您就玩,我們盡量配合。而神宗的心態是:我比你們都懂,我給你們出主意,如果有用,那不挺好嗎?我至少要讓你們知道,指揮權還是在我手里,你們在千里之外的一舉一動,老大哥都盯著呢。有這個感覺就行啊。
但實話實說,神宗皇帝還是一個非常明智的人,他雖然勤于指揮,勇于發言,但是我在史料中從來也沒有看到過,他特別蠻橫地下命令一定要怎樣怎樣,不聽我的我就要把你怎樣怎樣。沒有。他對戰場變化是有敬畏的,對前方將領見機行事的權力,是有基本尊重的。
還是回到五路伐夏和永樂城之戰:如果說這場戰爭失敗,就是因為神宗瞎指揮,其實有點夸大了。空間距離太遠了,皇帝對戰場的影響,有,但是很小。
我說到現在,你可能有點困惑了:這期節目,難道就是替神宗皇帝洗地?不怪他,那你說,五路伐夏和永樂城之敗,到底怪誰?
問得好。這就是我今天特別想表達的了:觀察一個歷史現象,如果我們非要用因果思維來分析,非要找出一個單一的原因,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就拿這場戰敗來說,你可以拿出一張紙來,在上面列原因:后勤問題、情報問題、用人問題、瞎指揮問題、組織問題、訓練問題、裝備問題,從前線將領到后方皇帝,所有地方全有問題。當然,你還可以把這張紙反過來寫,西夏那邊要是總結為什么贏,也可以寫一長串原因:皇太后英明、將士用命、堅壁清野這招好使,等等。
你會發現,用簡單的因果關系來分析世界,容易讓我們陷入原因的汪洋大海,或者是陷入一種荒謬的獨斷論。就像我們經常看到的那種文章標題:“因為老師當年的一句話,20年后他當上了院士”、“就這三招,他賺到了人生第一個一百萬”、“飯后百步走、活到99”,等等。我們的周邊充滿了這種以偏概全的話語。
但是沒辦法。人類的大腦天然偏愛這樣的表達。比如說,我們喜歡這樣的句子:“一只南美洲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兩周以后引起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哇,好神奇的因果關系。但是,你只要跳出來一想就知道,這場龍卷風,不可能只是因為那一只蝴蝶。世上的所有蝴蝶、所有的昆蟲、所有的活物、所有的山川河流、所有的長天大地,甚至來自遙遠星系的一次電磁輻射,都有可能是它的原因。那么請問,到底哪個是最重要的原因?你會發現,在線性因果關系的思維下,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在哲學上,反省因果關系是不是客觀存在,是一個非常悠久的傳統。如果你感興趣,可以去讀英國哲學家休謨的這本書《人類理解研究》。我們這里就不展開了。
但是,如果凡事不能歸因,你可能會覺得憋得慌:那人類還怎么思考呢?又怎么能進步呢?
那就還讓我們回到1081年,元豐四年的宋夏戰場上,我們來看看,人類的失誤和進步究竟是怎么發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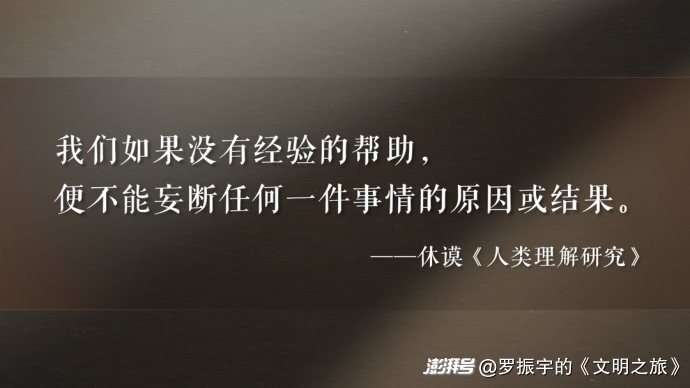
魔鬼在現場
我們都知道,宋朝是一個崇文抑武的時代。這不僅體現在對武將的防范、對文人士大夫的尊崇上,它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后果,那就是過于相信人類理性的力量。
比如前幾年,朝廷要改進兵器的制造。負責的文官就上書說了這么一段話:原來呢,造兵器總是要去征詢那些軍人的意見,兵器是造給他們用的嘛。聽起來合理,其實不然。那些武夫啊,見識太差了,固執,什么都不愿意改,所以啥都搞不成。現在,朝廷派我去管兵器制造,是因為我會打仗,擅長造東西嗎?不是啊,是因為我能洞察事物的原理啊,我有學問啊。說白了,造武器這個事兒,雖然是打仗用的,但是反而得聽我們文臣的。
說得有道理啊。他確實在這個崗位上干得有聲有色,統一了武器的制式,提高了武器的性能。這不挺好的嗎?
但是,這次宋夏大戰慘敗,事后總結經驗,前線將帥就提出來說,那些兵器的性能參數確實很高,但是粗大笨重啊,稍微弱一點的軍人根本就拉不開弓弩。這是這次失敗的重要原因。你看,理論上的強和實際戰場上的好用,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這種事情在戰爭史上是反復發生的。比如,我們以前經常說,在解放戰爭中,解放軍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擁有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意思是以弱勝強。
但事實恐怕沒這么簡單。陳毅元帥就說過,美式裝備的好處很明顯,火力很強。但除此之外就都是缺點了。比如:第一條,美式裝備結構比較復雜,對士兵的文化素質要求高。你想,當時的國民黨士兵基本都是文盲半文盲,訓練時間又短,復雜的裝備反而裹亂;第二條,消耗彈藥太多,這是需要龐大財力撐腰的,當時國民黨軍隊也不具備;第三條,需要先進的運輸系統配合,不然彈藥就供應不上。你想想當時中國的交通基礎設施的狀態,給美式裝備拖后腿啊。
所以你看,在理論世界用線性因果關系推導出來的結論,無論看起來多么的優美、完備、絲絲入扣、無懈可擊,你都要把它放回到現實世界,再去接受無數的、復雜的、其他維度的因素的考驗之后,我們才能知道它是不是立得住。是的。很多慘痛的失敗,不是因為最初的設想錯了、推導的邏輯錯了,而是因為現實世界里有許多該死的、意外的“摩擦力”。
在1081年的宋夏大戰的戰場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比如,有一路大軍,后勤糧草本來是夠的,但是管后勤的人沒有經驗,運糧用的牲畜是驢。驢比較難管,放在隊伍前面吧,亂哄哄,阻礙部隊前進,放后面吧,還得派人護送。事后總結,這也是重要的失敗原因。
再比如,為什么13萬大軍圍攻靈州城18天,也沒拿下來?說起來你可能不信,因為攻城部隊沒帶攻城器械。也難怪,這個時候的宋軍已經90多年沒有打過硬碰硬的攻城戰了,沒有經驗嘛。還記得前面說的,宋神宗聽說種諤要攻城,就急眼了嗎?上上下下是知道自己這邊的弱點的。你可能說,大部隊行動,不帶攻城器械很正常,就地造嘛。但是等到了靈州城下,發現軍中就沒有會造器械的工匠,更要命的是:靈州城下壓根就沒有粗大的樹木,有工匠也沒用。所以,這場所謂的攻城戰,根本就沒有什么搭云梯、滾木礌石、箭如雨下那些場景。宋軍這邊喊,你們怎么不快快投降。城上的西夏軍說,啊?投降?為什么啊?我們既沒有反叛朝廷,又沒有跟你打仗,對啊,你們沒有攻城器械,根本就沒有打嘛,投什么降?你說氣人不氣人?
再比如說下一年的永樂城之敗,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缺水。有史料說,有一半的士兵是渴死的。所以我看很多人說,都賴決定在這個地方選址筑城的徐禧。他是一個文人,怎么懂打仗?哎,在缺水源的地方筑城,蠢哪。
其實這么說有欠公道。
你想,這是在大西北沙漠的邊緣地帶筑城,本來就缺水,建城選址當然是要在河邊。但是,在夏天的豐水期,河水是要漲的啊。為了防止城池被河水泡壞,筑城的地點通常不會緊靠河流,要稍稍隔一點距離。那一旦城池被圍,不就斷水了嗎?所以又會建一個專門用于保衛水源的 “水寨”。這是當時常用的辦法。
但是,永樂城剛建成,西夏軍隊就過來了,很多建城的民工還沒有走,這些人要進水寨避難,守水寨的軍人一看,嚄!這么多人,進來得吃我多少軍糧啊?不能放進來。那民工能干嗎?我們得進城避難啊。他們手里還有工具,于是就開始挖墻。跟在民工后面的西夏軍隊等于是撿了個便宜,順勢就把水寨給奪了。
所以你看,永樂城缺水,不假,但這不是因為文人徐禧愚蠢,而是因為戰場上的一個偶然的變量,讓原來的規劃突然失效了。要命的是,戰場上的這類偶然因素,永遠會有,永遠也消除不掉。
那怎么辦呢?難道就任由這種偶然性作祟,人類就什么規劃都不做了嗎?什么都干不成了嗎?
那倒不是。
看到這一點,無非就是提醒我們:要學會把現實世界的多元性、豐富性、偶然性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智謀、理性、邏輯放在相對謙卑位置。不要搞什么畢其功于一役;不要動不動就發個狠、一把梭哈,富貴險中求;不要覺得我的計劃既然周全完備,那結果就一定萬無一失。
如果你目標是確定的,策略也是清晰的,那就盯死目標,日拱一卒,用長時間的耐力兼容掉現實世界里的那些從斜刺里殺出來的偶然因素。
大事往往都是這么辦成的。回過頭看,那些偶然因素不是沒有來過,而是跟你的長時段堅持相比,它潮漲潮落,風過無痕而已。
就拿宋夏戰爭來說,1081元豐四年的這場失敗,拉長了時段來看,不過就是一個小挫折,它一點也沒有改變宋夏雙方此消彼長的戰略態勢。到了后來的宋哲宗時期,勝利的天平繼續向宋朝這邊傾斜。1081年戰場上的那些偶然性因素,大宋軍隊也漸漸找到了預防和破解的辦法。如果不是后來金朝的突然崛起,大宋滅掉西夏,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最后,說一個笑話吧。
有位同學是樂隊里吹單簧管的。他們參加學校樂團排練的時候,用的都是以前學長們留下的樂譜,他就發現這些樂譜的某些段落上標著兩個字:“低頭”。這是啥意思呢?音樂里沒有這個符號啊。他請教了很多音樂老師,大家也都不知道這個符號是什么意思。
等第一次演出的時候,他就懂了。
原來演奏到那個位置的時候,如果不低頭,在他后面的長號,就會狠狠戳他一下腦袋。下回,他就知道了,這是真的要在現實世界里低下一頭,而不是老在純粹的音樂世界里琢磨這是什么音符。
對,這也是我們從1081年的這場失敗的戰爭中看到的教訓:理念世界固然美麗,但它也不過就是浸泡在無遠弗屆的廣大現實世界里的一座小島。
我們下一年,公元1082年,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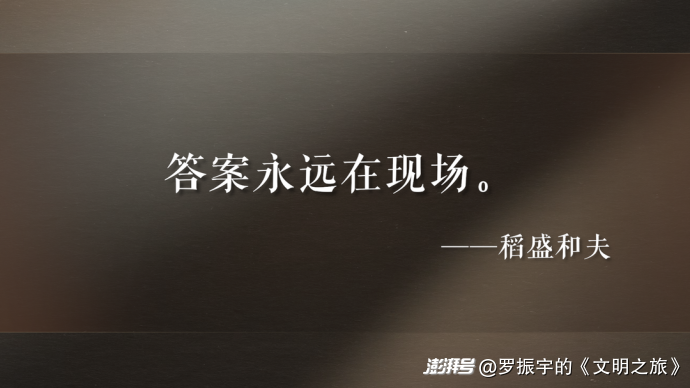
致敬
本期節目,我們講的是宋神宗五路伐夏的失敗。我們反對的是凡事都要找個簡單的因果關系,凡事都要強行解釋個為什么。有一本書,是朱迪亞·珀爾寫的《為什么》,副標題是《關于因果關系的新科學》。
里面有個段落很有趣:
在第100次讀《創世記》時,我注意到了一個多年來一直被忽略的細節。上帝發現亞當躲在花園里,便問他:“我禁止你碰那棵樹,你是不是偷吃了它的果子?”亞當答道:“你所賜給我的與我做伴的女人,她給了我樹上的果子,我就吃了。”“你都做了什么?”上帝問夏娃。夏娃答道:“那蛇欺騙了我,我就吃了。”眾所周知,這種推卸責任的伎倆對全知全能的上帝不起作用,因此他們被逐出了伊甸園。但這里有一點是我以前一直忽略的:上帝問的是“什么”,他們回答的卻是“為什么”。上帝詢問事實,他們回答理由。而且,兩人都深信,列舉原因可以以某種方式美化他們的行為。他們是從哪里得到這樣的想法的?
你看,真正重要的,只是是什么,是事實本身,是人類為了強行解釋,有時候甚至只是為了推脫責任,才說出了那么多為什么。
有時候,我們只是冷冷地看著事實,任由事實在復雜的因果中糾纏翻滾,這就已經是最好的思考。向古往今來所有冷峻地盯著事實本身,不匆忙地得出因果的智者致敬。
參考文獻
(宋)李燾 撰:《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
(元)脫脫等 撰:《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
(德)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戰爭論》,時殷弘譯,商務印書館,2022年。
(英)大衛·休謨:《人類理解研究》,關文運譯,商務印書館,1957年。
雷家圣:《宋神宗的軍事改革與對夏經略研究》,花木蘭文化實業有限公司,2024 年。
方震華:《和戰之間的兩難:北宋中后期的軍政與對遼夏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
王曾瑜:《宋朝軍制初探(增訂本)》,中華書局,2011年。
李華瑞:《宋夏關系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方震華:《將從中御的困境——軍情傳遞與北宋神宗的軍事指揮》,《臺大歷史學報》2020 年第 65 期。
林鵠:《從熙河大捷到永樂慘敗——宋神宗對夏軍事策略之檢討》,《軍事歷史研究》2019 年第 2 期。
方震華:《戰爭與政爭的糾葛—北宋永樂城之役的紀事》,《漢學研究》2011年第29卷3期。
田志光:《宋太宗朝“將從中御”政策施行考——以宋遼、宋夏間著名戰役為例》,《軍事歷史研究》,2011 年第2期。
范學輝:《宋人本朝軍政體制論爭試探》,《文史哲》2007年第4期。
范學輝:《“將從中御”始于宋太祖考》,《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李蔚:《略論北宋初期的宋夏靈州之戰》,《寧夏社會科學》1992年第6期。
趙滌賢:《北宋元豐靈州永樂兩次戰役宋軍死者人數考》,《學術月刊》1994年第6期。
孫方圓:《宋夏戰爭中宋軍對飲用水的認知與利用》,《史學月刊》2019年第2期。
楊樹:《解放戰爭是小米加步槍打敗美式裝備?美國貨其實沒那么神》,https://mp.weixin.qq.com/s/E4_0x6Edw-2T2KEhfs60iA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