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澎湃思想周報|硅谷的戰爭牟利者;屏幕革命與全球民粹的崛起
硅谷的戰爭牟利者
在多年夸大外國威脅、渲染全球沖突風險之后,硅谷的軍事初創公司終于迎來了屬于它們的“戰利品”——來自五角大樓的數十億美元投資。這些公司將從近一萬億美元的國防預算中分得巨額撥款,用于研發無人機和人工智能武器系統。美國國會的兩院——眾議院與參議院——已分別通過法案,要求五角大樓進一步加碼人工智能研發,并在軍隊內部“最大化作戰者殺傷力”。換句話說,人工智能不再是科技公司用來描繪未來的噱頭,而是被正式納入戰爭機器,用來提升致命效率。

當地時間2025年9月20日,美國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美國國防部總部五角大樓的航拍圖。
據路透社報道,今年以來,美國股市中表現最搶眼的不是傳統軍工巨頭,而是一批規模較小、專注于“新一代戰場技術”的防務公司。它們依靠低成本、可快速升級、適應現代戰爭需求的技術路線,在華爾街吸引了大量資金流入;而五角大樓正將重點從龐大復雜的傳統武器系統,轉向更敏捷、可快速部署的系統,這進一步推動了這類企業股價飆升。
俄烏與加沙戰爭推動了全球軍費增加,也令投資人將目光轉向能快速生產人工智能驅動無人機、無人車輛等系統的公司。這些裝備相對便宜、不依賴大規模地面部隊,并符合“低成本消耗型”戰爭趨勢。
《雅各賓》雜志轉載了調查媒體The lever的一篇報道(作者Freddy Brewster和Luke Goldstein),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度分析。硅谷的軍工初創公司——那些制造高端殺傷與監控設備的企業——在過去幾年一直積極推動“外部威脅”敘事:他們聲稱,美國面臨來自一些國家的高科技軍事挑戰,而只有最先進的無人機、人工智能與監控系統才能確保“國家安全”。政策研究者指出,這種論調往往將復雜的地緣政治問題簡化為“技術競賽”,從而正當化更多的軍費支出。
如今,這場由恐懼推動的敘事,終于結出了金錢的果實。根據最新的《2026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眾議院已批準至少47億美元用于無人機、人工智能與量子計算投資。參議院版本更慷慨,將這一數字提升至56億美元。兩院仍需協調,但無論結果如何,這意味著自主武器系統首次被單獨列入國防預算科目,象征著一個新的軍工黃金時代。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正削減醫療補助與食品援助等社會項目。然而,受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仍大幅擴充五角大樓預算,把更多公共資金投向硅谷的軍工合作伙伴。
推動這一預算浪潮的,不僅是軍方本身,還有龐大的商業聯盟。在無人機與AI產業背后,站著的是國際無人駕駛系統協會(Association for Uncrewed Vehicle Systems International, AUVSI)——一個強大的游說團體。該組織的成員名單讀起來像美國科技與軍工復合體的縮影:亞馬遜、波音(老牌軍機與商用飛機制造商)、霍尼韋爾(為軍工與工業提供傳感器與控制系統的供應商)、洛克希德·馬丁(全球最大軍工承包商)、RTX(前雷神,主要生產導彈和防空系統)等巨頭,以及與特朗普家族關系密切的企業。
特朗普本人也為這場軍事科技盛宴加了“催化劑”。他在7月4日簽署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中,為無人機行業額外撥出80億美元合同,并為反無人機技術增加13億美元預算。這不僅是一筆金錢的注入,更是一種政治信號。
風險投資機構同樣躍躍欲試。安德森·霍洛維茨(Andreessen Horowitz)、創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與Lux Capital等風投巨頭,已將資金源源不斷地投入軍工企業。它們支持的公司包括:導彈與無人機制造商Anduril、太空探索初創Varda、超音速飛機制造商Hermeus,以及由特朗普盟友、共和黨金主彼得·蒂爾(Peter Thiel)創辦的Palantir,這家公司專門為軍方提供人工智能分析與“戰場決策支持”。
這些公司與五角大樓之間,已經形成一條互相喂養的資金回路,即軍方通過合同支出維系企業,而企業再通過政治游說與媒體敘事影響國防政策。最近一系列聯邦行動,也為AI與無人機產業清除了障礙。今年1月,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取消對人工智能企業的部分監管與倫理限制,并推出所謂《AI行動計劃》,幾乎完全照搬了行業游說清單。
緊接著,6月的一道行政令“釋放美國無人機主導力”進一步放松空域管理、刺激無人機制造。而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則命令五角大樓撤銷更多生產限制,并成立跨機構工作組,以簡化無人機采購流程。這里的“跨機構”指軍方、國家安全機構與私營承包商共同參與的一種組織結構。這種結構常被批評為模糊了“公權力”與“企業利益”的界限。
這些行政命令發布后,無人機制造商股價迅速上漲,私人投資也隨之涌入。政策專家指出,華盛頓幾乎沒有對這些高科技系統的“必要性”或“有效性”提出任何質疑。正如長期研究五角大樓合同的學者比爾·哈通(Bill Hartung)所說:“只要承包商提到‘無人飛行器’,五角大樓就會立刻給他們開一張巨額支票。任何批評聲音一出現,硅谷的回應永遠是——‘我們必須打敗對手。’這就成了一個結束對話的方式。”
國防法案不僅是預算分配文件,也是在為未來的戰爭模式定方向。它明確要求五角大樓在更多日常軍事任務中使用人工智能,包括讓AI參與戰機與無人機的飛行操作,并協助飛行員決策(并非完全自動殺人機器,而是輔助人類控制)。參議院版本進一步要求AI深入軍方的網絡安全、后勤等各個運作環節,并構建能夠“一人同時操控多套無人系統”的作戰結構,以提高效率與殺傷力。這意味著各種無人武器必須可以互通協作,而不是各自為政。
不過,法案也承認風險:如果自主或半自主武器快速上陣,可能會削弱“人類必須授權每一次殺傷”的原則。因此軍方必須說明如何確保“AI不會在無人監督下自行開火”。與此同時,法案也希望將AI用于監視偵察與信息處理,但已有跡象顯示軍方過快引入大型語言模型等工具,可能產生網絡安全漏洞或倫理風險(例如誤導決策、數據泄露等)。
為了支撐這一切,法案推動放松AI數據中心的監管,并支持用“小型核反應堆”(small modular reactors)為其供能——這是硅谷科技公司多年來積極游說的訴求。文章還指出,國防部本身就是全美最大的能源消耗機構之一,而AI計算將進一步推高用電與冷卻成本。
無人機領域范圍很廣:有遠程操控的民用機、由人工智能自動飛行的系統,以及用于攔截無人機的“反無人機系統”。近兩年風投向這個行業投入很多錢,但市場競爭激烈,客戶主要是軍方,很多初創公司還沒真正賺錢,因此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的大合同上。
新法案鼓勵大量采購小型、低成本無人機,并建議把這類輕型無人機當作“消耗品”(consumable commodities,類似彈藥)來買,這意味著可以更快、從更多供應商處購買,審批更簡便。問題是,國防部到現在還沒有配套的作戰指南、訓練標準或專門的崗位設置,也就是沒有說明這些無人機該怎么用,誰來操作,如何訓練。這就可能出現:設備先大量進軍隊,使用規范、訓練和法律倫理討論卻跟不上,從而增加誤用或事故風險。
為爭取更多公共撥款,行業利益相關者頻繁出現在國會聽證會與媒體上,警示來自外國的無人機威脅。自今年4月以來,國會就無人機技術與國家安全問題召開了多場聽證會,出席者多為行業代表與軍事鷹派,而能批判性反駁其論點的獨立專家很少受邀。
在若干聽證會與公開聲明中,有關方面提出了許多聳人聽聞的說法。例如,國際無人駕駛系統協會的負責人在國會證詞中宣稱,在2024年7月針對特朗普的未遂刺殺事件中“甚至使用了一架中國制造的無人機”。這里的說法基于媒體當時關于刺客在事發前可能使用無人機偵察現場的報道,但顯然不能直接把這歸咎于某個國家。
更普遍的問題是:盡管反復有關于外國無人機在美從事間諜或竊密活動的警告,一些獨立審計與研究并未找到明確證據支持這些指控。比如,美國國家海洋與大氣管理局(NOAA)的一份報告指出,多數商用無人機型號不太可能將數據遠程回傳至海外對手,即對手通過商用無人機竊取情報的可能性較低。管理咨詢公司博思艾倫漢密爾頓(Booz Allen Hamilton)針對類似問題的分析也得出相近結論。
長期關注美國國防政策的批評者指出,關于無人機戰爭的許多說法其實被嚴重夸大。雖然中國在無人機產量上確實遠遠領先美國,占據全球約80%的生產份額,但一些專家質疑:這是否就意味著美國納稅人的預算應立刻優先大量投向這一領域?
哈通(Bill Hartung,美國知名軍費與軍工研究專家)指出:“我們聽到很多帶有絕對性的說法,例如誰先把人工智能全面應用到武器上,誰就會主宰未來,好像這是一場只有一個終點的競賽。這聽起來就像(某些科技領袖在說):‘我是技術天才,信我就對了。’”
民粹主義、屏幕革命與后讀寫社會
本月初,因提出“歷史終結論”而聞名的日裔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在線雜志《勸說》(Persuasion)撰文,指出在引發全球民粹主義浪潮的眾多因素中,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興起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這篇題為“是互聯網,笨蛋們”(It's the Internet, Stupid)的專欄文章中,福山首先列舉了自2016年英國脫歐、特朗普首次當選美國總統以降,社會科學家、記者、專家和幾乎所有人嘗試對全球民粹崛起給出的九種解釋:1、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的經濟不平等;2、經歷地位喪失的群體中存在的種族主義、本土主義和宗教偏見;3、將人們按照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分類的社會變革以及對精英和專家統治的不滿情緒;4、像特朗普這樣的煽動家個人的特殊才能;5、主流政黨未能提供增長、就業、安全和基礎設施;6、對進步左翼的文化議程的厭惡或仇恨;7、進步左翼領導層的失敗;8、人性中的暴力、仇恨和排斥傾向;9、社交媒體和互聯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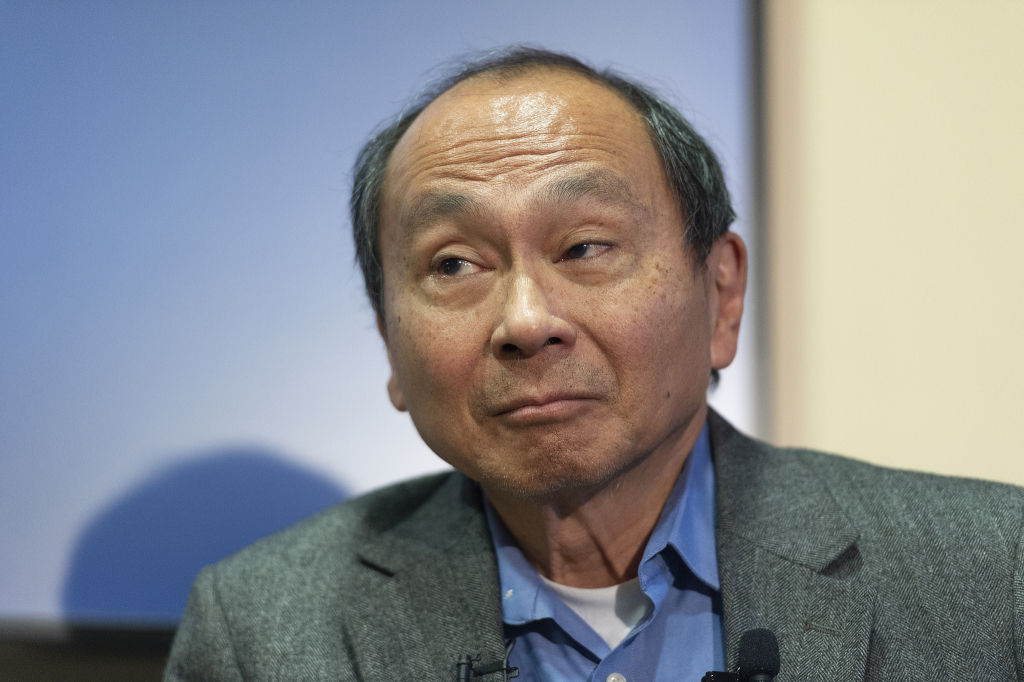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福山指出,上述九個因素都在全球民粹主義的興起中發揮了一定作用,民粹主義是一個多層面的現象,某些因素在解釋該現象的特定方面時具有更強的解釋力,但在近十年的思考之后,他得出結論:科技,尤其是互聯網,才是全球民粹主義在這一特定歷史時期興起并呈現其特定形式的最主要因素。
福山對前8個因素的不足逐一進行了剖析,這些解釋中討論的現象往往在過去早已發生過,發達社會在20世紀經歷過比近年來更嚴重的惡性通脹、高失業率、大規模移民、社會動蕩以及國內外暴力等狀況在20世紀,因此無法解釋全球民粹主義浪潮的興起為何發生在歐美社會經濟狀況發生良好的2010年代。福山指出,當前民粹主義運動與以往右翼政治的表現形式不同,它并非由明確的經濟或政治意識形態所定義,而是由陰謀論思維所定義。當代民粹主義的本質在于認為我們周圍的現實證據是虛假的,是幽暗的精英在幕后操縱的結果。雖然陰謀論一直是美國右翼政治的組成部分,但今天的陰謀論愈發荒誕不經且影響深遠。
因此,福山認為互聯網的興起才是最有力的解釋。互聯網取代了中介機構、傳統媒體、出版商、電視和廣播網絡、報紙、雜志以及人們先前獲取信息的其他渠道。早在1990年代互聯網進入私人生活時,人們就為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的出版商、在網絡上暢所欲言而歡欣鼓舞。而這既是這一時期人們普遍對各種機構喪失信任的誘因,也是其結果。
福山指出,互聯網創造了一個平行宇宙,它與現實世界存在某些關聯,但在有些情況下又與之南轅北轍。此前,“真相”由科學雜志、傳統媒體以新聞問責機制、法院和司法發現、教育和研究機構的標準予以并不完美的認證,如今真相的標準開始轉向特定帖子的點贊和分享數量。大型科技平臺為追求自身商業利益,創造了一個獎勵聳人聽聞和顛覆性內容的生態系統,其推薦算法也同樣出于利潤最大化的考慮,將人們引向在過去不會被采信的信息來源。此外,網絡迷因和低質量內容的傳播速度和范圍急劇加快和擴張。過去,一份主流報紙或雜志通常只能覆蓋一百萬讀者,而且只覆蓋一個地理區域;而現在,一位網紅可以覆蓋數億粉絲,且不受地域限制。正如蕾妮·迪雷斯塔(Renee DiResta)在其著作《隱形統治者》(Invisible Rulers)中所解釋的那樣,網絡帖子的內在動力學解釋了極端主義觀點和材料的興起,網紅們受其受眾驅使,追求聳人聽聞的內容。互聯網的貨幣是注意力,而你無法通過冷靜、反思、提供信息或深思熟慮來獲得關注。
福山還提到了另一種可以解釋當下政治特殊性的互聯網內容,即電子游戲。槍殺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的年輕嫌犯泰勒·羅賓遜(Tyler Robinson)就是這種關聯的例證,他是一個活躍的游戲玩家,在彈殼上刻上了游戲世界的迷因。1月6日國會山動亂的許多參與者也是如此,他們服用了“紅色藥丸”因而“可以看到主流力量試圖偷竊特朗普的選舉結果”。電子游戲市場規模龐大,全球收入估計在2800億至3000億美元之間。
文章最后總結到,互聯網的出現既可以解釋民粹主義興起的時機,也可以解釋它所具有的令人費解的陰謀論特征。在當今政治中,美國兩極分化的紅藍雙方身處截然不同的信息空間:雙方都認為自己正卷入一場關乎美國民主的生存之爭,因為他們對美國民主秩序所面臨威脅的本質的理解有著不同的事實前提。
互聯網摧毀民主的觀點并非福山的獨創,《泰晤士報》(The Times)撰稿人詹姆斯·馬里奧特(James Marriott)上月在其Substack博客上發表的“后讀寫社會的開端”(The dawn of the post-literate society)一文,提出了屏幕革命(screen revolution)這一概念。馬里奧特認為,2010年代發生的以智能手機出現為標志的“屏幕革命”,是對18世紀印刷文化興起帶來的“閱讀革命”的反動,正如印刷術的出現給腐朽的封建世界帶來了致命一擊,屏幕也在摧毀自由民主的世界。
馬里奧特指出,我們所熟知的世界是在閱讀革命中形成的。尼爾·波茲曼指出,十八世紀印刷文化的興起并非偶然,它與理性日益增長的威望、對迷信的反感、資本主義的誕生以及科學的飛速發展息息相關。其他歷史學家則將十八世紀識字率的激增與啟蒙運動、人權的誕生、民主的到來,甚至工業革命的開端聯系在一起。然而300多年后的今天,書籍正在消亡。在美國,過去二十年里,為樂趣而進行的閱讀減少了40%,在英國,超過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表示他們已經放棄了閱讀。英國國家讀寫素養基金會(the National Literacy Trust)報告稱,兒童閱讀量“令人震驚和沮喪”,目前已降至歷史最低水平。出版業正處于危機之中,過去能賣出數十萬冊的書現在能賣到幾千冊已是幸事……
更驚人的是,經合組織(OECD)在2024年末發布的一份報告發現,大多數發達國家的讀寫能力正“下降或停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是2010年代中期智能手機在發達社會被廣泛使用,這幾年將成為人類歷史中的一道分水嶺。智能手機的設計初衷就是讓人上癮,讓用戶沉迷于無意義的通知、無聊的短視頻和社交媒體的憤怒誘餌。現在,普通人每天平均要花7個小時盯著屏幕,而Z世代則高達9個小時。《泰晤士報》最近的一篇文章發現,現代學生平均要花25年的時間在滑動屏幕上。今天的大學正在教授第一批“后讀寫時代”的學生,他們幾乎完全是在短視頻、電腦游戲、令人上癮的算法(以及日益流行的人工智能)的世界中成長起來的,他們中的很多人實際上失去了讀寫能力,讀不懂莎士比亞、彌爾頓和簡·奧斯丁等作家流傳了幾個世紀的經典作品,無法從書籍中汲取知識。知識的傳承和學習的傳統瀕臨斷裂。馬里奧特稱,如果說閱讀革命代表著歷史上知識向普通人的最大規模轉移,那么屏幕革命代表著歷史上針對普通人的最大規模的知識竊取。
讀寫能力的下降導致了各種認知能力指標下降。一項名為“監測未來”(Monitoring the Future)的研究持續調查18歲的青少年是否在思考、集中注意力或學習新事物方面存在困難,報告存在學習困難的學生比例在20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初都保持穩定,但在2010年代中期迅速上升。這些認知問題不僅局限于學校和大學,各個年齡段的成年人中都出現了推理和解決問題能力的下降。除了信息和智力的流失,讀寫能力下降還造成了人類體驗趨于貧乏的悲劇。幾個世紀以來,幾乎所有受過教育的有識之士都認為,文學和學習是人類存在的最高目標和最深慰藉,智能手機正在奪走這一切。21世紀在年輕人中肆虐的焦慮、抑郁和無目的感正是無意義、碎片化、瑣碎的屏幕文化的直接產物,這種文化完全無法與人類對好奇心、敘事、深度關注和藝術滿足的深層次需求對話。隨之而來的是創造力和創新的終結。
馬里奧特進一步指出,現代文明的整個知識基礎設施都依賴于與閱讀和寫作密不可分的復雜思維:嚴肅的歷史寫作、科學定理、詳細的政策建議,以及在書籍和雜志中進行的嚴謹而冷靜的政治辯論。這些先進的思想形式為現代性提供了思想基礎,而這些基礎正在我們腳下崩坍:屏幕世界將比印刷世界更加動蕩不安:更加情緒化、更加憤怒、更加混亂。寫作讓思考變得冷靜和理性,而短視頻可以通過大喊大叫、哭泣、播放煽情的音樂和展示可怕的圖像等種種手段繞過邏輯論證而讓觀眾屈服。很多觀點如果寫在紙上會顯得荒謬至極,但在屏幕上卻能讓很多人相信,因此陰謀論者能夠在網絡上找到大批信眾。這些情緒化和非理性思維方式的興起對我們的文化和政治構成了深刻的挑戰。
他接著寫到,18世紀的閱讀革命對于舊的封建等級制度發起了沖擊。舊等級制度建立在前讀寫時代中神秘主義和情緒性思維的吸引力之上,而隨著知識在社會中的傳播,以及印刷術所培養的分析型、批判性思維模式的興起,維系舊秩序的整個精神和文化氛圍被摧毀殆盡。在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讀者群的支持下,啟蒙哲學家和激進思想家開始提出那些主要基于印刷品的批判性問題。權力從何而來?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多?為什么人與人不平等?因此,即便印刷文化不是一個完美無缺、不可腐蝕的交流系統,但它無疑是民主的先決條件。印刷文化傾向于培育的深厚知識、邏輯論證、批判性思維、客觀性和冷靜參與,讓普通民眾擁有了理解統治者、批評統治者,甚至改變統治者的工具。
然而,短視頻時代的政治更偏愛煽動情緒、無知和毫無根據的斷言,這種情況對于擁有個人魅力的冒牌貨非常有利。不可避免地,在后讀寫時代,敵視民主的政黨和政客正在蓬勃發展。TikTok的使用與民粹主義政黨和極右翼的選票份額上升息息相關。大型科技公司樂于將自己視為知識和好奇心的傳播者,但事實上只有宣揚愚蠢才能維持其生存。讓民眾保持無知對于科技寡頭們的重要性,絲毫不亞于其對于最反動的封建獨裁者的重要性。古老的歐洲君主制不得不致力于審查危險的批評性內容,而大型科技公司卻可以通過向我們的文化中灌輸憤怒、分散注意力的和無關緊要的內容來更高效地確保人們的無知。這些公司正在積極摧毀啟蒙運動的遺產,從而開啟一個新的黑暗時代。
馬里奧特最后指出,我們或許正在步入第二個封建時代,抑或正在進入一個想象之外的政治時代——無論如何,曾經熟悉的世界正在消逝,我們來到了后讀寫社會。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