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6年前接受我們采訪的時候曾說……
瑞典學院將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
近年,拉斯洛始終位于諾貝爾文學獎熱門人選的前列,也被認為是匈牙利文學的最杰出代表。

匈牙利作家拉斯洛(Laszlo Krasznahorkai) 澎湃資料
2009年,拉斯洛來到北京和上海旅行,在此期間曾接受了湃新聞前身東方早報記者的專訪,以下是當時專訪的部分內容。
澎湃新聞:一直很奇怪,像《撒旦探戈》這樣的作品當年怎么能在匈牙利順利出版,小說出版后當時有沒有遇到政治上的問題?
拉斯洛: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知識分子有很多時間,每一天都長到不可思議。我每天早晨去酒吧喝酒,心想這一天會很長,生命會很慢。
在匈牙利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本書幾乎不可能出版。書稿在出版前換了許多人的手,小說最后能出版,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出版社的社長對我說:“我們可以出你的書,但有一個條件,只能印‘最小印數’。”那時的最小印數是10000冊。現在的人會說印10000冊是瘋狂的,出書一般都是2000冊、5000冊,但當時最少就是10000冊,那是個非理性的時代。我覺得當時在高墻后面,當局者覺得困惑,他們覺得有什么事要發生了,而我們那時候還沒感覺到。
在正式出版前,有一天,導演貝拉·塔爾打來電話跟我說,想把它拍成電影,我說不行——而我們的友誼就是這么開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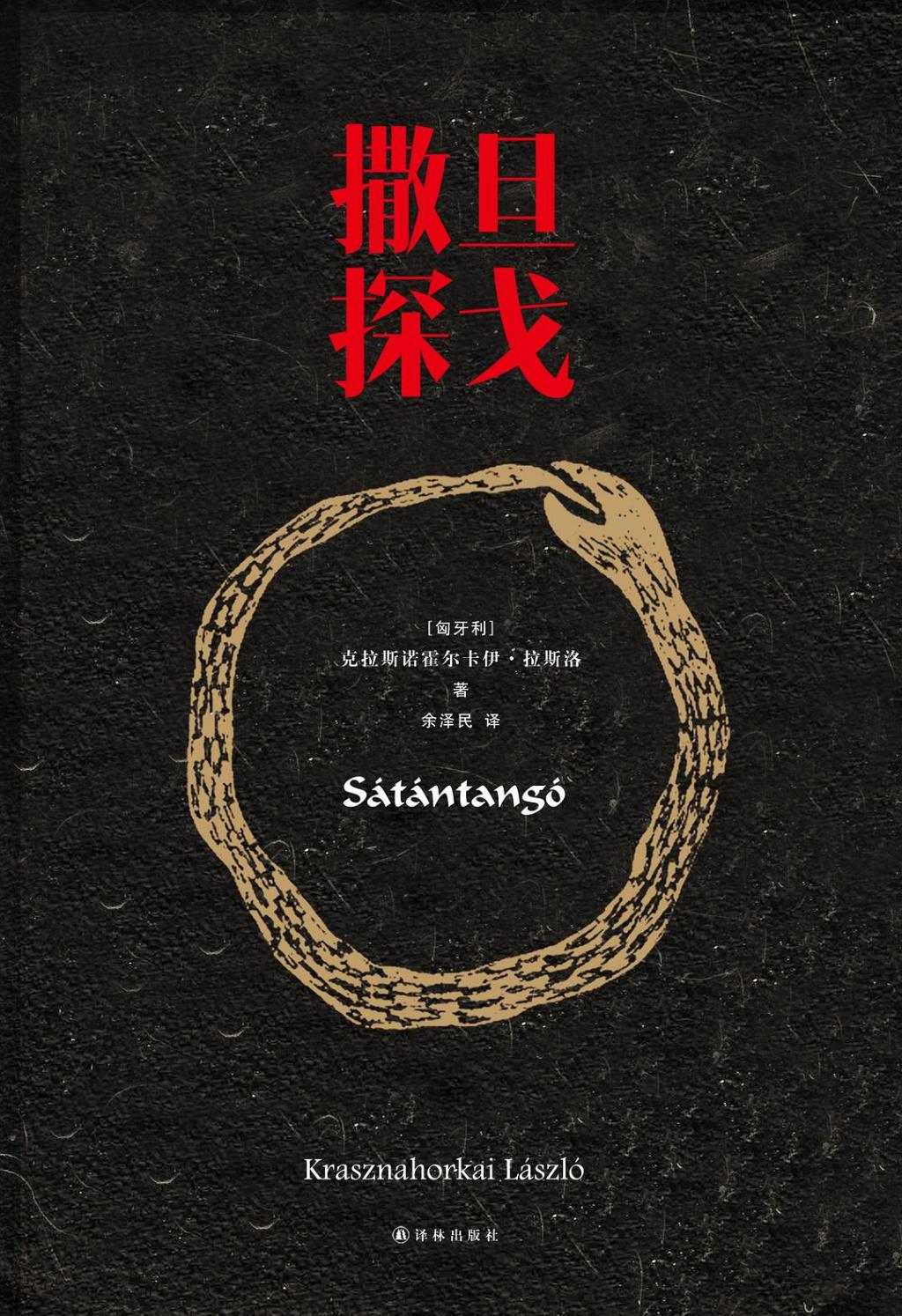
《撒旦探戈》
澎湃新聞:是什么原因離開匈牙利的?
拉斯洛:1987年是我第一次能離開匈牙利,當時已經30歲了。我當時只有一個作家朋友,他說你不走就會被殺,我走后兩年國家就發生劇變。
澎湃新聞:1989年,匈牙利首先開放了通往西方的邊界,然后才有了柏林墻的倒塌,也許匈牙利才是開始。
拉斯洛:匈牙利開放邊界是導致東歐劇變的第一波,比柏林墻倒下還早。當時蘇聯已到了崩潰邊緣,沒人覺察。然后,匈牙利的一件小事就有了這么大的效果。
澎湃新聞:柏林墻倒塌時你在哪里?
拉斯洛:柏林墻倒塌時我在柏林,德國人很激動,我沒有。在西柏林時,我有種感覺,覺得柏林墻保護著我。我當時想:“天吶,下面會生發生什么?”我覺得自己沒了保障。然后自由世界就開始了。墻倒后我的流浪就開始了。
澎湃新聞:你的小說還沒有翻譯成中文(2009年訪問時還沒出版中文版),但我從電影版的《撒旦探戈》和《反抗的憂郁》里可以看出,你的小說有點黑暗,充滿哥特味。
拉斯洛:是當時的現實太黑暗。但從我開始創作的那年到現在,我沒覺得世界有什么大的變化,在非洲、美洲、中國,我都覺得一樣悲傷。什么是幸福呢?是愛嗎?我覺得不是,愛是痛苦的。幸福是一種幻覺,也許你可以幸福上那么一兩分鐘,但之前和之后都是悲傷的。我覺得沒有什么理性的原因讓我可以快樂起來,當我回顧人類歷史,有時我會覺得是一出喜劇,但這喜劇讓我哭泣;有時又覺得它是出悲劇,但這悲劇讓我微笑。

《反抗的憂郁》書封
澎湃新聞:我覺得,你的小說和其他東歐作家的作品不太一樣,你的作品里沒有那種戲謔、反諷和幽默。
拉斯洛:東歐作家并非完全是幽默有趣的。在東歐文學中,事情經常顯示喜劇和悲劇的兩面。從這面看是喜劇,那面看是悲劇。東歐作家對事情的這兩面格外敏感。我告訴你一件事,我覺得《撒旦探戈》不是黑暗的作品,也不是悲劇,它是一部悲喜劇,是關于沒有根據的信仰。
澎湃新聞:這些年的西方生活對你的寫作和思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拉斯洛:在柏林墻倒塌之前,我們有種幻想,覺得在遠離匈牙利、遠離東歐的地方,有一個絕對理性、自由、奇妙的世界。但柏林墻倒塌之后,我的幻想就破滅了。我們看到了夢中的自由世界,但那是現實的,是苦澀的,是不提供幻想的。在專制統治下生活,你覺得自由是甜的,但它其實是苦的。
在1989年前我覺得寫作是有目的的,是理性的。1989年后環球旅行,這種感覺卻漸漸消失了。今天我也寫人的尊嚴,但我不知道為誰而寫。自由世界里的人要的是金錢、女人。人的尊嚴、自由、獨立思考之類的東西免談。文學也跟著遭殃。作為作家,如果一本正經,讀者就覺得沉悶,別人就說:“對不起,沒時間,我要去掙錢買新車。”這讓我覺得傷心,這就是我悲傷的原因。人類有許多選擇,但大家都只選一樣,那就是什么都想要。
澎湃新聞:所以,我覺得你的寫作更多是哲學寫作。
拉斯洛:我覺得我的書是哲學,是關于痛苦的。
澎湃新聞:你現在定居在柏林,可離開母語環境和祖國寫作,會傷害你的語言敏感度嗎?我知道你堅持用匈牙利語寫作。
拉斯洛:柏林很新,但花上一點時間,你會感受到45年里發生的事。柏林是我的城市。
我住在柏林,但用匈牙利語寫作。因為匈牙利語是我的母語。我想過能否不用語言思考?發現不行,思維的結構是和語言緊緊綁在一起的。而母語又不同于其他語言,母語不單是語言,還是本能。我在寫作時,也在思考,所以我用匈牙利語。我不僅住在柏林,還住在我的文字中。我在柏林付賬單,但我還住在我的文字里。
澎湃新聞:你的寫作似乎關注那些人類終極命題,而今年(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米勒——當然她也是從東歐羅馬尼亞出來的——她的寫作始終關注的是歷史。
拉斯洛:我在1980年代就認識赫塔·米勒,她先在漢堡和丈夫一起,后來來了柏林。因為她的過去很重要,她寫過去。在她的過去,人們痛苦地生活,沒有尊嚴。我覺得赫塔的作品和部分中國的作品相似。
澎湃新聞:那你的另一位老鄉雅歌塔·克里斯托夫呢?居住在瑞士的她用法語寫了“惡童三部曲”。
拉斯洛:她的小說很殘忍,看的時候感覺是在受罪。她的故事和我以及其他人都不一樣。她到西方的時候很年輕,說“想丟掉一切”,她不需要過去,也不需要語言,說自己必須向匈牙利語說“不”,于是就用法語寫作了。
澎湃新聞:相對而言,生活在美國的羅馬尼亞作家諾曼·馬內阿和你的情形相近,他堅持用母語羅馬尼亞語創作。
拉斯洛:今年夏天我在西班牙開會時遇到了他。當我剛流亡到西柏林的時候,我就認識他了,他那時候拿了獎學金在柏林學習,他離開柏林后,我就很久沒見他,今年再見時,他已經變了一個人。在美國的日子讓他變得開朗有趣,而在柏林時他很封閉。
澎湃新聞:很多人開玩笑說,諾貝爾獎如果要在羅馬尼亞人頭上輪的話,怎么也得是諾曼而不是赫塔,當然對于諾曼,不得不注意他的猶太身份。
拉斯洛:猶太人的認同有時是加法,有時是減法。大屠殺的時候是減法,減到了零,猶太人成了零,成了沒有面目的人。眼下在做加法了。諾曼又來去了美國,許許多多的猶太人和匈牙利人到了美國,到了紐約,到了好萊塢。
拉斯洛:中國的情況很不同,中國身處另一個大洲,另一個世界。現在中國是古代中國的延續,中國有很長的過去,這很重要。而歐洲的歷史特別是匈牙利歷史總是在被打破,總是在失落。匈牙利人的認同在19世紀之前都是清晰的,我們知道自己是匈牙利人,也覺得驕傲。但19世紀末開始,危機就產生了。羅馬尼亞人、斯洛伐克人、許多外族人都和匈牙利人住在一起。這就是匈牙利人的認同危機的源頭,也是已經自由的匈牙利最深的痛苦之源。雖然歷史匈牙利人的獨特身份對我寫作沒有太多直接影響,但我想說,我也可以從家庭中嗅到匈牙利的歷史:一個潰敗接著一個潰敗。我的家庭構成復雜,母親那邊是純匈牙利人,父親那邊有法國的,有猶太人,還有許多其他民族的血統。所以我們的歷史總是被打斷。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