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羅永浩,帶不動視頻播客

是風口還是假象?
定焦One(dingjiaoone)原創
作者 | 陳丹
編輯 | 魏佳
曾被調侃“天天喊破圈、年年是元年”的中文播客,這一次終于迎來破圈時刻。
理想汽車CEO李想在羅永浩視頻播客中潸然落淚、魯豫說要“收養”竇文濤的片段,在社交媒體上實現了病毒式擴散——從微博熱搜到朋友圈刷屏,再到短視頻平臺的二次創作,播客這個“小眾自留地”被納入了大眾視野。
9月24日,360公司董事長周鴻祎做客羅永浩的播客節目,與其對談AI,再次引發討論。這些名嘴+明星嘉賓的視頻播客節目,也讓不少人看到了中文播客對標國際頭部的可能:美國“播客之王”Joe Rogan的同名節目,訪談對象覆蓋特朗普、馬斯克等全球頂流,僅在YouTube平臺的訂閱數就突破2000萬,影響力早已超越普通播客節目的范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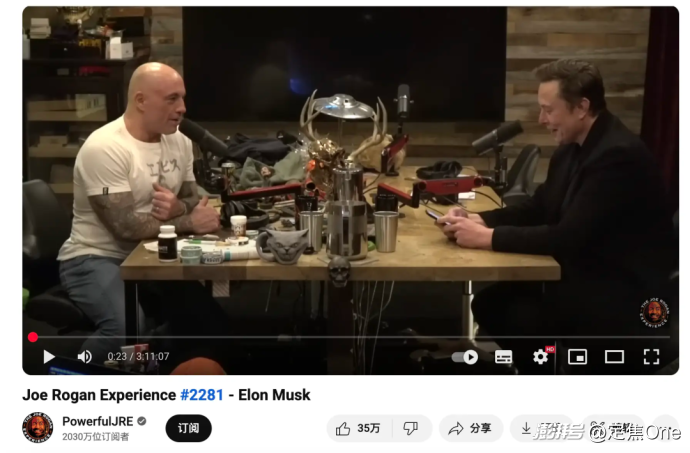
Joe Rogan節目截圖
不只羅永浩和魯豫,于謙、李誕、楊迪等名嘴紛紛試水,在B站開設專屬視頻播客欄目,每期播放量都輕松突破百萬,節目切片更是散播于互聯網的各個角落。
其他互聯網巨頭也不再滿足于旁觀,而是直接下場:小紅書打造“隨時隨地視頻播客”標簽,抖音在精選板塊為播客內容開辟流量入口——當大廠們帶著龐大的用戶基數與流量入場,當明星名嘴帶著粉絲與話題度加盟,播客從“音頻賽道的小眾分支”躍升為“內容領域新寵”,甚至有人視其為“內容行業的下一個風口”。
但熱鬧之下,亦有隱憂。
“這會不會是一種熱鬧的假象?”在一期播客節目上,一位主播拋出了自己的疑問。
這份擔憂并非空穴來風。當前視頻播客的熱度,幾乎都由“名人效應”支撐——破圈的是名人的眼淚與話題,刷屏的是明星的段子與過往,那些廣泛傳播的片段,是娛樂化、碎片化的情緒點,與播客原本追求的“深度、陪伴、信息增量”相去甚遠。
更關鍵的是,這場由名人與互聯網巨頭催生的熱度,能持續多久?當名人的新鮮感褪去,巨頭的流量扶持轉向下一個風口,視頻播客是否會曇花一現?而行業里那些中小播客主,那些仍在“為愛發電”的普通創作者,又能否從中分到一杯羹?畢竟現在的熱鬧,與他們無關;未來的機會,也仍在迷霧之中。
風口下的分裂:“新概念”還是“舊生意”
“要不要做視頻播客?”這道選擇題,擺在很多播客主面前。有人果斷劃掉選項,有人卻想抓住這個“風口”。
肉松和室友哈拿在小宇宙運營著的播客欄目《置頂廢話》,訂閱用戶剛剛突破1200人,某期節目還上了平臺熱門榜單,現在正是需要擴大聲量的時候。但當她們聊起是否要做視頻播客,話題很快轉向為“為什么不做”,理由直白又現實——“誰會愿意花時間單純看兩個普通人聊天?”

圖源 / pexels
小宇宙的頭部主播劉飛,運營的兩檔節目《三五環》和《半拿鐵》加起來訂閱用戶超過80萬。很多聽友也勸他嘗試一下——“不就是架個鏡頭的事兒?”但劉飛告訴「定焦One」,未來也許會考慮,當前并沒有找到合適的形式與方法。
劉飛和肉松的謹慎,都源自于對當下視頻播客這一形式的疑慮。
在劉飛看來,視頻播客現在就是個“生造的概念”——它的邊界模糊到幾乎可以囊括所有內容:魯豫、羅永浩、于謙等名人推出的播客,本質是貼了“播客”標簽的訪談或綜藝節目;而小Lin說、巫師財經、半佛仙人的作品,雖信息密度高,卻無需依賴畫面,純聽也能獲取完整信息。換句話說,所謂的“視頻播客”,不過是給傳統視頻內容或音頻內容套上了一個新殼子,并未形成獨特的內容形態。
這種疑慮,進一步延伸到“供給”與“需求”的雙重困境。
從供給側看,對播客主而言,視頻化遠非“架個鏡頭”那么簡單,機位數量、剪輯邏輯、打光、妝容,每一項都是全新的挑戰,制作精良視頻的成本遠超音頻。更關鍵的是,單槍匹馬或小團隊作戰的他們,要面對的是視頻行業專業團隊的競爭。若只是將音頻內容直接轉化為視頻,慢節奏、長時間、低畫面信息量的“粗糙成品”,在中長視頻賽道上沒有什么競爭力。
從需求側看,播客的核心優勢,本就是適配“眼睛和手被占據”的場景,例如通勤、健身、做家務時,聽眾無需分心看畫面,就能接收信息。一旦用戶有時間看視頻,往往會優先選擇信息密度更高、視聽更刺激的內容,視頻播客反而成了末位選項。
用戶需求不強烈,制作成本飆升——這是很多播客主“望而卻步”的原因。
但行業里也有一群人的態度截然相反。
一位從業5年的廣播人在社交媒體直言,聲音永遠只能是邊緣媒體,穿透力和商業價值天然弱勢,建議所有播客主“高度重視視頻播客”這一轉身的機遇。狂喜播客節創始人關雅荻也在一檔播客節目中,鼓勵大家開放心態。在他看來,視頻播客是未來的趨勢,而且制作的門檻并沒有想象的那么高,“有話要說比技術更重要”。
播客公社創始人老袁對視頻播客也持積極態度,他尤其鼓勵行業新人嘗試,因為他們迫切需要的是被聽到、被看到,至于通過什么形式并不重要。在他看來,當前國內視頻播客與傳統訪談類節目、綜藝節目無明顯區別,但只要支持“閉屏場景收聽”,就具備播客屬性。
他指出,當前播客滲透率提升的一個瓶頸就是,對于播客的認知混亂,視頻播客尤其容易形成“精英化、明星化”的刻板印象。而美國播客市場的成熟,恰恰在于其認知的統一性——播客就像社交媒體,人人都能做,不限形式、不限平臺,也無關名氣大小。
有人怕踩坑,有人想搶位,這一波視頻播客熱度傳導到行業一線的從業者,冷熱并不均勻。
大廠的野心和困境:內容與算法錯位
互聯網平臺入局播客,核心目標始終是拓展增量,即通過播客內容吸引新用戶、壯大創作者生態。但在具體落地中,B站、小紅書、抖音等平臺基于自身定位,打法各不相同。
從現階段來看,B站的動作最為激進:暑期投入10億級冷啟動流量,還在北上廣杭等城市提供免費錄制場地,甚至計劃上線視頻播客專屬AI創作工具。這一系列資源傾斜,看似誠意十足,實則延續了“長視頻邏輯”。
老袁指出,B站早期想借視頻播客拓展內容生態,現階段則將重心放在“明星大咖節目”上。對B站而言,這類內容的核心優勢在于以低成本撬動高價值資源:無需像劇集、綜藝那樣投入重版權成本,僅靠“播客”標簽就能吸引明星參與,既豐富了內容池,又能借明星流量拉新。
小紅書則走社區運營路線,試圖將播客納入自身生態:推出“隨時隨地視頻播客”專屬話題,8-9月參與創作的用戶可直接獲得5萬-30萬曝光資源;更早前,市場傳言原小宇宙COO芒芒(陳臨風)、內容總編ouli(歐里)、商業市場負責人小福等核心人員加盟小紅書,足見其對播客業務的重視。但這一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證實。
老袁分析,小紅書的核心訴求是“讓播客主將其作為第一運營陣地”。此前播客主在小紅書多發布播放截圖、錄制花絮,信息碎片化,通過視頻播客,小紅書希望將播客內容納入社區生態,但15-20分鐘的內容時長,與小紅書用戶“碎片化瀏覽”的習慣、播客的深度陪伴都存在一定矛盾。
相比之下,抖音的嘗試更為謹慎,僅在“抖音精選”推出《奇遇記播客》,6月中旬上線至今已更新28期,每期嘉賓均為抖音數百萬粉絲級大V。老袁認為,抖音更注重內容產品的商業化效率,而當前播客行業的招商、付費等商業模式尚未成熟,因此當前的動作僅僅是試水,暫不會押寶視頻播客。

圖源 / pexels
盡管平臺投入力度不小,但劉飛與老袁均向「定焦One」表示,多數活躍在小宇宙等音頻平臺的播客主,遷移至B站、小紅書的意愿并不強烈。
首先,從用戶習慣來看,小宇宙等音頻平臺已培養起播客用戶“閉屏收聽”的場景依賴。而B站、小紅書均以視頻場景或圖文場景為主,若用戶想聽播客,仍會優先選擇小宇宙等音頻平臺,而非在視頻平臺“看播客”。主播更在意用戶聚集的平臺,自然也就缺乏遷移動力。
其次,播客的內容邏輯也與平臺算法存在錯位。劉飛告訴「定焦One」,做播客不太有流量焦慮。在其他平臺,內容創作者可能需要不斷適應算法規則和用戶預期以獲得推薦,但做播客只需要給聽眾提供“非常穩定的預期”,如果創作者“跳來跳去”、每天琢磨如何“算流量”,反而會妨礙長期積累。
老袁補充到,他做播客近10年,流量增長雖然緩慢,但“只漲不跌”,與公眾號“擔心打開率”、直播“擔心用戶時長”的焦慮形成鮮明對比。如果單純依賴平臺現有的算法分發,深度內容很難存活。
更關鍵的是,B站、小紅書等平臺雖然短期內能帶來一定流量,但并沒有解決播客商業化的難題。老袁表示,無論是音頻平臺,還是小紅書、B站,中腰部創作者都難以觸達平臺的商業化資源。只有創作者穩定變現、平臺吸引更多創作者入駐、用戶獲得優質內容——如此健康循環,才能形成一個穩定的市場,否則現有的熱度只能是“一波流”。
劉飛則認為,這場熱潮跟2017年悟空問答挖知乎大V,5年前西瓜視頻挖B站UP主,沒有本質區別。
歸根究底,播客主的核心需求是“低成本創作+穩定受眾+可持續變現”,若平臺無法為播客主提供更低的創作成本、更精準的聽眾、更明確的商業回報,就難以真正吸引播客主遷移。這也是當前視頻播客行業熱鬧表象下的核心問題。
未來,一場漫長的等待
對于跌跌撞撞發展了十幾年的播客行業來說,商業化始終是痛點所在。
目前,播客主的商業收入主要來自于廣告和用戶訂閱,但兩者目前都難以支撐行業整體發展,即能養活頭部,大量的腰部、尾部創作者依舊是為愛發電。
根據Statista統計,去年中國播客廣告總收入僅為33億元,這一數字遠遠低于短視頻平臺。老袁告訴「定焦One」,當前播客廣告市場完全處于“買方主導”:一方面,定期投放播客的品牌相對固定,多集中在消費電子、生活服務等細分領域,整體市場需求有限;另一方面,廣告合作缺乏明確的定價體系——品牌方通常會通過數據監測,篩選出訂閱量達標且呈增長態勢的節目主動接洽,但最終投放金額、合作形式完全由品牌說了算,播客主幾乎沒有議價權。
此前,曾有媒體報道,訂閱數近50萬的某播客品牌,單條口播廣告刊例價為38889元,定制單集報價也僅13.3萬,2024年3月到11月總收入19萬,扣除基本開銷,凈收入只剩13萬。
相較于廣告的不穩定,用戶訂閱被老袁視為更可持續的變現方式。據了解,播客訂閱的收費模式主要分兩種:單集付費,價格通常在4-10元不等;專題付費,在30-300元之間。但現實是,整個播客行業能依靠訂閱收入實現穩定生存的節目很少,老袁預估占比不足5%。
播客商業化之所以陷入困境,核心源于兩大癥結:一是“內容看不見”導致的效果追蹤難題,二是“流量掣肘”引發的用戶規模與變現效率瓶頸。
播客作為純音頻內容,天然缺乏視頻、圖文的可視化優勢,這給廣告效果追蹤帶來極大挑戰。對廣告主而言,投放短視頻可通過“完播率、互動率、商品鏈接點擊量”等數據直觀評估效果,投放圖文可通過“閱讀量、轉發量、轉化漏斗”衡量價值。

圖源 / pexels
但播客的廣告植入多為“口播提及”,用戶是否完整聽到廣告、是否因廣告產生消費意愿,甚至是否記住了品牌信息,都無法通過精準數據量化。這種“效果模糊性”,讓不少廣告主對播客持謹慎投放態度,進一步壓縮了行業的廣告市場空間。
根據CPA中文播客社區發布的《2025播客營銷白皮書》,2025年,中文播客聽眾規模預計將突破1.5億人,但和抖音、B站等平臺相比,用戶規模仍有限。不少從業者將視頻播客視為風口的理由之一便在于視頻市場的用戶人群超過音頻市場,覆蓋的用戶更多,商業機會也更大。還有人將美國的視頻播客市場視作未來——單單在YouTube,播客內容每月活躍觀眾就超過10億。
這個未來到底會不會到來,每個人的想法并不相同。
在劉飛看來,當前互聯網平臺做播客,對行業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像小宇宙仍然是小圈子的產品,視頻播客內容不斷破圈,肯定會讓越來越多人知道這個載體和這種內容形態,但至于能培育多少深度內容用戶,他比較悲觀。
美國用戶對“talkshow(脫口秀式對話)”接受度高,轉向YouTube播客視頻順理成章;而國內市場,即便像《圓桌派》《十三邀》這類優質對談節目,也始終屬于小眾需求,多數觀眾對慢節奏、重對話的播客內容接受度有限。因此,把播客搬到視頻平臺,并不意味著用戶規模就能擴大、商業化就能突破。“目前播客已有的用戶,可能就是當下市場能吸引到的大多數用戶。”劉飛的預測有些無奈。
老袁比劉飛更樂觀一些,他相信播客商業化時代終會到來。當播客成為人人可參與的社交媒體,行業生態成熟后,商業化自然會水到渠成。在那之前,播客對大多數創作者而言,只能是自我表達的出口,而非賺錢的工具。
“它不是風口,可能也不會有大爆款,哪怕偶爾有一期數據還不錯,但除了心理上的安慰外,并不會帶來實際的商業回報”——老袁告訴「定焦One」,播客主必須要做好這個心理準備。
肉松還在堅持。
她和室友做一期播客,從確定話題、錄制到剪輯,需要一周多的時間。每月更新兩期節目對她們來說已經比較吃力。今年之所以能堅持更新,是因為她和室友都在GAP期。隨著兩人其他工作的增加,未來能否保持現在這個更新節奏,她也沒法保證。
最近,肉松留意到小宇宙的開屏廣告變多了。她偶爾也會點進一些之前關注,但沒有廣告和訂閱收入的播客,很多人在做一段時間后,漸漸就不更新了。
*題圖來源于pexels。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