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老的多重奏|當(dāng)“老漂”說(shuō)“我想回家”
“我們不會(huì)一直留在這里,這里說(shuō)到底也不是我們的家。”
像許多背井離鄉(xiāng)來(lái)到東莞的老人一樣,六十多歲的老陳和妻子四年前成了“老漂族”,為了減輕兒女的育兒負(fù)擔(dān),他們離開了鄉(xiāng)村,暫時(shí)落腳在城市。如今,他們決定要回老家。
類似的返鄉(xiāng)故事并不少見。人們往往把它理解為一種“城市融入的失敗”,或者解讀為“老年幸福感不足”的表現(xiàn)。于是,在公共討論中,我們習(xí)慣性地強(qiáng)調(diào):要提升“老漂族”的幸福感,就需要幫助他們?nèi)谌氤鞘校缭卺t(yī)保政策上給予更多支持,讓社區(qū)活動(dòng)更豐富,重建鄰里之間的“附近感”,以及依靠數(shù)字技術(shù)幫助他們與家鄉(xiāng)親友保持情感連接。
這些努力當(dāng)然重要,但也許我們忽略了一個(gè)更簡(jiǎn)單卻更本質(zhì)的可能性:對(duì)一些老人而言,真正能帶來(lái)幸福的,不是繼續(xù)尋找在城市的立足點(diǎn),而是能心安理得地回到家鄉(xiāng),不再做“老漂”。

《父母的城市生活》劇照
要理解這種返鄉(xiāng)的邏輯,我們需要從“老漂族”自我敘事中去傾聽。在我們接觸到的多個(gè)案例中,老人們的返鄉(xiāng)故事清晰地展現(xiàn)了家庭責(zé)任與個(gè)人愿望之間的反復(fù)權(quán)衡。這并非個(gè)別現(xiàn)象,而是一種廣泛存在的文化困境。在他們的講述里,最常見、也最強(qiáng)大的,是一種家庭中心的話語(yǔ)。
為家而來(lái),也為家所困
“沒(méi)辦法,是一定要過(guò)來(lái)幫他們的。兒子媳婦他們兩個(gè)都上班,如果不來(lái)幫的話,小孩就沒(méi)人帶。”——吳叔這樣描述他選擇留在東莞的原因。
對(duì)于大多數(shù)“老漂族”而言,為子女提供嬰幼兒照料與家務(wù)支持,使其能更集中精力從事社會(huì)勞動(dòng),是他們“漂”入大城市的主要?jiǎng)右颍彩撬麄兎掂l(xiāng)時(shí)的重要考量。
確實(shí),年輕家庭完全可以通過(guò)請(qǐng)保姆、托幼機(jī)構(gòu)來(lái)解決育兒工作,但高昂的費(fèi)用與對(duì)社會(huì)托育資源的有限信任,讓很多家庭覺(jué)得“請(qǐng)父母來(lái)幫忙”是最劃算、甚至唯一可行的方案。在這種理性計(jì)算背后,有一個(gè)不言自明的前提:家庭的穩(wěn)定,尤其是子女能在城市里扎下根,是需要全家人合力去完成的大事。于是,在權(quán)衡利弊之后,父母進(jìn)城照料孫輩,成了很多家庭的“最優(yōu)解”。
僅僅把這事算成一筆“家務(wù)賬”還不夠。當(dāng)理性的權(quán)衡被日常話語(yǔ)化之后,它往往會(huì)被裹上一層道德的外衣。也就是說(shuō),家庭里那場(chǎng)看似務(wù)實(shí)的選擇,常常會(huì)被轉(zhuǎn)述成一種“應(yīng)該”的命令:父母來(lái)幫忙,不只是方便了年輕人,更是在履行一種被期待的道德角色。時(shí)間一長(zhǎng),理性的安排就變成了必須承擔(dān)的義務(wù),哪怕當(dāng)事人心里并不完全甘愿。
這種道德壓力,一部分來(lái)自長(zhǎng)輩自身的自覺(jué):有些老人把照顧下一代看成生命的一部分,是“當(dāng)了父母就該做的事”。李姨就這樣說(shuō):“對(duì)現(xiàn)在的生活有什么滿意不滿意的,就是來(lái)這里照顧這兩個(gè)小的,大的照顧完照顧小的,小的大了我們才算是真正的完成任務(wù)了。”另一面是來(lái)自外部的聲音:親戚、鄰里甚至子女偶爾無(wú)心的一句“要不就是你太自私”,都能把原本可以協(xié)商的安排變成難以開口的負(fù)擔(dān)。陳姨就坦言:“我們是沒(méi)有義務(wù)說(shuō)一定要幫他們帶孩子的,我跟其他老人講過(guò)。但這個(gè)話我不敢跟我兒子說(shuō),不帶的話,他就說(shuō)你自私,說(shuō)你一點(diǎn)忙都不幫。”這不是個(gè)別情緒,而是許多家庭里反復(fù)上演的場(chǎng)景。
于是,帶孫輩的行為從一項(xiàng)實(shí)用安排,悄悄變成了一個(gè)衡量人格與情感的尺子:誰(shuí)愿意無(wú)怨無(wú)悔,就被冠以“好父母”;誰(shuí)敢說(shuō)“不”,就可能被貼上“自私”的標(biāo)簽。學(xué)者李永萍就總結(jié)過(guò),當(dāng)代農(nóng)村家庭的倫理邏輯是:父母必須不斷地為子女付出,把資源一代代往下傳。否則,就會(huì)被村莊輿論指責(zé)為“不會(huì)做父母,不會(huì)做老人”[1]。
這種道德化的衡量在影視文化中也被放大并具體化。在熱播劇《小舍得》中,夏君山因家中沒(méi)人照顧孩子而向母親尋求幫助,不料遭遇了母親的明確拒絕——她說(shuō)這輩子伺候人伺候得夠夠的了,下半輩子再也不想伺候人。母親的這番“說(shuō)不”令家庭成員感到措手不及,并迅速引發(fā)誰(shuí)該承擔(dān)責(zé)任的爭(zhēng)論,恰恰說(shuō)明當(dāng)老人拒絕介入時(shí),這一選擇往往被解讀為越軌或冷漠,而非一種合理的邊界設(shè)定。
想回家,也想做回自己
“老漂族”在為家庭整體利益奔波的同時(shí),也會(huì)在心底反復(fù)權(quán)衡自己的感受 [2]。
首先,是對(duì)經(jīng)濟(jì)依附的擔(dān)憂與對(duì)挺直腰桿的追求。離開家鄉(xiāng)進(jìn)入子女所在的城市之后,“老漂族”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經(jīng)濟(jì)來(lái)源,這在城鄉(xiāng)流動(dòng)的老漂中表現(xiàn)尤甚:大城市高昂的物價(jià)水平與鄉(xiāng)土社會(huì)“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形成顯著差異,大多數(shù)“老漂族”的日常生活所需都依靠子女供給,整體呈現(xiàn)出一個(gè)“只出不進(jìn)”的狀態(tài)[3]。即使有少數(shù)老人設(shè)法找到一份工作,比如做清潔、看門,甚至靠撿廢品補(bǔ)貼家用,但與青壯年流動(dòng)人口相比,他們的體力和技能早已不占優(yōu)勢(shì),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始終處于邊緣[4] 。
相信每個(gè)小區(qū)都會(huì)有那么一位“愛(ài)撿垃圾”的老人,毛叔就是其中之一。他一邊幫忙帶孫子,一邊在當(dāng)?shù)刈銮鍧嵐ぃ槺銚煨U品。雖然在老家他只是普通農(nóng)民,但他仍覺(jué)得“撿廢品”不太體面。然而,即便如此,他還是堅(jiān)持干這份“不體面”的活兒,因?yàn)槟苡幸恍┦杖搿S谩袄掀濉钡脑拋?lái)說(shuō),經(jīng)濟(jì)獨(dú)立意味著“腰桿挺直了”,“人活著才有尊嚴(yán)”。
其次,是對(duì)家庭空間中的話語(yǔ)權(quán)侵蝕的不快與對(duì)重獲自主權(quán)的渴望。對(duì)許多老人而言,“子女的家”和“自己的家”是兩個(gè)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子女的家中,他們常常缺乏決策權(quán)和優(yōu)先使用權(quán),哪怕是最日常的生活空間也未必由自己掌控。陳姨就曾向筆者訴苦:“她(孫女)媽媽天天在客廳刷抖音,聲音放得特別大,我電視的聲音都聽不見了,跟她說(shuō)也沒(méi)用,我就走了,早點(diǎn)去床上睡覺(jué)算了。”在她看來(lái),房子是兒子和媳婦的,她只是“臨時(shí)借住”,即便不滿也只能忍下。返鄉(xiāng),意味著再也不用忍受這種“臨時(shí)借住”的位置,可以重新把生活的小事掌握在自己手里,而這些“微小的決定權(quán)”本身,就是自由的一部分。
返鄉(xiāng)話術(shù):想回家,也要說(shuō)成“為了家”
抖音上有個(gè)段子很有意思:女兒說(shuō)“媽,您回老家歇歇吧”,母親嘴上說(shuō)著“沒(méi)事沒(méi)事,我不累”,下一秒?yún)s眉眼帶笑地開始收拾行李。鏡頭雖然輕松,但背后點(diǎn)出了一個(gè)普遍的現(xiàn)實(shí)——許多老人不愿把“我想回家”直說(shuō)出口,不是不想,而是不敢給這句話貼上“為自己”的標(biāo)簽。
面對(duì)家庭責(zé)任與自我實(shí)現(xiàn)之間的矛盾,大多數(shù)選擇返鄉(xiāng)的“老漂”并不會(huì)直接否認(rèn)家庭的重要性,也不會(huì)明白地說(shuō)“我要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晚年”。他們更常見的做法,是在“家庭中心”的話語(yǔ)框架下,為自己的返鄉(xiāng)尋找一個(gè)合情合理的理由。換句話說(shuō),他們必須把返鄉(xiāng)包裝成“對(duì)家庭有好處”,才能讓這個(gè)選擇被子女和外界接受。
常見的一種策略,是把返鄉(xiāng)的前提設(shè)定為“家庭責(zé)任已經(jīng)完成”。比如,很多老人會(huì)說(shuō):“等孫子大一些,再回去。”在他們的邏輯里,只有當(dāng)孫子長(zhǎng)大、自己的“帶娃任務(wù)”告一段落時(shí),個(gè)人的自由與理想晚年生活才有被追求的正當(dāng)性。
另一種策略,是強(qiáng)調(diào)返鄉(xiāng)后的“持續(xù)性支持”。即便人不再留在城里,他們也會(huì)承諾繼續(xù)為家庭提供貢獻(xiàn)。正如毛叔所說(shuō):“我回到農(nóng)村種地賺錢了,我給我老伴給我兒子他們生活費(fèi)。”在他的設(shè)想里,自己等孫子大一些后回鄉(xiāng)務(wù)農(nóng),把收成變現(xiàn),再把錢寄給在城里的家人。這樣一來(lái),返鄉(xiāng)就不再是“為自己圖輕松”,而是另一種形式的“為家里付出”。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老人并不打算“徹底”返鄉(xiāng),而是想短暫回家休息幾個(gè)月。但即使是這種暫時(shí)性的離開,他們也往往需要以“家”的名義來(lái)包裝心愿。比如,有人會(huì)說(shuō)是為了照料年邁的母親,有人會(huì)強(qiáng)調(diào)“大家族那邊也需要自己”,也有人以“照顧另一半”為由來(lái)合理化返鄉(xiāng)的選擇。借助這些理由,他們才能在家庭話語(yǔ)的框架下,為自己的短暫休憩爭(zhēng)取到正當(dāng)性。
不可否認(rèn),一些“老漂族”在照顧子孫的過(guò)程中確實(shí)能獲得幸福感與成就感,但這種體驗(yàn)可能與他們心中理想的晚年生活存在落差。更為重要的是,當(dāng)照料孫輩逐漸被社會(huì)文化視為一種道德義務(wù)時(shí)[5][6],老漂族的自我需求往往難以被主流文化所認(rèn)可。因此,他們通過(guò)“繼續(xù)履行家庭義務(wù)”的方式合理化自己的返鄉(xiāng)決策,以避免道德譴責(zé)。
返鄉(xiāng)?“這很正常”
在“老漂”返鄉(xiāng)敘事的背后,我們需要看到:主流文化尚未充分承認(rèn)老漂族為家庭付出的自我犧牲,反而對(duì)這種付出有一種理所當(dāng)然式的期待。這讓“老漂族”不僅在家庭內(nèi)部缺乏話語(yǔ)權(quán),也在更廣闊的社會(huì)文化空間中面臨“失語(yǔ)”困境。
如何回應(yīng)這一困境,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公共議題。這不僅需要政策和社會(huì)制度的支持,例如建設(shè)更普惠的托育與養(yǎng)老體系,減少家庭對(duì)子女與父母之間的過(guò)度依賴;也需要倡導(dǎo)家庭成員能夠理解與承認(rèn)“老漂族”的個(gè)人需求,對(duì)其給予更多尊重與空間。
更為關(guān)鍵的是,應(yīng)當(dāng)讓“老漂族”們?cè)谖幕a(chǎn)中發(fā)出自己的聲音,讓真實(shí)需求被聽見,而不是被家庭理性或道德化的敘事掩蓋。影視劇、新聞報(bào)道和公共討論都應(yīng)展現(xiàn)多元化的老年生活選擇,而不是簡(jiǎn)單地把父母不幫忙帶孩子描繪為家庭關(guān)系緊張、老人自私或能力不足的“異常行為”。通過(guò)這樣的文化表達(dá),社會(huì)才能理解老漂族的委曲求全,停止“以家之名”來(lái)壓抑他們對(duì)尊嚴(yán)與自主的追求。
當(dāng)“老漂”說(shuō)“我想回家”,這并非一句簡(jiǎn)單的鄉(xiāng)愁,更是一代人對(duì)家庭責(zé)任與個(gè)人自由的艱難權(quán)衡,是在矛盾中爭(zhēng)取到的一點(diǎn)點(diǎn)主動(dòng)。它提醒我們:老年生活,不應(yīng)只是犧牲,更應(yīng)包含選擇。真正的社會(huì)進(jìn)步,不是讓老人無(wú)條件地“為家操勞”,而是當(dāng)他們說(shuō)“我想為自己活一活”時(shí),社會(huì)和家庭能真誠(chéng)地說(shuō)一句:“這很正常。”
每個(gè)人都會(huì)變老。給老漂族一個(gè)可以說(shuō)出自己心聲的空間,不只是為了他們,更是為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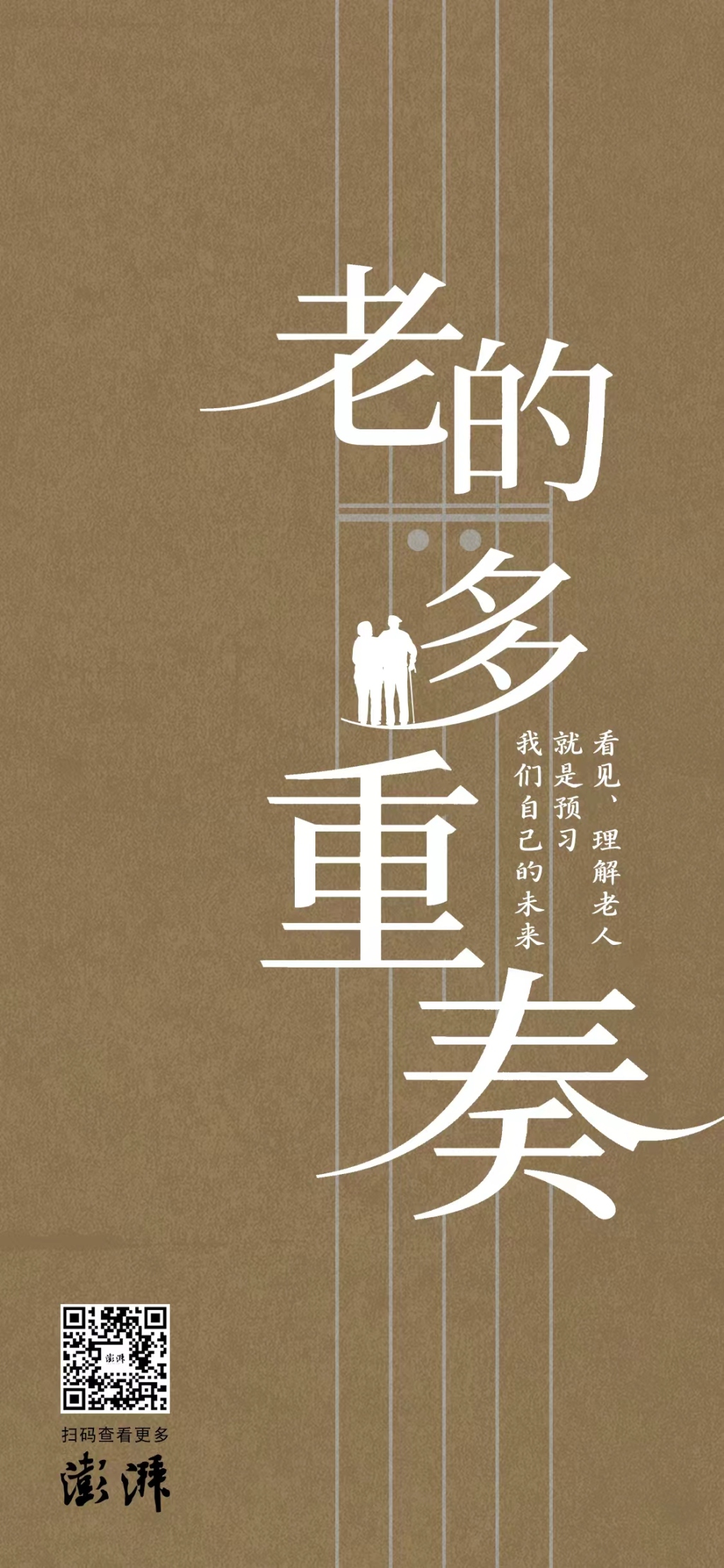
參考文獻(xiàn):
李永萍.“學(xué)會(huì)做老人”:家庭轉(zhuǎn)型視野下的農(nóng)村老年人危機(jī)——基于北方農(nóng)村的分析[D].武漢:武漢大學(xué),2017.
陳英姿,趙玉港,胡亞琪.社會(huì)融合視角下中國(guó)老年流動(dòng)人口居留意愿的影響因素[J].人口研究,2022(1):97-112.
黃麗芬.進(jìn)城還是返鄉(xiāng)?——社會(huì)空間與“老漂族”的自我實(shí)現(xiàn)[J].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2019(11):4-14.
梁宏.戶籍、代際及年齡層差異視角下的務(wù)工經(jīng)商型流動(dòng)人口[J].南方人口,2019(2):1-15.
Yan Y. Familial Affections Vis-à-Vis Filial Piety: The Ethical Challenges Facing Eldercare Under Neo-Fami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J].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 2023(1): 5.
澎湃新聞.專訪丨閻云翔:從新家庭主義到中國(guó)個(gè)體化的2.0版本[N].(2021-08-03)[2024-04-01]. http://www.ditubang.cn/newsDetail_forward_13743892.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