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杭侃:遺產即是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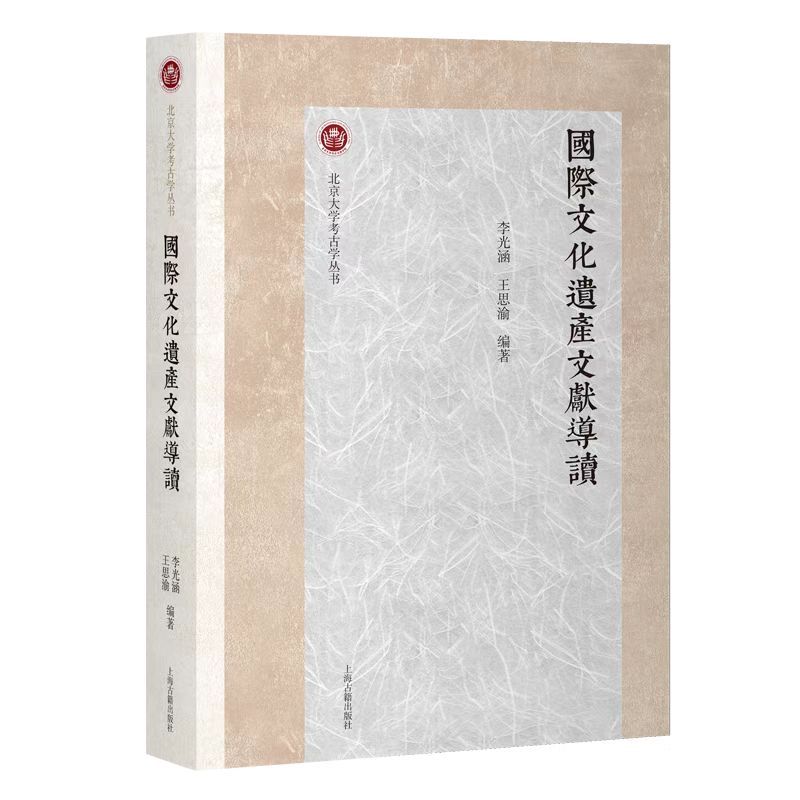
《國際文化遺產文獻導讀》,[新加坡] 李光涵 王思渝 編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4月
我的專業是考古,1998年去上海博物館工作之后,開始接觸公眾,這些年來考古與公眾之間的關系問題一直縈繞在心,所以幾年前我看到羅德尼·哈里森的著作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的時候,就組織一些在校學生進行了翻譯,即202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批判性思路》。這本書的前言《遺產無處不在》提出了一些我們關注的問題:
難道沒有別的比“過去”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們去思考嗎?把遺產放到一個特定的歷史情境下,作為一種社會、政治與經濟現象考察,我希望不僅能探討自20世紀70年代實施《世界遺產公約》以來遺產與我們之間發生了什么樣的大變化,同時也表明,遺產最重要的不是關乎過去,而是我們與現在、未來的關系。
現在,北京大學兩位青年學者李光涵、王思渝組織全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一批青年學者撰寫了《國際文化遺產文獻導讀》。編著者在編后記中說:編輯初衷是“作為長期在高校從事文化遺產研究與教學工作的學者,日常中我們經常被問到的問題之一是,文化遺產研究是一個學科嗎?”在現在高校的考核壓力下,他們關注這個問題是很自然的。遺產無處不在,又與現在、未來發生著關系,按照常理,遺產相關的研究應該在高校中受到重視,因為只有高校及時為社會培養合格的人才,才能夠應對不斷變化社會中的人才需求。
中國高校中的遺產研究最初脫胎于考古研究。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大規模基本建設中考古工作的需求,考古專業人才奇缺。1952年北京大學在歷史系下創辦了新中國第一個考古專業,并在國家文物主管部門的指導下,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開辦了四期考古人員短訓班,為新中國的考古事業培養了一批亟需的人才。改革開放后,隨著大規模基本建設的開展,國內迎來了新一輪的建設熱潮,山西大學、鄭州大學等高校陸續創辦考古專業。1983年,北京大學考古系獨立建系,這個時期基于田野發掘的考古工作仍然是文物事業發展的重點。經過幾十年的積累,2013年,考古學從歷史學的二級學科成為獨立的一級學科,標志著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的逐漸成熟。隨著國力的增強,除了考古的發掘與研究之外,文化遺產本體的保護、博物館的展示闡釋、與當代社會的協調發展等一系列問題,都擺在了我們的目前,這些均不是傳統考古學研究的內容。高校學科建設受到學科評估的強烈影響,而學科評估評的是那些比較成熟的學科,但是現實社會中許多亟待研究的問題,卻會因此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比如文化遺產由于沒有成熟的學科體系,年輕學者的文章很難找到所謂的核心期刊發表,這是造成我國高校人才培養和社會需求脫節的表現之一,在此情境下從事遺產研究的年輕學者在高校不得不面臨更大的生存壓力。
《國際文化遺產文獻導讀》的編者認為:“‘文化遺產研究’能否成為一門成熟乃至獨立的學科的問題,至少需要回答,這門學科能夠解決哪些已有的學科所解決不了的問題?它契合的是怎樣的時代發展需要?”基于此,他們編選了國際文化遺產學界四個方面的經典著述,第一部分便圍繞著“價值與保護”,介紹了李格爾、勒-杜克、卡博納拉、布蘭迪的保護理論;第二部分便圍繞著不同的遺產類型而展開,這些遺產類型是隨著國際遺產保護運動的深入而擴展出來的;而今天意義上的“保護”已經不可避免地涉及不同的利益相關方,已經不是,也不可能再是純粹書齋里的學問,展示闡釋、活態傳承、社區參與、文化旅游乃至文化經濟,都已經成了今天的保護運動必須面對的問題,這些問題也使遺產的話題更有批判研究的需要。
《國際文化遺產文獻導讀》讀后使人思考良多。書中介紹的第一部著作是李格爾的《對文物的現代崇拜——其特點與起源》。正如標題所示,對古物的現代崇拜確實說明它并不是一種古已有之的傳統,雖然我們能夠把對古物的收藏追溯到很遠,收藏意味著喜歡,但喜歡還不是崇拜。這種崇拜帶來了不同的保護理論和保護實踐,所以,“保護”是伴隨著西方現代性成長起來的概念,并隨著“二戰”之后的國際化協作的開展,在全球推廣開來。
勒-杜克參與了巴黎圣母院的修復,他認為“修復一座建筑并非將其保存、對其進行修繕或重建,而是將一座建筑恢復到過去任何時候都不曾存在的完整狀態”,這種觀點自然會引起激烈的討論(從這一點來說,編選者應該對拉斯金的理論予以介紹)。我也一直在想:勒-杜克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修復理念?他是不是在構筑一種建筑風格的理想狀態?這種理想狀態有點“不可思議”,但是,如果我們把它放在中國建筑師對民族建筑風格的追求,這樣一個層面進行思考,也許能夠更好地理解勒-杜克的做法,雖然在不同的建筑師眼中,民族風格是不一樣的,梁思成有梁思成的做法,貝聿銘有貝聿銘的設計,但是他們心中其實都有一種“執念”。
布蘭迪是遺產保護理論界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雖然布蘭迪基于高雅藝術作品展開的修復理念在相當一部分人看來已經“過時”,但是其跨學科思考聯結了形而上的藝術哲學與形而下的材料世界,仍然是我們思考藝術作品必須思考的方向。在《和卡爾米內論繪畫》中,布蘭迪認為:“藝術作品,是人類為了超越自身短暫存在而付出的最高努力,通過抵達永恒中的不變之法,使人類自身從時間中獲得解脫。”
在我看來,藝術品的創作與宗教活動具有相似性,宗教是人類構筑神圣世界的活動,藝術也是。只是布蘭迪認為:“這種努力一旦實現,作品本身就脫離了創造者之手,它被封裝起來,成了完成時態,從(生成)中獲得解放,然后被持續不斷地拉向接收它的當下意識。”為了解釋清楚藝術作品的這種特征,布蘭迪引用了杜威的美學論證:“一件藝術作品,無論多么古老或經典,只有當它活在某些人的個體化經驗中,才實際上是一件藝術作品,而不僅是潛在的藝術作品。”在我看來,藝術品肯定存在于人的個體化體驗當中,但是,它的藝術性同樣存在于現代國家和社會的建構中,概言之,我認為文化遺產的價值既具有客觀性,也具有主觀性,并且通過國家、社會、個人不同的層面,與當下發生著聯系。
世界遺產保護運動的發展使得更多的遺產類型被納入研究和保護的視野。2008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第十六屆大會通過了《關于文化線路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憲章》。作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遺產學界對文化線路長期理論研究和保護實踐的總結性成果,《憲章》厘清了文化線路的概念和內涵,中國絲綢之路、長城、大運河也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但是在我看來,文化線路還有繼續討論的空間。如果說大運河、絲綢之路構成“路”,長城并不是“路”,討論這個方面的內容,可能還要涉及線性遺產和線狀遺產,比如明代為了抗倭而在沿海地區修筑了許多衛所城,這些具有軍事防御性的城堡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防御體系,但又沒有一條直接的交通線將其串聯,聯系它們的更多的是支撐它們的腹地城鎮和聚落。
書中第四部分編選的批判遺產的幾篇文章具有足夠的批判性。美國學者大衛·洛文塔爾于1985年出版的《過去即異邦》一經出版,便立刻引起了英美人文學界的廣泛關注。1992年10月31日,英國曼徹斯特大學便邀請洛文塔爾參加一場以“過往即是異邦”為題的辯論會,可見其學術上產生的影響。書中值得探討的論題很多,重新回到李格爾的《對文物的現代崇拜——其特點與起源》,這種崇拜導致“遺產無處不在”,甚至在2014年,庫哈斯出版了一本名為《保護正在壓倒我們》的書籍,宣稱“當下幾乎沒有辦法來與我們巨變和滯脹并存的未來談條件”。那么,我們究竟為什么要產生這種崇拜,甚至發展出一種壓迫感呢?我想其實源自人類靈魂深處的焦慮和吶喊。隨著現代性的產生,“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向哪里去?”的靈魂追問就沒有停歇過,對遺產的保護其實是人何以為人的探究,在0和1構成的怪獸在人類面前越來越有壓迫感的時候,我們需要回望過去,重新構筑我們的神圣世界。如果說哲學就是懷著鄉愁的沖動去尋找精神家園,那么就可以說:
過去并非異邦
遺產即是故鄉
杭侃
2025年4月16日于山西大學
(本文系作者為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北京大學考古學叢書”《國際文化遺產文獻導讀》所作序,澎湃新聞經授權發表。)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