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身為女兒,為什么抗拒成為像媽媽一樣的人?|翻翻書·送書

在生下我的那一刻,聽到醫生說“是女兒”,
我媽一下就哭了。
每個女性似乎都經歷過這樣的時刻:身為女兒,對來自母親的關心感到難以招架,卻也同樣無法完全將之割舍。
在當下的生活語境中,“母親”是一個格外特別的名詞。對于媽媽關心的嘮叨,我們總認為“她根本不懂我的苦衷”。對于母親的話語中種種隱形的控制、疼痛、呼喊、渴求,我們看到了陷阱,卻不由自主地一遍遍回到她們身邊。
究竟什么是母愛,又是什么讓我們無法成為像母親一樣的女性?在這個女性普遍覺醒,奮力追尋更自由輕松生活的當下,我們似乎也亟待回過頭去,看看背后那群追不上我們,卻又與我們血肉相連的女人。
母女關系一直是個古老的命題,也被認為是人際關系中最為復雜的一種,女兒們始終很難割舍與她們至親至疏的母親,但又常常從母親那里收獲失望和頹傷。
不得不面對疑問,不能不給出回應,“不得不”的背后,纏繞著欲語還休、復雜變幻的愛。
這本《中國式母女》開始于2024年初《三聯生活周刊》的一次選題會,幾個記者聊起一本女性題材的小說,不知怎么話題一轉,大家開始談論各自和媽媽相處的方式,母女關系成為那場聊天的關鍵詞,也直接啟發他們做了一期封面專題:《母女關系》。
但母女關系這個話題不是一期雜志就能談完的,這些采訪、對談、聲音,匯聚成了這本《中國式母女》,我們在里面可以讀到記者們深入采寫的母女故事,這些故事發生在不同年齡階段、不同職業、不同地域的母女之間,真切、細膩,且勇敢、坦誠。
本期翻翻書活動,就為讀者們帶來這本譯文紀實系列的新書《中國式母女》,去看一看最為復雜,也最為深刻的親密關系——女兒與母親。
(以下內容摘自《中國式母女》,編輯過程中略有刪減,經出品方授權發布。)
參與贈書活動可直接滑至底部,8月12日當天我們會選出3名讀者,請留意公眾號文章的回復。
你愛我嗎?你會恨我嗎?
文|卡佐卡
時間已過去23年,每當盛夏來臨,蟬鳴響起時,我的心仍會朝下一沉。直到高中畢業,暑假總是我最難熬的日子,因為在這62天的時間里,我必須日復一日,全天候地和母親相處。從睜眼開始,我就要判斷母親這一天的心情:如果她從廚房出來時的腳步聲很輕,客廳里放著廣播,在早餐前就和我說話,那么至少我能度過一個輕松的早晨。但如果她趿著鞋,重重地把馬克杯放在玻璃茶幾上,一言不發,我就會盡可能地不發出任何聲音走過她的身邊。更多時候,判斷母親心情好壞的條件并不那么明確,它更像一種隱約籠罩在她身邊的光暈,全要靠我的經驗去猜測。這樣的夏天從我的童年一直持續到成年前。
小時候,媽媽總會不斷問我,你愛我嗎?也常問我,你會恨我嗎?她這么問的時候看起來非常疲倦,好像她為了索要一個自己也能相信的答案已經忍耐很久了。但她的眼神不知疲倦,總是很鋒利。那時,在一年里最熱的日子里,我身后往往會傳來無休止的蟬鳴。一開始我哭著搖頭,扭頭逃避掌心和指節;后來長高,到她的胸口那么高,她抄起遙控器扔向我的額頭,我已不會躲也不會哭,只是把身體交還給母親,不說愛,也不說恨;再后來我終于能平視她,同她一樣扯高嗓子,據理力爭,渾身發抖。直到我16歲后的某天,母親突然停下,不再詢問我那些問題。
可每年的第一聲蟬鳴傳來時,我仍能隱隱從中聽見母親的聲音。和6歲時聽見的聲音一樣,反復確認:你愛我嗎?你會恨我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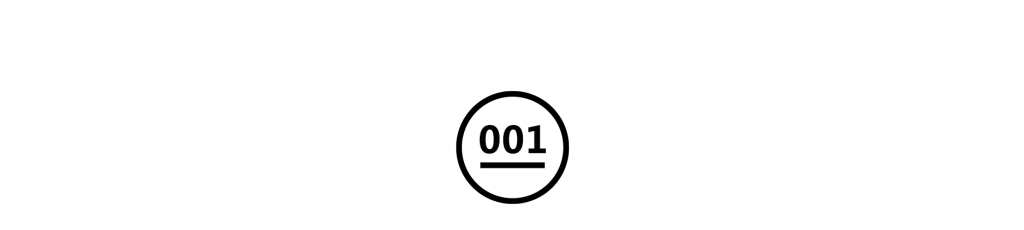
我永遠無法達到母親的要求
母親對我做過最好也是最壞的事,就是給了我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說我不喜歡她。鈴木涼美筆下那種在小孩發燒生病時不會怒吼卻會為女兒熬一碗病號粥的母親,曾是我6歲時幻想的母親。我的母親并不是這樣的人。我幼時體弱多病,是醫院的常客,屢次進出,幾個月下來就耗盡了她本就不多的耐心。我常常咳嗽,夜里躺在床上遲遲無法入睡,迎來的往往是陣陣更劇烈的咳嗽,咳到肚子酸痛,冒出眼淚。母親出于母親的義務睡在我身邊,同時又因被我驚醒而做回她自己。“你為什么就不能停下來?”她吼道,拳頭和巴掌落在我的背上,也落在我的臉上,“你為什么就不能別咳了?”
我因為喘不上氣而無法回答。當我重新躺回床上后,母親在一旁說話。她的聲音朝著天花板,第一次問我:你會恨我嗎?這是一個開始,從此她就經常這么問我了。往往是在收起巴掌、拳頭、木棍之后,看著我的眼睛這樣問我。她也會在怒吼和尖叫后這樣問我。她會要求我對同學和老師撒謊,說我身上的淤青和疤痕都是摔跤時弄的,并在我點頭答應后這樣問我。我在那時候意識到我無法回答母親的問題并不真的因為我喘不上氣,而是我確實,從內心深處,認為這是我無法回答的問題。 6歲開始就無法回答,并且早早預料到等我長大以后也依舊無法回答。
我的母親并不是常見敘事里的家庭主婦。那種刻板形象往往指向沒有經濟能力,依賴丈夫的權威,無法從暴力中拯救自己的孩子——而我的母親就是家庭中的暴力本身。但同時,她身上沒有那種常與暴力捆綁在一起的特征,比如愚昧無知,或是欺辱弱小。母親也從不吝于為我提供經濟上的支持,鼓勵我學習與閱讀。在她身上,還有很多如今在社交媒體上被褒獎的特質——尤其當她身為一個母親和一個女性時。她聰明勤奮,是外婆的驕傲,也是那條弄堂里唯一的大學生,工作后業績出色,在同事間口碑極好,一度辭職創業,收益頗豐,婚后表面上回歸家庭,但也掌握了家里的財政大權,對金融股票一類的投資事項也算有些研究。她堅持家務分工或者請鐘點工,鄙棄傳統主婦的生活,不屑家務事,與鈴木涼美筆下瞧不起周圍家庭主婦的母親形象如出一轍。可以說,她在沒有接觸過任何女性主義思潮的時候起便完全貫徹著這樣的理念生活,二十多年來從未改變。因此,我自小就免于那種“女孩就不應該讀太多書,長大后得趕緊嫁人”的詛咒。但不可避免地,我墜入了另一種詛咒——我永遠無法達到母親的要求。
優秀是應該的。100分只是暫時的,難的是永遠第一,永遠 100分。97分是恥辱,92分就該滾出家門,我的名字應該待在榜首,任何其他地方都是不可容忍的。從4歲學琴、6歲上小學起,她親自教我各類學科,送我去參加奧數競賽班,補習英語口語,同時監督我練習鋼琴,每年暑假參加考級。我面前的試卷從 6歲時就如流水般源源不絕,錄音機里的磁帶嘎吱嘎吱放著聽算題,兒童套餐里的玩具尺因為母親打在我手臂上太用力而斷成兩截。
在我長大成人之前,甚至直到如今,母親都從未給過我一次情感上的支撐。她倔強,頑固,強勢,自信,果斷,對我來說,母親就像是一把不斷在我身上拉扯的銼刀,試圖把我打磨成她人生中應有的完美女兒,好比打造一個她親手啟動的項目。我從很小的時候就知道,我的煩惱是不能和母親訴說的。不再優秀的名次,成績沒有進步——她比我更惱火,更要指責我不努力不用心。人際關系不順利,朋友沒有理由地疏遠了我——你為什么總那么敏感?她查看我的手機,翻到同學的告白短信,罵我下賤,不要臉。她偷看我的日記和小說,甚至懶得擺回原樣,上面掩飾用的筆記本疊得很亂,她引用我日記里的話,口吻冷靜,一臉無辜地問我是不是覺得她不愛我,卻又演技拙劣。高三時我一天只睡三個小時,拼命學習,并不真的是為了考上自己心儀的院校,而是從內心深處知道,如果我沒有考到一個足夠體面的學校,未來幾十年我都無法從母親的失望里逃脫。但母親當然不會因為我滿足了她的期待而滿意,她始終掐著一個秒表,并對我不斷產生新的失望。
我的母親從來都不是溫柔,無私,樂于奉獻的。她在別人眼中風趣獨立,包容謙和,優雅美麗,卻是一個只在我面前才會出現的瘋女人,她咒罵我,鄙夷父親,卻又反復要我們愛她,并且證明我們愛她。她很聰明,也因為聰明而知道如何傷害他人。我在那時發誓:長大后,我絕不會成為母親這樣的人——我要竭盡全力保護自己,然后逃走。我的身體生來必須成為她的女兒,但我的頭腦是自由的,只要我堅持,我就能保有真正的自己而不會成為她。
大學畢業后,我出國念書,離家的一年多里,我沒有打過一次電話或者視頻。有時看見室友在做早餐時還要和母親打視頻,我就覺得不可理喻:那些雞毛蒜皮的事有什么可說的?為什么做個早飯還要和媽媽打電話?可在聽見她對著母親撒嬌時,我卻愣住了。那是我和我的母親之間從未有過的對話。我知道這種親密的、無話不談的母女關系是存在的——但在那之前也僅僅只是知道而已,當它真正呈現在我面前時,我才第一次直觀地看見我缺少了一些什么,并意識到在我過去的成長中,我往往都在別人而非母親身上尋找這種我渴望的關系。從捧著我腫脹雙手的鋼琴老師,偷偷送我毛絨玩具的班主任,到給予我極大耐心的保健老師,鼓勵我的語文老師,我始終在不斷伸手,從身邊取下一些我幻想中母親會給予我的東西:愛,無條件的愛,寬容的愛。我母親口中的愛并不是這樣的,寬容就是縱容,是懶惰。她說她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真心希望我好的人,為此她給我的愛是嚴厲的愛,是充滿譏諷、羞辱、疼痛的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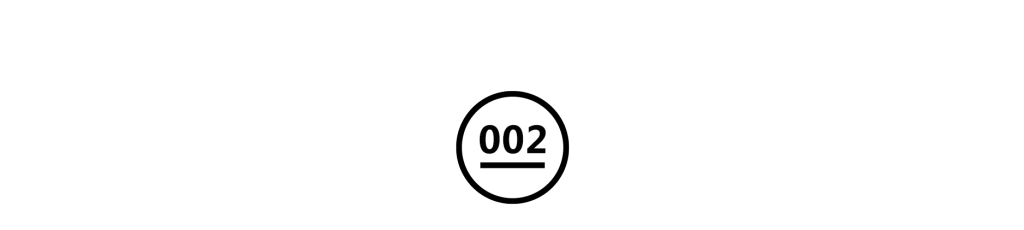
我決定不再逃開了
27歲時,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我被迫在上海的家中與母親再次朝夕相處了整整兩個月,好像童年過分漫長的暑假卷土重來。那時,我已經短暫地談過戀愛,分手,建立過深刻的友情,也被友人絕交過。我逐漸發現在我的心底有什么確實不對勁— —哪怕我曾那樣努力地說只要我自己堅持,我就不會被母親塑造成她想要的樣子,但我仍然在對抗中不可避免地擁有了她的一部分。
我常常想到她會說自己多么愛我。而如果這就是真正的愛——如果這真的是真正的愛——那我這輩子就絕對不會主動尋求任何愛。難怪我從來都不相信別人口中對我的愛意,以至被人覺得冷漠,被指責有一顆捂不暖的心、怒叱我自私,以自我保護的名義傷害他人的感情。“愛”只會讓我想要逃走。
在又一次母親大發脾氣沖我怒吼時,我面對緊閉的防盜門無處可逃,忽然很疲倦。好像自己一下子理解了童年時,母親問我會不會恨她時一樣的疲倦。我發現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對話過。我們的閑談總是些無關緊要的話題,而二十多年來一旦我們要真正面對自己的情緒,談論彼此的事情時,她就總是在怒吼,而我不得不條件反射般地用一種漠然的態度保護自己。這好像已經成為過去我們談論自己的唯一方式。但從那天開始,我決定坐下來,和她對話。我問:媽媽,你為什么要生我呢?
母親給出的回答簡單得像在敷衍:我們那個時候哪想那么多亂七八糟的,結婚之后就該要孩子了。
我那時候想,原來“孩子”是一種理所當然的產物,是社會時鐘里她人生必經的下一步。母親以她認為絕對正確的尺度來丈量我的人生,所以會指責我性格強硬,不可理喻,無法經營好一段戀愛關系并踏入婚姻,畢竟在27歲那年,她已經把我生下來了。
我那時才意識到,我已經到了媽媽生下我的年齡了。我從來沒有告訴過媽媽,我頻繁的噩夢之一就是我懷孕了。因為懷孕,我的身體浮腫,皮膚皺巴巴的,膝蓋很痛,走起路來一搖一擺,又因為向來笨拙,四肢總是撞得青一塊紫一塊的,就好像6歲的我。我的夢里沒有丈夫,只有一個因為到了27歲所以懷孕的自己,帶著恐懼,獨自光腳走在路上。我腹部表面的血管像大地龜裂的花紋,肚皮里沒有呼吸也沒有擺動,只有我不知道的東西從內部凝視著我。醒來時,我常常渾身冷汗,久久不能入睡。
我告訴母親,我沒有辦法想象自己成為一個母親。她很驚訝,反問我:在成為母親之前,有人知道自己會成為什么樣的母親嗎?那天我們聊了很久,不能說是溫情的,更像是彼此冷靜地交換我們眼里的世界。母親第一次談到她自己的童年。她說因為她還有個弟弟,因此她感到外婆所有的愛都是流向弟弟的,而她必須非常非常努力,永遠考到第一,永遠把所有人都甩在身后,才會得到夸獎。她談到外婆對我的寵愛,說起有一次她在外婆面前吼我,結果自己反倒被外婆大聲責備——她以前明明不是這樣的,母親望著我說,幾乎是憤恨地。那一刻她好像是在嫉妒我從外婆那里得到了她過去渴望但從沒得到過的東西,就好像一些我也從未在她那里得到過的東西。
我從那一刻開始理解母親,雖說那只是一個開始,但畢竟不再逃避了。我意識到那些暴力的源頭都來自焦慮,來自一個有才能的人面對擁有孩子前后生活的落差,不甘瑣事卻被迫沉入其中的郁結,被社會時鐘追趕而無法停下的緊張,渴望女兒能實現她另一種人生的期許,在匱乏中體悟著不甘與嫉妒長大又被人生驅趕著要去給予愛的迷茫。也就是從這一刻起,我內心那個不存在的完美“母親”也隨之消亡了。
從俄狄浦斯王的故事開始,人們常常談論兒子的弒父,卻從未提出女兒的弒母。因為父親不是天然成為父親的,所以它可以被簡化成一個符號,一種權威的象征,它更具有正當性,故而被頻頻以不同方式演繹千年。而母親在傳統敘事中往往會天然成為一個母親,它是一種對女人的桎梏,化作母職懲罰著那些成為母親的女人們,但同時也束縛著作為女兒的我們。
身為同樣會成為女人的孩子,你怎么能憎惡自己的母親呢?你從她十月懷胎的肚皮里出來,就算她不是天然地愛著你,你也要天然地愛著她,無論母親是個怎樣的人,會帶來什么樣的愛或者什么樣的傷害,人怎能不愛自己的母親?如果說弒父意味著抗爭,象征著兒子抹去父親的至高地位并取而代之,創建新的秩序,那么人們避之不談的弒母背后大概是一種深刻的理解吧。一旦抹去理想中女人應成為的“母親”,否認與生俱來的無條件的愛,母親在我面前便只是個和我一樣的女人。從理解她的那一刻起,她作為母親的神圣性便已不復存在——只有圣人才能無條件地愛人,而母親也不過是別人的女兒。母親和我們是一樣的。
那之后我與母親的對話漸漸多了起來,雖然有些生硬,有時也并不愉快,但我不再逃走了。我從沒有懷疑過母親對我的愛。我只是懷疑愛本身并不純粹,懷疑母親不因我是我而愛我,懷疑她的愛永遠伴隨著標準與籌碼,我更懷疑的是我對母親的愛,并且對我曾經無法回答她的問題而不安。母親問我會不會恨她時,是不是也和我抱有一樣的懷疑呢?這樣想著,過年時我久違地擁抱了她。她很瘦,從我記事開始一直都這么瘦,我小時候不喜歡她的擁抱,因為總是硌得我很疼。如今我和母親一樣高了,能夠直視她的眼睛,也能看見她半白的頭發。回家前我給她買了新外套,什么都沒有說,但她看起來很高興。
如今我仍在試圖理解母親,并不斷質疑自己的猜測——母親真的是這樣想的嗎?更重要的是,母親愿意誠實地面對自己嗎?就算我們開啟了真正的對話,試圖彼此理解——我會相信她嗎?在她誠實地講述自己之前,我永遠都不會知道。而我仍抱有期待,并決定不再逃走,迎接只屬于我們的對決。
▼ 第五十期書目:《中國式母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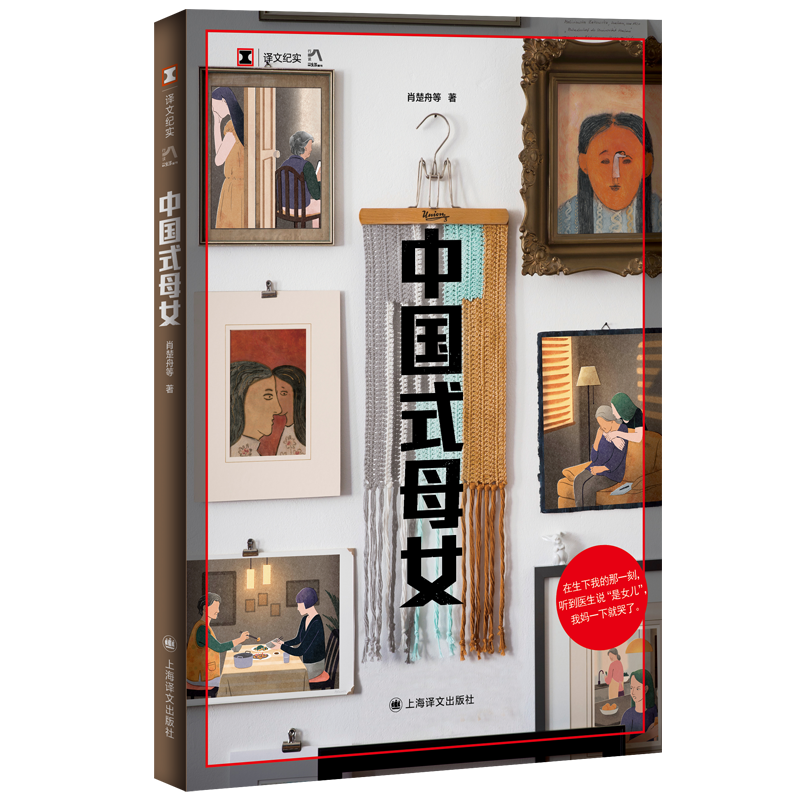
《中國式母女》肖楚舟等 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6月出品
★ 在成為“母親”或“女兒”之前,每一位女性首先是她自己。
★ 她可以后悔成為一個母親,她可以為過于嚴厲或過于沉重的母愛而痛苦。
★ 《中國式母女》的作者們以“沒有標準答案”的包容視角,坦誠地訴說自己的經歷與思考,呈現母女關系從對抗到和解的多元可能。
★ 消除對母性的神化,讓母女關系回歸為人際關系的一種,愿每一位在母女關系中困惑的讀者,在閱讀的共鳴中找到重新理解彼此、解放自己的鑰匙。
▼ 書籍簡介
對于母親來講,母愛是一種天性嗎,是否需要學習?母職,是一種被天生賦予的使命,不可回避,還是一種個人選擇?
對于女兒來講,和母親的相處,除了天然的血緣、親情聯結,是否也是一種女性之間的相處?如果是這樣,為什么我們和女性朋友或長輩能夠深入探討的話題,面對自己的母親卻往往難以啟齒?
母女關系是人際關系中最為復雜的一種,是一個古老的命題。在尋求自我與尋求依戀的矛盾中,她們往往是最熟悉的對手,也是最堅固的盟友。
當下,一方面我們身邊的母女關系越來越多元;另一方面,整個社會對于母女關系的認知和討論,被放置于更復雜的語境和維度,既尖銳又模糊。來自學者、女性創作者以及我們身邊普通母女的故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青年一代對于親密關系和家庭關系的理解,以及近年來女性精神處境、性別意識的真實樣貌。
▼ 作者簡介
采訪記者
肖楚舟,《三聯生活周刊》主筆,2016年起為周刊撰稿,2022年成為周刊文化記者。
孫若茜,《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在周刊多年從事以文學領域為主的文化報道。
段弄玉,《三聯生活周刊》記者,關注心理、教育和年輕人的生活方式。
卡生,《三聯生活周刊》記者。
孫雅蘭,《三聯生活周刊》記者,長期從事文化領域的報道。
陳璐,《三聯生活周刊》主任記者,關注藝術與文化,也在寫作中靠近自己與母親的關系。
▼ 如何參與共讀?
希望你
1、關注人類學、社會學等相關話題,或對母女關系有自己的思考,具有獨立的判斷和思考能力
2、有表達的欲望,能用文字表達內心的感受
3、尊重彼此的時間,遵守我們的約定
▼ 你需要做
1、前往“湃客工坊”微信公眾號,在文章評論區告訴我們為什么想讀《中國式母女》,包括但不限于你對相關議題的了解及興趣。截止時間為8月12日12時。
2、8月12日當天我們會選出3名讀者,請留意公眾號文章的回復,并及時添加“湃客小助手”微信,發送地址和聯系方式,我們會第一時間郵寄圖書。
3、在10天內(從收到書當日起計)把書讀完,發回800-1000字的評論。你的文字,將有機會在澎湃新聞客戶端及“湃客工坊”微信公眾號上發布。如果你成為當期的圖書推薦人,我們將邀請你加入“湃客讀者”微信群,讓你與來自各行各業的喜歡閱讀、享受思考、愿意表達的讀者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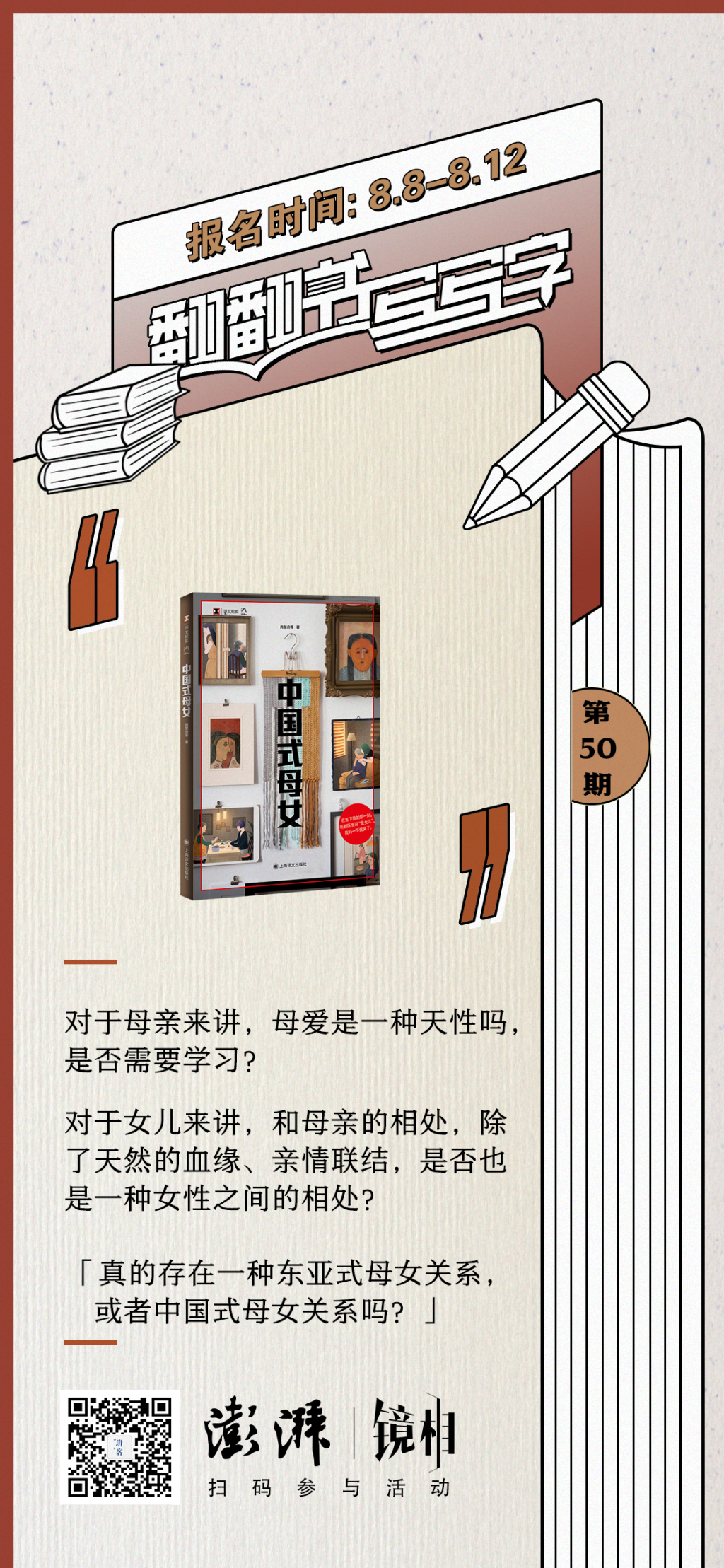
策劃/吳筱慧 實習編輯/周鐘元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