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出租屋文學”里有什么?遷徙世代的家庭想象 | 漣漪效應

畢業季一向是租房旺季,這個夏天,又有一大批年輕人即將搬入自己人生的第一個出租屋,他們會在這個空間里完成自己新舊身份的轉變——成為一個社會人,也將基于此地,向更廣闊的城市空間進行探索。
在倡導生活美學的小紅書上,出租屋改造始終是大熱的詞條:“樓道破,關我屋里什么事?”、“爆改30㎡老破小”、“媽媽以為我在上海出租屋過得很慘”……大量關于漂泊與租房的感受、經驗和段子被批量炮制出來,形成一種獨特的“出租屋文學”。租房的生活意味著脆弱、變動、漂泊、不占有,也意味著一種輕盈的力量,意味著變革與流動的可能性。脫離大家庭在異鄉獨自生活,在大都市的出租屋里,有著屬于成年人的“后青春期”嗎?從千禧年初《蝸居》《裸婚時代》《北京愛情故事》中的出租屋,到如今的“出租屋文學”,出租屋這一特殊的空間所承載的意涵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作為遷徙的世代,今天的我們如何理解租房這件事?
通過討論、想象一種“租”的生活,我們期待看見更多格外的活法。
以下為文字節選,更多討論請點擊音頻條收聽,或【點擊此處前往小宇宙App收聽】,效果更佳。
【本期嘉賓】
夏周
文學編輯,播客《席地而坐》主播。
普照
文學編輯,編輯有非虛構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遞》等。
【本期主播】
柳逸
澎湃新聞·鏡相工作室 非虛構寫作編輯
【收聽指南】
08:38 精致又懸浮:上海梧桐區生活圖鑒
16:08 疫情之后,我和社區的鏈接感更強了
20:08“媽媽以為我在老破小過得很慘”:出租屋文學在反抗什么?
26:55 愛情地獄or友誼烏托邦?出租屋寄托了千禧年初的家庭想象
32:59 蕭紅、魯迅、沈從文、張愛玲......滬漂作家與黃金時代
42:15“東京8平米”如何可能?年輕人為何涌進酒店洗衣房?
48:42 706社區、定海橋互助社......生活可以是一場實驗嗎?
53:00 韓國的出租屋文學:“半地下”里的露餡人生
【本期福利】
歡迎在小宇宙單集評論區留言,我們將選取一位聽眾送出圖書盲盒一份!
【本期配樂】
591——鄭宜農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歡迎通過小宇宙節目主頁公告欄加入“漣漪效應聽友群”,解鎖更多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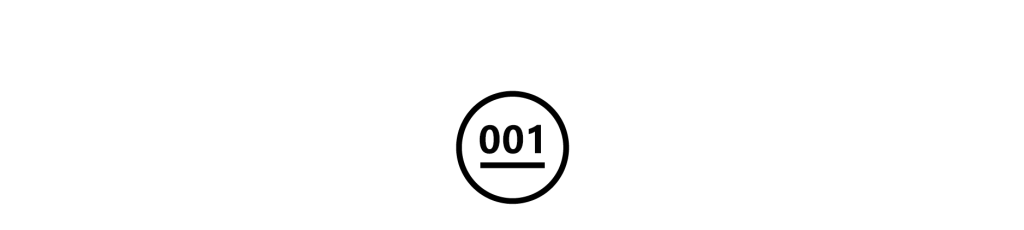
媽媽以為我在上海老破小過得很慘:“出租屋文學”在抵抗什么?
柳逸:
我自己因為用小紅書特別多,經常會發現上面有大量關于出租屋的各種筆記,它已經形成了一種類似于景觀的存在。所以我會給它貼一個標簽,覺得這像是互聯網上的“出租文學”。比如像“爆改30平米老破小”,或者是強調家里家外巨大反差的“樓道破關我屋里什么事?”“媽媽以為我在上海出租屋過得很慘”“上海月租2500能過上什么樣的生活”。關于出租屋改造或者在出租屋里追求精致生活的各種段子正在被大量炮制出來。
我個人的觀察是,千禧年初的出租屋,要么被懸浮成像《愛情公寓》里的那種非常烏托邦的存在,要么就是被污名化。在像《蝸居》這樣的影視作品中,或者在《北京愛情故事》《裸婚時代》中,出租屋多少都被呈現為一種會扭曲美好的一種空間。
而在今天,我們這一代人再去談論和表現出租屋時,很多時代的語境和情緒其實都發生了變化。所以今天我們就特別想聊聊,作為不斷遷徙和流動的一代人,我們怎么看待出租屋。大家可以先聊聊自己的租房經歷,有沒有哪個房子讓你印象特別深刻?你回憶那段經歷時,覺得那個空間為什么會讓你覺得特別難忘?
夏周:
我印象最深的是和朋友在上海“梧桐區”租的房子,因為客廳可以看到梧桐葉,步行還能到武康大樓。雖然那段時間因為個人生活計劃的變化,很想離開上海,但回想起來,還是覺得那個區域很不錯。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搬過去正好是2022年疫情剛結束,我除了被拉進小區群,還進了新華路街道的群。在那個群里看到了很多文化行業的從業者,周末還參加過新華社區營造中心的活動。新華路社區的居民會在那里賣咖啡、冰淇淋、可麗餅之類的,還有一些居民共創的雜志。我就在那些雜志上看到了很多平時活躍在豆瓣和微博上的ID,會讓人覺得生活中文化氛圍特別濃厚。
但在那樣的街區,我又會有一種很強的懸浮感。一方面住在比較中心的位置,可以看到很多象征上海的符號,但另一方面總覺得自己只是暫時住在這里,誰知道一年后會發生什么變化。結果一年后我就離開上海了。
當時剛搬進去收拾房子的第二天,就發現空調插座有點問題。房東叫來了住在這棟樓里的一個比較熱心的爺叔,讓他幫我們清洗修理空調,他一邊洗一邊感嘆“真的好臟”,然后又補了一句,“你們在外打工都不容易,我可憐你們。”所以我現在回想那段歲月時,感受到的是精致又懸浮。
一方面,我可以收獲非常好的城市體驗,而我認為除了上海之外,這樣的體驗很難找到,它有某種特殊性。與此同時,我也會時刻提醒自己,這樣的生活其實并不真正屬于我,我只是獲得了一些美好而時髦的體驗。所以我覺得那段歲月和生活有些懸浮,但同時也非常珍貴,尤其是現在已經離開了上海以后再回看。
普照:
我在現在的這個地方已經住了4年了,我不想搬家了,已經厭倦了搬家的生活,而且在這里甚至還建立了鄰里關系。因為疫情期間,有一位上海阿姨家里的小貓沒有吃的,我幫她買貓糧之類的。她那時家里發生了一些變故,情緒很低落,連去搶菜都沒有力氣,基本上都是我幫她去做這些事。后來她就挺照顧我的。我出去十來天,她會幫我喂貓。我想回禮,她也不要。她覺得這已經是一種很健康的鄰里關系了,這在以前是沒有的。我覺得如果沒有疫情那種特殊的環境,我也不會和這樣一位本地的阿姨有這樣的往來吧。
柳逸:
確實,一些共同的經歷,不管是好的還是不好的,都能幫助你真正獲得一種社群生活,夏周也提到自己是疫情之后才被拉進街道群,好像在公共事件發生之后,才會真正有一種社區的參與感。
夏周:
那時候還有“樓長”,我經常在群里和樓長“吵架”。因為作為租客還是有很多權利無法得到保障,比如發放物資的時候,租客的物資被漏掉了,當時我非常生氣,還在群里和樓長爭論,我覺得作為租戶,自己的權利一定要得到保障。但比較有意思的是,最后我要離開上海時,這位樓長還送了我防護服,當我見到本人的時候,我又覺得這個人似乎變得更加親切了。
有時候我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注重這些微妙的權利。我現在住的房子其實是我買的,我的身份發生了轉變,已經不再是租客了。但是我樓上的一位老爺爺,他對面的房子是租的,有時候他和我講話時,天然帶有一種房主的傲慢。他會說“對面那家常常點外賣,送餐員老是敲錯門”,每次敲到他家時他都特別生氣,然后他還會補上一句,“對面是租的”。哪怕現在我已經不是租客了,我還是會非常不舒服,因為我自己以前也是租客。像這樣微妙的權利,以及你作為權利較低的一方的感受,都非常深刻。哪怕你住在一個很漂亮的地方,擁有很多時髦的體驗,但這種權利的不對等仍然是我當時內心不安的底色。
柳逸:
所以圍繞著這種“割裂感”,小紅書上的網友們就生產了大量的段子。
比如標題是“媽媽以為我在上海老破小過得很慘”,內容是自己在家中非常精致的生活視頻。還有比如“樓道破關我屋里什么事啊?”,大家不斷地在強調,即使生活是臨時性的,是租來的,但仍然要通過改造權、極致精致的生活美學,去對抗這種臨時性和不穩定。
在上海租房其實就那幾種建筑類型,如果你想要獨居,其實你的選擇非常有限。工人新村,就是大家常說的老破小,它是上海非常常見的一種生活形態。在類似這樣的建筑類型中,樓道這個空間承載了大家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一直到現在的生活痕跡,自然是很破敗的。這就是公共空間給人的感覺。但作為租客,你在這里要開啟的是自己全新的生活,于是就有了“樓道破關我屋里什么事”這樣的說法。大家不斷在強調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之間的巨大反差。雖然我的生活是臨時性的,但我好像在這里建立了比那些擁有這個空間的人更好的一種生活。
至于“媽媽以為我在上海住老破小過得很慘”這樣的梗,其實是在強調兩代人對于幸福完全不同的理解。上一輩可能覺得有了房產才算有家,但是對于我們來說,出租屋中的那種幸福正在于它脫離了傳統的大家庭,它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小生活。
還有一種叫做“出租屋文學”的東西,它通常用來形容一種男女關系。比如張曼玉和黎明主演的《甜蜜蜜》,或者是《春光乍泄》這些電影中的愛情給人的感覺,甚至五條人的許多音樂也是這樣,講的是用極致的浪漫來對抗非常貧窮的生活。就像《阿珍愛上了阿強》歌詞里說的,“雖然說人生并沒有什么意義,但是愛情確實讓生活更加美麗。”類似這樣的出租屋文學,呈現出一種關于愛情的觀點:我們的愛看起來很頹廢,很貧窮,但卻非常熱烈。
夏周:
我自己其實也很喜歡點開類似的推文,我嘗試從一個比較積極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拋開那些為了流量而取的夸張聳動的重復標題,我會理解為,這背后展現的是一種很強的生命力,是在有限條件下,熱愛生活的人在努力改造自己的環境。就像我之前說的,租房的時候會有各種各樣的要求,但最后你會發現,必須舍棄其中一些,但你可以積極地改造,讓它看起來沒那么臨時。
之前我聽脫口秀演員Echo講她二姐的生活,里面有一句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話:“二姐把鮮花和桌布帶回了出租屋。”她的段子里,二姐的出租屋應該非常狹小和逼仄,但無論房子多么破舊,鮮花和桌布都是我們用心生活的證明。所以我覺得,“媽媽以為我在上海老破小過得很慘”,這種小紅書上的敘事,其實可以看作是對主流生活的一種抵抗。
那我會想象,媽媽是在什么樣的語境下說出這樣的話的。有可能她是想勸你,大城市生活不容易,所以還是回來過安穩的生活吧。因為買不起房,甚至租不到看起來體面的房子,難道你選擇的生活方式就因此失去了合理性嗎?所以,把外面破舊的空間溫馨地改造,也會成為一種抵抗。“你以為我過得很差勁”,或者在主流社會的敘事中,好像被邊緣化了,過得不幸福,但其實一點也不。實際上,很多女孩是在出租屋里獲得了自由。這種生活很有可能是你小時候住的真正意義上的家,或婚姻生活,都無法給予你的。因此,我覺得從積極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一種抵抗。
柳逸:
我還有一個感受,出租屋和傳統意義上的家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在于它帶給你的時間感是不同的。如果你習慣了流動遷徙的生活,你可能每次搬家時都在不斷舍棄一些東西。你最終會發現出租屋是一個沒有過去痕跡的地方。有些人的家是他和父母從小生活的地方,他也許可以在房間里找到初中、高中等各種時期的痕跡,但出租屋就是一個沒有過去、永遠只有此刻和未來的空間。
由于你沒有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空間,所以在現實層面上,你并不能擁有過去,你只能不斷擺脫“占有”,去過一種非常輕盈的生活。但是這樣的空間給人的感覺,就是你永遠可以面向未來去創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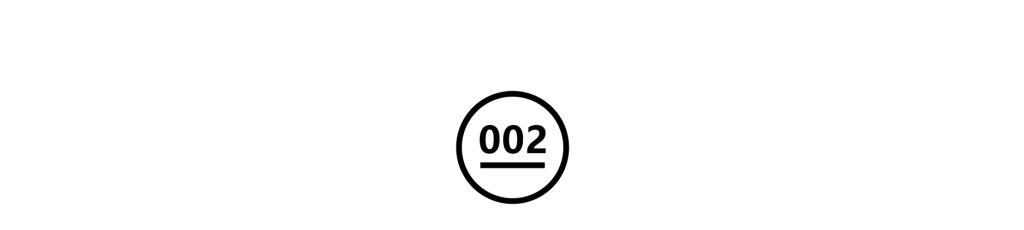
幾代人的出租屋想象:從愛情地獄、友誼烏托邦到心靈家屋
柳逸:
我會覺得千禧年初關于出租屋的影視作品,其實存在兩種非常極端的敘事。要么將出租屋生活描繪得特別美好,比如《粉紅女郎》,以及更早的《老友記》,它們都會有這樣的一個設定——因為種種原因,貧富差距很大的主人公們一起住進了一個大房子。在《粉紅女郎》里,這棟大房子是一棟位于市中心的爛尾樓,是朋友的閑置資產。主人公們在屋子里過著充滿友誼和幸福的生活。在《老友記》中,Monica則是繼承了祖母的公寓,因為美國有租金管制政策,繼承之后的租金不能漲價。總之,主人公們再一次有幸用很少的錢住進非常理想的住房,過上理想的生活。
很多基于出租屋的想象,實際上都是很失真的,要么就是非常扭曲的。像《蝸居》里的主人公海藻,她在這樣的空間里生活,最終走向了墮落。甚至在她成為了別人的情人之后,那個男人還給了她一套公寓。包括像《裸婚時代》,它討論的也是物質的匱乏最終會磨損愛情。
從當時到如今,其實關于出租屋的討論至少變得更加切實際了。我想和大家討論一下,你們覺得從影視作品的脈絡上來看,出租屋所承載的意義有沒有發生比較大的變化?
普照:
這兩個例子都挺極端的,一個是《老友記》,它是一部情景喜劇;另一個是朱德庸的漫畫改編成的影視作品,它的體裁就已經決定了它必須是失真的,或者是有些懸浮的。我想到的是《武林外傳》,它們的共同屬性就是都是某種想象空間,而不是有實質的。
柳逸:
以《老友記》為典型吧,我們總是把以友誼為核心的家庭生活想象寄托在出租屋里,因為這種生活在現實層面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老友記》里Monica的公寓在現實中每月租金是4200美元,而劇情中Rachel每個月只需要付200美元租房。但通過《老友記》,我們實際上可以看到社會對于出租屋寄托了怎樣的情感。
比如說2001年的911事件對《老友記》的劇情走向其實也產生了很大影響。911事件就發生在紐約,所以當時紐約是一個承受了巨大創傷的地方,似乎人人都生活在一種脆弱和不安全感當中。那時候的《老友記》正準備迎來第九季,當時整個劇組面臨的困難是,我們如何在巨大的傷痛中創作喜劇。在這樣的語境下,《老友記》徹底變成了烏托邦。制片人也知道這樣的背景設置非常不現實,但人們非常需要這樣的烏托邦,用以寄托我們對生活的想象,一種友愛、幽默、富有安全感的日常生活。那個出租屋幾乎成了美國人情感上的避風港和安慰劑。
從這個意義上說,《粉紅女郎》其實也很像這樣一個作品,是一種懸浮的烏托邦,展現的是我們當時對一種以友情和愛情為核心的非傳統家庭生活的想象。它好像也成了一個時代的寄托。
夏周:
現在,即使是現實主義題材的電視劇,其實對出租戶的呈現也都挺懸浮的。其實社交平臺上也有很多類似的討論,有人說《三十而已》里的王漫妮,她租的房子是不是太夸張了?或者在《裝腔啟示錄》里,唐影的工資是否真的租得起那個小區的房子?
如果你想了解那些真正真實、更接近普通人的租房體驗,我覺得可以在脫口秀或者《一年一度喜劇大賽》這樣的綜藝里找到,這類內容我也很喜歡看。比如說,邱瑞最開始吐槽他自己租的奇葩戶型房子,上廁所的時候都會被卡住。還有何廣志,他之前分享過出租屋的段子,說自己住在上海7號線最末端,非常偏僻,他吐槽說,每次看到"禁止捕捉野生動物"的牌子都會很感動,因為覺得“這里居然也是有法的”。等到有錢以后,他租了一個比較大的房子,他又說“從客廳走到陽臺就消氣了”。這些感受都非常真實。
普照:
我覺得當代的很多事物都比較景觀化,所以我現在都在讀1949年以前的作品,我覺得還是要回到經典,他們寫的東西更真實。比如蕭紅,大家真的以為她的“黃金時代”真的很美好嗎?其實無論是在電影里,還是在她自己的筆下,在種種現實處境中,她始終是一個在城市中漂泊的寫作者,一名寫作的女性。她總是去魯迅先生家拜訪,經常寫東西換點稿費,別人偶爾也會接濟她一下。魯迅開玩笑說,蕭紅在上海搬了幾次家,卻始終沒搬出那條路,基本上一直住在那個地方。這么一個漂泊了一輩子的人,最后在一個不屬于自己的地方——遠離東北老家的香港病逝。
但我讀出了某種更強大的、超過我們現在討論的“有產”“無產”概念的東西。當你更早地去了解這些人的一生,這個過程會讓你對房子的執念沒有那么重。無論是租房還是買房,整個看法都會有一種顛覆性的改變。所以現在我總是在想蕭紅,也在想沈從文。
我剛讀完沈從文的全傳,也知道他經歷了戰爭時代以及后來更加混亂的歲月,他一直是租房的,從沒有自己的房子,而且還拖家帶口。甚至在每一個時期,他都很艱苦。但讓我感動的是,無論多么艱苦,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事業。比如說,他后半生無法寫作了,他就去做文物研究和整理工作。前半輩子傾注全部心血做的事業,突然換了一個軌道,是一件很艱難的事,但他似乎沒有受多大影響,依然把同樣的心血投入到另一件事情上。這一點很讓我佩服。說到底,我覺得能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你在怎樣的空間,獨居還是其他狀態,這些最終都不會影響到你。
柳逸:
我想到張愛玲。其實張愛玲和蕭紅,她們都是逃到上海的出租屋里的。蕭紅也是從北方家里逃出來的,所以上海的出租屋就成了她們的落腳點。在那種非常動蕩的年代,她們給自己租來了一張書桌,然后在這里誕生了大量的作品。
我也一直在想張愛玲和魯迅的上海漂泊經歷。
比如魯迅,他其實一直非常焦慮房租的問題。哪怕當時他已經很有名,但依舊會因為交不上房租而發愁,因此寫了大量雜文。他覺得寫小說賺錢太慢了,所以到后期甚至連和妻子的通信都要設法出版,其實就是因為很缺錢。
包括張愛玲,現在的她已經成為小資生活的代表,但其實你去看她的寫作生涯,會發現這就是一個租客的一生。常德公寓是她誕生大部分作品的地方。那個公寓確實位于靜安寺附近,現在看來是非常寸土寸金的地段。她當時和姑姑一起租住在那里,生活還算比較好,是一種比較體面的獨居女性公寓生活。有管家、專門為你按電梯、打牛奶的人。但是她后來的生活就每況愈下,包括搬到美國以后,其實一直在住廉租房,經濟非常拮據。為了賺錢,她去寫好萊塢的爛劇本,甚至在多次搬家的過程中遺失了翻譯的《海上花列傳》的手稿。這些都是很讓人心酸的故事。
讓我特別心碎的一個細節是,張愛玲她年輕時寫過一句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虱子。”這是她二十出頭時寫下的一句話。但到了晚年,她不斷搬家,總覺得房子里有虱子,或者認為自己皮膚出了問題,不斷去看醫生。她到了晚年,幾乎有一種心魔,就是覺得自己住的房子里有蟲災。我覺得這句話在某種意義上成了她對自己人生的一個隱喻。
她晚年的租房條件已經簡單到不能再簡單:單人小床,帶浴室,沒有爐灶,不怕蟲子,無懼噪音,家里只留下紙箱和折疊床,行李隨時可以丟棄。我在張愛玲寫的租房條件里,其實感受到了一種離散的酸楚。這種離散不僅僅是在有產或者無產意義上的,更是一個現代人特有的離散的狀態。
普照:
對,我覺得我們現在討論的一些像《老友記》或者更當代的電視劇,它們的敘事時長大概就是幾年到十年左右。但如果你把關注的時間跨度延展到一個人的一生,覆蓋幾十年,甚至民國時期的一百年,回過頭再看,就會更明白所謂的“人如何變化”,人和房產的關系,或者說人與物的關系。
夏周:
其實說到文學作品中的租房,我想到《殺死房東太太》,張敦寫過的一個小說,講一對年輕人和房東老太太合租的故事。房東老太太非常嚴苛,不希望租客在房子里留下太多痕跡,也不想他們經常做飯,不希望廚房里有油煙,把灶臺弄臟,于是提出各種要求。讓你覺得雖然花錢購買了這個居住空間,但卻無法正常使用,變得非常小心,像寄人籬下。所以這對夫妻就產生了殺死房東太太的念頭。老太太在故事里真的被他們殺死了,他們把她放在了墓地里。后來他們決定不在這個房子里待了,想去戈壁。這時卻發現,死去的房東老太太竟然又來找他們了,理由是:你們把我放錯地方了,這不是我的墓,是別人的墓,現在我已經成了別人的租客了。
在現實生活中,活著的人需要付房租,死去的人在公墓里也可能成為租客。通過這樣的反轉,把租客和房東之間的權利關系展現得非常微妙。
薩利·魯尼的小說中其實也有很多關于租房的片段和階級的描寫。比如說,《聊天記錄》中的Frances出身于工人階級,而她的好友Bobi則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在《正常人》這本小說里,康奈爾的母親在瑪麗安家做保姆。當瑪麗安住進母親提供的房子時,康奈爾還需要與別人合租,忍受窘迫的租房環境。她的第三本小說《美麗世界,你在哪里》中,主人公艾琳擁有文學碩士學位,但只能在文學雜志社拿著微薄的薪水,被姐姐稱為“三十歲了還在干一份不賺錢的破工作并且住在合租房”的人。當艾琳的朋友愛麗絲因為暢銷書搬進了郊區別墅時,艾琳還要面對室友長時間占用洗手間、沒有熱水洗澡的窘境。
讀到魯尼小說中的這些描寫時,我覺得它與很多文化行業、尤其是較年輕的從業者的經歷十分貼近。但這樣的煩惱更像是一種隱性的壓力,不像《殺死房東太太》里那種非常尖銳的矛盾、讓人深陷泥潭的苦楚。
柳逸:
關于出租房相關的寫作,我首先會想到韓國,因為我覺得韓國的情境可能與東亞更加貼近一些。我最先想到的是電影《寄生蟲》里的那個半地下空間。《寄生蟲》中有一個很經典的場景,洪水淹沒了整個地下室,家里的東西都漂了起來。
圍繞半地下空間,其實韓國有很多類似的表現,韓國的出租文學也展現了這樣一種“半地下的人生”。
我記得金愛爛的《滔滔生活》里有一篇,講的是一個做小生意的家庭,他們給女兒買了一架鋼琴,鋼琴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體面生活的象征符號,所以即使他們住在首爾的半地下,也想要在家里放一架鋼琴。后來一場洪水把整個地下室都淹掉了,鋼琴在洪水中被泡爛,然后我們跟隨主人公一同發現,鋼琴上的雕刻花紋其實只是貼皮貼上去的而已。
一個底層家庭,他們把鋼琴當作一種階級躍升的意象,但最后,這個意象在一場洪水中直接被淹沒了。
半地下其實在韓國是一種特別普遍的建筑形態,在當時南北沖突的那十年間,政府規定所有建筑底層必須配備地下室。剛開始這些地下室并不是用來住人的,但后來由于租金緊張,加上地產危機爆發,很多地下室,特別是首爾的地下室,被開放出租。所以現在在首爾,有很多人都是住在半地下。《請回答1988》里面德善家就是住在半地下。
在金愛爛的“出租屋文學”中,她把暴雨作為一個很有趣的意象,雨本身是中性的,但當它落在韓國,落在首爾時,就變成了一種結構性的暴力。我們仿佛可以在其中發現某種模型,即“偽裝——偽裝最終被暴露”的故事模型。金愛爛的寫作風格就是如此,她好像總是在書寫那種夾縫中的人生。你以為自己偽裝得很好,但其實最終還是會暴露。
夏周:
其實,現在買房的成本越來越高,經濟下行的壓力越來越大,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因素也不斷增加。這些影響不僅僅局限于無法租到好房子的人,實際上對持有房產的人也是很大的打擊。你會發現,很多人在失業之后,房子就會變成法拍房。除非真的沒有貸款,否則即使擁有房產的人也處于很大的不確定性中,根本無法預料未來會發生什么。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其實大家的處境都差不多?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其實租房的人和買房還貸款的人,在本質上并沒有太大區別。所有人都處于同樣的不確定性中,大家都在擔心自身是否會陷入困境。我們在討論租房這個話題時,實際上是在探討一種臨時的生活狀態,或者說,這種狀態背后所暴露出的結構性的社會問題。我覺得,人有時候本來就是一個容易焦慮的生物,人總是在為自己的不安在買單的。
柳逸:
我們也許又可以回到那個最根本的“離散”的問題。我不知道大家在讀到像蕭紅、張愛玲、沈從文、魯迅等人漂泊一生的經歷時,會不會從中獲得很大的力量?有時候我又會想,是不是因為我們作為文學讀者,自帶了一種文學性的濾鏡,于是覺得在這種漂泊中似乎有某種巨大的能量。我想客觀地討論一下,大家是不是也像我一樣,從這種漂泊的人生歷程中汲取到了很多巨大的力量?
普照:
沈從文基本上可以說是一生都在逆境中度過。他小時候就是一個看過砍頭的小孩,見過很多顆人頭在他身邊掉落。從小就目睹這樣的場面,以致后來他變成了一個充滿大愛的人,我覺得是因為他很早就見證了生命的珍貴,以及死亡的近在咫尺,所以他對生命有著更強烈、更超乎常人的熱情。
民國時期大家都在漂泊不定,經常過一段時間就有戰爭爆發,就要換地方、換城市,要隨著戰火的蔓延不斷遷徙。其實那時候整個高校體系都是沒有根基的,很多大學都是在臨時租用一些地方,比如西南聯大,或者其他學校。
在沈從文的觀念里,是否有一個家并不重要。他覺得心里有掛念的人,有正在做的事情,再加上可以遮雨的屋頂和擋風的墻,這些就已經構成了他心中的“家”的空間。那不一定是傳統意義上的家,但這些事物,包括他租住的空間,構成了他心靈上的家。我覺得我們談到家的時候,可能不只是指那樣一個物質空間,不只是指它是租賃屬性還是購買屬性,它的整體意義其實還包含了很多心靈方面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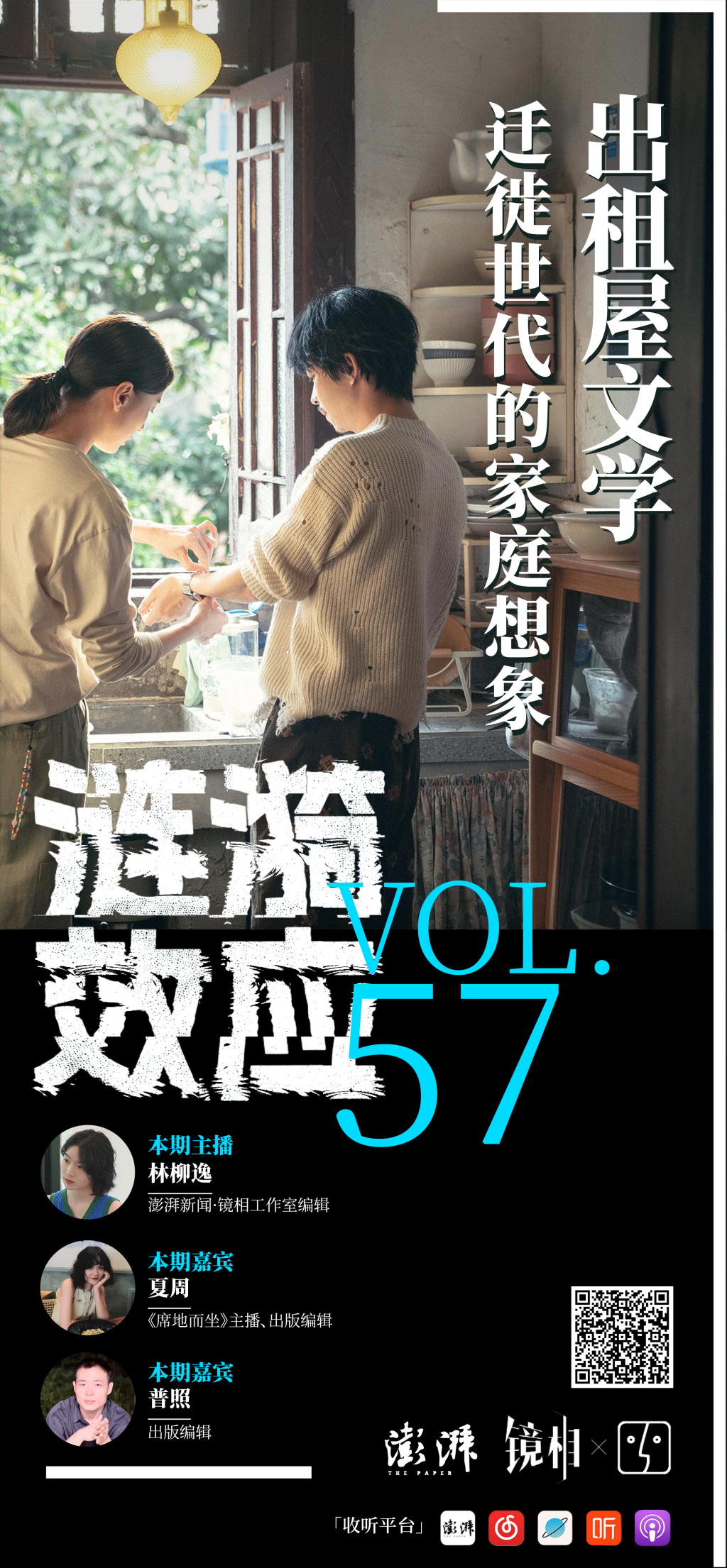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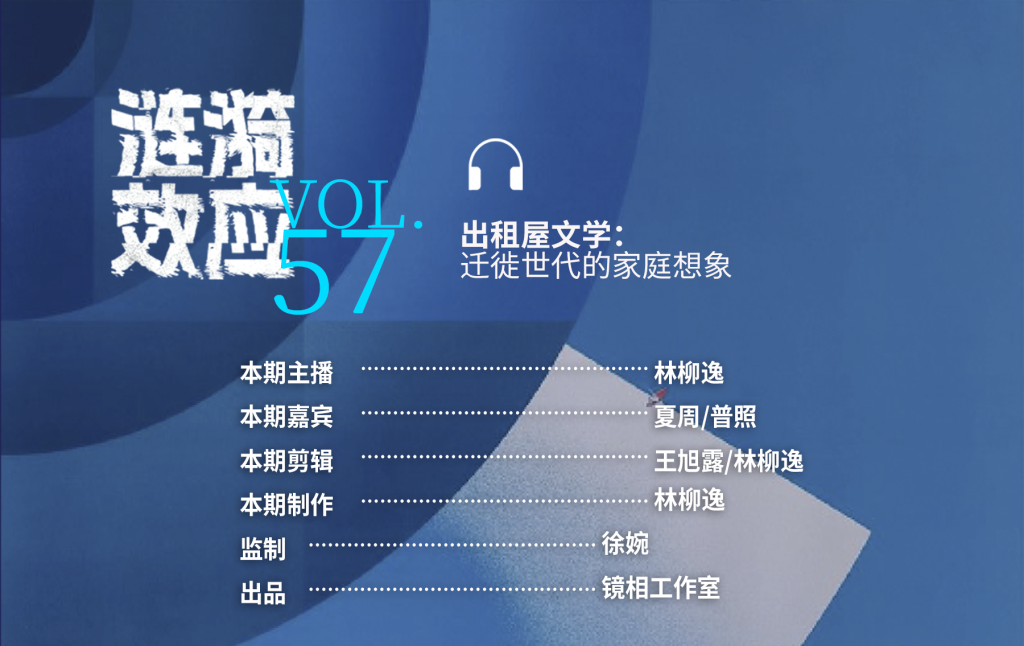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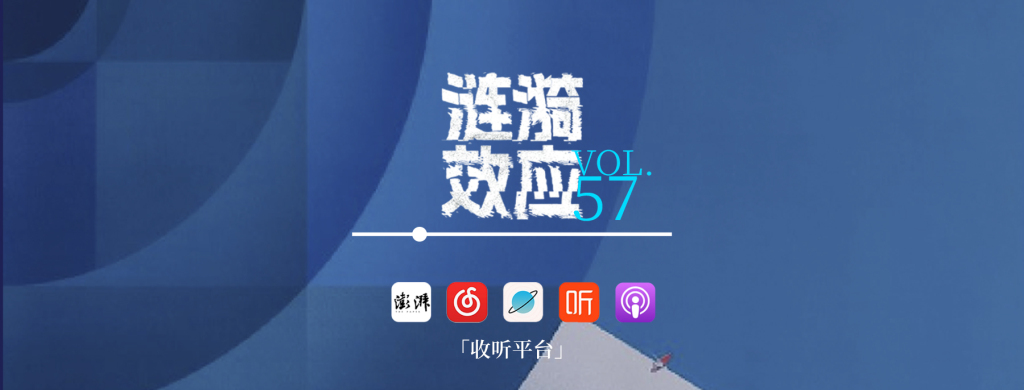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