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元1047年:十一世紀的全球文明為何支離破碎?
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047年,大宋慶歷七年,大遼重熙十六年。
這一年的四月份,大宋宮廷里面舉辦了一場婚禮,是由宋仁宗和曹皇后親自操辦的。誰結婚啊?居然有這么大面子?
新郎官叫趙宗實,是宋仁宗的侄子。你想,仁宗今年38歲了,不年輕了。他結婚23年,總共生了三個兒子,但都夭折了。為了以防萬一,就找了一位關系比較近的侄子,小時候養在宮里,雖然不是太子,但算是皇位的一個備胎吧。這就是新郎官趙宗實。
新娘子叫高滔滔。她既是宋初名將高瓊之后,也是曹皇后的外甥女,也是自小就被曹皇后接到宮里養大的。
你看這對青年男女:一個是皇帝的養子,一個是皇后的養女,同歲生人,這一年都是虛歲16,又同在宮里生活多年,算得上是青梅竹馬。所以,年歲一到,仁宗和曹皇后一合計,就給他倆湊了一對。
熟悉歷史的朋友會知道,這兩位,其實就是未來大宋的第五位皇帝宋英宗和他的高皇后。明年5月,他們還會生下一個兒子,那就是大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而高皇后,后來又成了高太皇太后,元祐年間掌握朝政八年之久。
你看,每一個時代都是既在展開自己的故事,同時也在為下一個時代的到來埋下伏筆。
那就順便交代一下:這是我們《文明》第一季的最后一期節目。第二季隨后就會正式上新。
那在這第一季的最后一期,我打算集中來回應一個問題,一個很多朋友都在問的問題:咱們這個節目既然叫《文明》,那就應該回望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話題就不應該局限在中國。可是整個第一季,完全沒有提到中國之外的世界,這是為什么呢?
好,這一期節目,我們就來看看中國以外的世界,以及為什么我們暫時擱置了跟它們有關的話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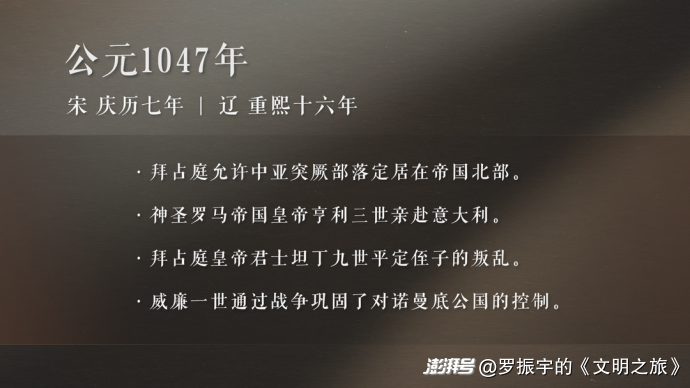
紀年之惑
為什么整個第一季的《文明》節目,我們都沒有提到中國之外的世界?“非不為也,是不能也”,不是不想做,是真的很難做到。
我先舉個例子,你感受一下我的難處。
我們《文明》節目是從公元1000年講起的。哎,你聽這個詞兒:“公元”,那可是一個從歐洲開始的概念,公元元年就是從耶穌誕生開始算的。整日子嘛,總該有點慶祝。還記得公元2000年,第二個千禧年時候,世界各地熱熱鬧鬧的慶祝儀式吧?光紐約的時代廣場就聚集了200萬人。照這么往回推,公元1000年,也就是第一個千禧年,可就是耶穌他老人家誕辰1000年,歐洲或多或少總該有一些慶典吧?

哎,不好意思,這個真沒有。
公元1000年的這第一個千禧年,整個歐洲找不到任何慶典的記載。哎,奇怪,這可是歐洲中世紀啊,宗教氛圍那么濃厚,耶穌誕辰1000年,不看僧面看佛面,不表示表示說不過去吧?為啥啊?
原因很簡單,因為絕大多數歐洲人,并不知道這一年是公元1000年。
公元紀年這種東西,它成為歐洲人普遍使用的歷法,還要再等將近600年,到了1582年,羅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的時候,才正式推行。這個教皇是誰啊?在中國澳門設天主教的教區,就是他干的。你想,這已經是中國明朝的晚期了。所以,公歷紀元確立得非常非常晚。
那問題來了,公元1000年它到底是哪一年呢?你要是對應到中國歷史,很清晰,這是北宋年間真宗在位的咸平三年。但是這一年你要問歐洲人,那可就麻煩了,因為歐洲人還沒有普遍用公歷,他們用什么方式紀年呢?答案是,各家用各家的,沒個準譜兒。
比如,有文化的人,有的用羅馬建城的那一年當元年,

有的是用羅馬皇帝戴克里先稱帝那一年為元年,

有的是以希臘召開第一次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那一年為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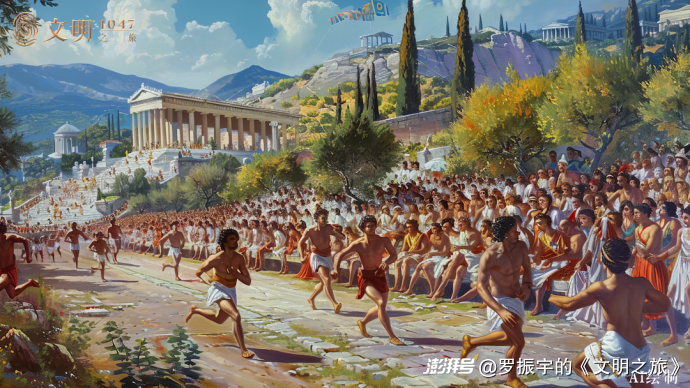
宗教界還有所謂的“世界紀年法”,也就是亞當夏娃在伊甸園的日子當元年。

那亞當夏娃是哪一年呢?問得好,那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啊,各種說法之間相差有上千年。別說亞當夏娃了,就是耶穌出生到底在哪一年,其實當時也沒有共識。我看到的資料,當時至少有六種以上的說法。要不怎么法國哲學家伏爾泰說:“羅馬人常打勝仗,但不知是哪一天打的”。指的就是這種情況。
這還只是文化人,如果是歐洲普通老百姓日常用的紀年方法,就更粗糙了,通常就是當地國王繼位的年份,比如這個時候的法國卡佩王朝的人,就說這是羅伯特二世統治的第四年。這跟中國春秋戰國的時候一樣,你說今年是魯襄公二十二年,還沒出山東呢,另一撥人就說這是齊莊公三年,翻過太行山,又變成了晉平公七年。你看,各地有各地的說法。
那你說,這不是亂套了嗎?其實你想,亂才是正常的;不亂,全世界有一個統一的紀年方法,反而是不正常的。
為啥?因為這個時候,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大多數人過的都是“本地生活”。絕大多數人一輩子都沒有出過自己的村子。他一輩子生老病死,都只和本地資源、和熟人相關。你可以代入這樣的生活想一想:村里的老太太聚在一起聊天,說到哪一年,可不就是:那是我生我家老二那一年,發大水之后的第二年,村長他們家娶媳婦那一年,等等。本地生活的人,用本地的重要事件當標尺來紀年,這就完全夠用了嘛。
而用什么公元紀年,或者是像中國這樣,用朝廷頒布的年號來紀年,這在本質上是要求一個過本地生活的人,用一個死去很多年的,自己也不認識的人的生日,或者是用一個天高皇帝遠的規定,也就是年號當時間坐標,這反倒非常奇怪。那是一種對本地生活的入侵,是要花很大氣力,很長時間才能做到的。
這個時候你才知道文明的力量多么強大。到這一年為止,中國人用皇帝的年號來紀年,已經有1000多年的傳統了。比如在這一年,公元1047年,隨便在大宋朝的哪個村口找個老太太,她都知道這是慶歷七年。為什么呢?因為朝廷每年頒布的歷法上有年號,朝廷征發賦稅、徭役之類的文告上有年號,家譜、族譜上也有年號,買賣土地的契約上還有年號,可以說年號與百姓的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老太太都不需要識字,因為她身邊會有無數人嘴里念叨著年號。
你抽身出來一看,那可是1000年前啊,沒有任何現代化的傳播工具啊,朝廷定下一個時間標準,居然就能影響到幾千里之外的人的日常生活,這是一個多么罕見的文明成就啊。所以,咱們不能怪當時的歐洲落后,我們反倒是要為中華文明驚嘆,怎么就能在那樣的技術條件下,創造那么大范圍、那么深入的公共生活?
那么多人共享同一張時間表,說叫它什么名字大家都管它叫什么名字,這個公共生活的深度是非常偉大的,這樣的公共生活的反面是什么呢?就是我們剛才說到的“本地生活”這個詞,各村人過各村的,村外的事情你管不著。歐洲人大多數過的就是這種本地生活。
在歐洲,自從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后,歐洲迅速地進入“黑暗的中世紀”。雖然現在有些學者說,中世紀沒有那么糟糕。但是,總體上,尤其是中世紀的前五百年,歐洲處在一個更貧窮落后的狀態,這是沒有什么疑義的。那你說原因是什么?最淺層的答案,當然是戰亂。但是沒有那么簡單。
如果大規模戰爭的結果,是打出了一個新的秩序,就像在中國歷史上常見的那樣,舊王朝崩潰之后,亂上一段時間,總能打出一個新的草頭王。那接下來很可能是繁榮,而不是像歐洲這樣,陷入長達一千年的中世紀。歐洲當時的情況是,西羅馬帝國的大共同體解體了,確實是到處打仗,人人自危,盜匪橫行,但并沒有打出一個新秩序。所有人開始了小共同體的本地生活。歐洲到處都是自給自足的小莊園。

這就可怕了。戰爭對財富的摧毀是暫時的,而全面陷入本地生活,那就不只是對財富的摧毀了,那甚至是文明的浩劫。你可千萬別覺得遍地莊園是什么田園牧歌啊。陷入本地生活結果是什么?我們一層層地看。
第一個結果,就是貧窮。
現代經濟學告訴我們,繁榮的基礎是分工和合作啊。一旦進入本地生活,和外部的分工合作網絡也就崩潰了,財富增長也就不再可能了。
吳伯凡老師就曾經問過一個問題:城市化的本質是什么?不是一大堆人聚在一起,而是人類獲取生活物資的方式變了,從本地獲取變成了異地獲取。你看,中文有一個詞,叫“薪水”,就是柴火和水源,這是最重要的生活物資。原來過鄉村生活的時候,柴火和水源在哪里?就在本地和附近啊。但是一旦過上了城市生活,你家的煤氣從哪兒來的?水是從哪兒來的?是由專業化的公司從遠處給你帶來的,只要付錢,打開管道就用。這才是城市生活和鄉村生活的本質區別。為什么城市生活的水平高?脫離了對本地生活資源的依賴,每個人都活在分工合作的網絡里面,這才是根本原因。
這是只過本地生活的第一個后果——貧窮。
第二個結果,就是人會變得殘忍。
這首先是因為過本地生活的人,安全感只能來自于本地,同時就會對所有外來事物抱有天然的敵意。沒有跟陌生人的合作嘛,我有什么動機,有什么必要去理解他人呢?
但是更重要的還不是這個,而是因為我沒有辦法和外來人和解。
我舉個例子。有一次我和作家郭建龍老師聊天,說到中國歷史上那個著名的慘劇:長平之戰之后,秦國坑殺了40萬趙國的降卒。人家都投降了,還要把這40萬人殺了,這也太殘忍了吧?但是你如果站到秦國的角度想想,可以不殺嗎?答案是不行。因為這些人的自我認同是趙國人,常年的敵對,導致這些人不可能轉而認同秦國。養著費糧食,放回去等于重新武裝趙國,不處理隨時有嘩變的風險,不殺又能怎么辦呢?溶解不了的東西只能毀掉。
所以,秦國的統一戰爭的殘酷性就在這里,秦國不只是贏了戰爭,而是把山東六國的人口資源消耗殆盡,才完成了統一。僅僅秦國大將白起,就起碼殺了上百萬的人。
現在你就知道了,大家生活在一個統一的大共同體中的好處了。不只是可以合作,而且大家有和解的可能性。就拿宋朝來說,宋朝統一戰爭,打得最艱苦的就是滅北漢的戰爭,但是只要北漢皇帝一投降,戰爭迅速就結束了,北漢的人馬上就成了大宋的子民。對啊,只要大家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戰爭再殘酷,分出勝負之后,都沒有必要趕盡殺絕啊。人口也是資源啊,為什么自己不留著用呢?
所以你看,只過本地生活的人,因為隔絕,就愚昧,因為愚昧,就殘忍。
本地生活,還有第三個后果:精神生活的貧瘠和治理水平的低下。
我手頭的這本書《新編劍橋中世紀史》第三卷,就是寫公元1000年前后這個階段的。你乍一看,這書不是挺厚的嗎?里面應該有很多內容啊。但是你翻翻導言部分,編書的人一直在叫苦:前面時代的史料很豐富,后面文藝復興時代的史料也豐富,唯獨這個階段,沒有靠譜的史料啊!這還不止是說史料少,而是這個階段的歐洲人的讀寫能力下降得太厲害。識字的人少,所以即使是能讀會寫的人,水平也不行。水平差到什么程度呢?他們寫的東西,作者自己也分不太清是在記錄歷史還是在胡說八道,虛構和非虛構的界限模糊得很。所以這本書看下來,很有意思的一個感受,就是作者寫什么,口氣都是猶猶豫豫的,“也許”、“應該”、“大概”,都是這種詞兒,寫書主要靠猜,真是心疼寫這本書的歷史學家。
對啊,大家都過的是本地生活,沒有和遠方交流的需求,識字有什么用呢?在這樣的精神生活水平上,社會治理的水平自然也就很低下。
順便糾正一個誤區,很多人以為是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后,北邊的日耳曼蠻族給歐洲帶來了封建制。其實不是。西羅馬帝國晚期,大量地方已經退回到本地生活和莊園經濟。那一個莊園總是需要地方性的軍事保護啊。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這么一個自給自足的莊園的莊主,你總要找一個附近的有武力的山大王投靠過去,我平時給你交點保護費,需要的時候你保護我的安全,但平時你不用管我村子的內部事務。你想想看,這不就是封建制嗎?這就是領主和附庸的簡單關系嘛。這是一種極低水平的社會治理方式,適用于這種弱政治、弱軍事、弱經濟、弱文化的社會條件。

所以不是日耳曼人后來創造了所謂的封建制,上面有領主,領主下面有附庸,附庸接著分發自己的土地,不是這樣的,而是自下而上找保護這么找出來的。不是日耳曼人創造了封建制,他只是繼承了西羅馬帝國晚期這種自發的、低水平的治理方式而已。
這就是公元1000年前后的歐洲。其實,這個時候的世界,都和歐洲類似,是一大群分崩離析的孤島。
我們從東到西簡單捋捋:日本和中國的聯系,什么遣唐使、鑒真和尚東渡、大化改新這些故事基本都發生在唐代,到了現在這個階段,商貿聯系雖然還有,但是官方關系基本斷掉了。當時日本是藤原家族掌權,很沒有進取心,整個日本文明都處于一種收縮的狀態。
再來看中國的西邊:阿拉伯帝國的鼎盛時期已經過去了。這個時候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也就是中國史書上說的“黑衣大食”,能控制的地方也就在巴格達附近,整個帝國其實已經四分五裂。

往中國的西南看,印度。印度文化對歷史太不重視了,幾乎沒有什么史料留下來。這個階段的印度,大概的狀態就是小國林立,紛爭不斷,也沒有什么可說的。

現在你明白我一開始說的那句話了:我們為什么在這個階段不提中國之外的世界?“非不為也,是不能也”,不是不想做,是真的很難做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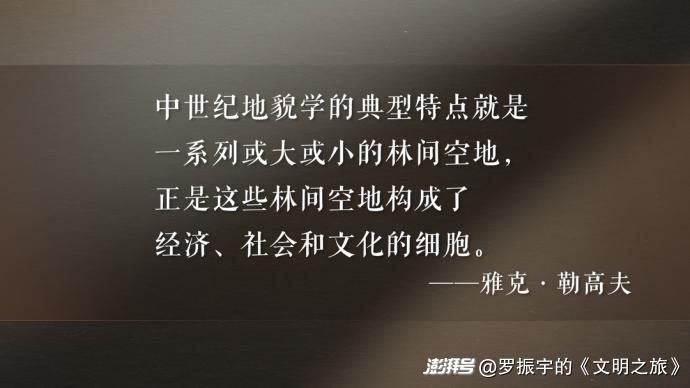
文明之光
聽了剛才的解釋,你可能會說:世界支離破碎,也不耽誤你講世界的故事啊?就像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不也是支離破碎的嗎?出了多少有趣的故事啊。
這就要說到我們這個《文明》節目的初心了。
嚴格地說,《文明》并不純粹是一個歷史節目。我們更關心的,不是歷史事實本身。我們追問的其實是一個當代性問題,那就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生存所依賴的人類文明的基座,它到底是怎么演化而來的?這個世界何以如此?我們又何以活成了現在這個模樣?
我之所以要做這個節目,就是想用20年的時間,一邊學、一邊講,讓自己可以向后覺知,覺知到那些不可掙脫的約束;同時又能往前眺望,眺望見那些可能開拓的空間,從而體面地、有尊嚴地過好這一生。如果同時能對你,對看到這個節目的人有所幫助,那就太高興了。
所以,歷史上哪一年,在哪里,發生了什么事?哪個國王上位了,哪個國王死去了,哪場戰爭發生了,這些孤立的事件,在我們的視角里,價值就沒有那么大。除非,它不僅發生了,而且還和世界的其他部分發生了廣泛的聯系,不僅有聯系,而且這些聯系還在持續擴展,不僅有擴展,而且它的影響還存留下來、疊加起來、映射到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現實中,那才是我們要關注的事情。
這就是《文明》節目要暫時擱置世界史話題的原因:因為這個時候的人類世界過于破碎,缺乏這種整體性的聯系。當然,這也是我們將來必然要涉及世界史話題的原因:因為人類世界的聯系大爆發馬上就要到來了。
你說具體是什么時候?1492年,也就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后,世界史的相關選題當然會大幅度增加。但其實,就在第三季的開頭,也就是1096年,我們會聊到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那是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一次巨大的文化碰撞。而且,它還是歐洲人醞釀了500年的一項文明成果。
為什么會這么說?
我們還是回到這個階段歐洲的政治現實,就兩個字,破碎。
其實,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后,北方蠻族不是沒有完成過統一。公元800年前后的時候,查理曼大帝就統一過歐洲的西部。這個人是誰啊?你其實經常見到。他就是撲克牌中的紅桃K啊。
但是很不幸,這個時候的歐洲人還是搞不懂國家整合的意義,國王只是把國家當作他自己的財產,高興了,隨意就能切一塊送人。所以,沒過幾十年,查理曼大帝的三個孫子一合計,就簽了個條約,把國家給分了三份。如果看歷史地圖,你會發現三個國家的領土形狀,都是南北方向的長條條。這就是后來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的雛形。奇怪,為什么這么分呢?這肯定不符合國家的外部安全利益,也沒有考慮國家的內部整合難度啊。還是那個原因,他們只是把國家當財產。因為分財產要平均嘛,三兄弟每一家都既要分到北方牧場,還要分到南方能產橄欖和食鹽的地方,反正每個緯度帶的東西都要有,只能分成南北方向的長條條。所以緊接著,歐洲西部又亂成一鍋粥。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一點點政治整合成果,馬上又瓦解了。

那怎么才能解決這個政治破碎的問題?其實這個時候的歐洲在醞釀另一種力量,那就是基督教。
這里我們要澄清兩個誤解。很多人以為,整個中世紀的1000年,都是基督教會在歐洲稱王稱霸。其實不是的。在公元1000年前,教會非常弱勢,總體上是聽命于國王的,甚至連教皇都是由國王們來任命的。你想,教會嘛,手里只有一個虛無縹緲的上帝,又沒有軍隊,遇到那些蠻族大老粗國王,所謂“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他們怎么能欺負到國王呢?
還有一個誤解,就是覺得基督教是一種黑暗、愚昧的勢力,其實也不然。在當時的歐洲,基督教反而是光明和智慧的代表。是他們保存了文明的火種,是他們代表了當時歐洲的最高道德水準,也是他們推動了后來的文藝復興。不信你就想想,后來“文藝復興三杰”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的大客戶是誰?給錢讓他們畫那些名畫的,主要都是基督教會啊。
我們《文明》節目第二季要經歷的這個階段,也就是11世紀的后半葉,正是基督教會突飛猛進發展的時期。教會拿回了教皇的任命權,我們自己選,不用你們國王操心。大量建立教堂,擴編神職人員的隊伍,強化教會組織,到了11世紀末,教會成了整個歐洲規模最大、組織最嚴密、權力最集中的超國家組織。
有了這些準備,教會就可以和國王們掰掰手腕了。其中最著名的事件發生在1077年,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亨利四世得罪了教皇。這個時候教廷的權威已經到了什么程度?教皇說,我不承認這個人是基督徒,就這么輕輕一指,不用打不用罵,其他人就都說,哪怕你是皇帝,除非教皇原諒你,不然我們就不承認你是皇帝。所以,亨利四世沒辦法,只好唱了歐洲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出苦肉計,赤著腳翻越阿爾卑斯山,到教皇的駐地卡諾薩,在冰天雪地里站了三天三夜,懇求教皇的原諒。

明白了這個背景,我們才能看懂十字軍東征是怎么回事。為什么要東征啊?是因為一個宗教理由,大家要響應教皇號召,為基督教收復圣城耶路撒冷而向穆斯林世界開戰。
但問題是,這是打仗啊,很嚴肅的事啊。軍隊怎么動員?后勤怎么補給?路線怎么走?軍費誰來出?由誰指揮戰爭?這些計劃一概沒有,就憑教皇烏爾班二世的一通忽悠,歐洲各地的貧苦農民、騎士,就帶著武器出發了。
想象一下吧,那可是從今天的法國徒步走向耶路撒冷啊,幾千公里,幾乎沒有像樣的路,甚至當時歐洲壓根就沒有人走過這么遠的路,沒有地圖,語言不通,路上沒有酒店,也沒有錢,而隊伍里的人,大多數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過自己的村子,這些人就憑著教皇的一句話——參加十字軍的人,死后直接升天堂——就義無反顧地出發了。你想想,這可是害怕外部世界就像害怕洪水猛獸一般,看一眼村子外面的森林就覺得里面有狼人和妖怪的中世紀的歐洲人吶,能對他們進行大規模動員,這是一股多么可怕的精神力量。

正是這股力量,打破了本地生活的堅冰,歐洲文明開始融解、整合。
好吧,未來一年里,我們《文明》節目,就這樣一邊關心著大宋王朝的進展,一邊側耳聽著歐洲堅冰破碎的聲音。我們這個項目長著呢,咱們慢慢等著人類近代文明的融匯和展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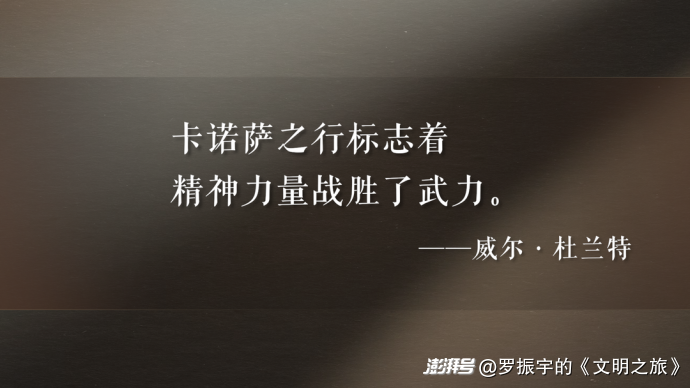
大宋舞臺
現在我們講的是公元1047年,大宋慶歷七年,我們還是把目光撤回到中華文明的舞臺上。這一季的最后,我們來關注幾個人,幾個馬上就要登上大宋政治舞臺的重要人物。
在這一年的年底,在大宋境內的貝州,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清河縣,會發生一場兵變,朝廷花了65天就把它平定了。負責平叛的大臣叫文彥博。他本來長期在地方上工作,今年才被召到朝廷做參知政事,年紀僅僅42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下一年,他因為平叛有功嘛,會進入宰相班底。再過20多年,他將對宋神宗說出一句非常著名的話,皇帝“與士大夫治天下”,把宋代士大夫政治的那個核心點出來了。當然,文彥博這個人還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活得特別長。今年他都42了,但是我們下一季節目結束的時候,他還健在,還對朝政有影響。他是出將入相50年,一共活了92歲,在那個時代算是個奇跡。
還有一位朋友,一定要介紹給你,那就是司馬光。
這一年,司馬光才29歲。九年前,他考中進士,但一直是留在父親身邊做事,直到上一年,才來到開封,在國子監,就是國家的最高學府教書。再過十幾年,司馬光突然開掛,發了一個宏愿,要修《資治通鑒》,從宋英宗治平三年開干,一直干到宋神宗元豐七年,前后19年,全書修完,司馬光已經63歲了。他在1000年前做的這件事,也給了我們《文明》節目一個重要的啟發。你懂的,向司馬光默默致敬。
還有一個人,咱們不得不提,那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今年才27歲。五年前,他考中進士,今年,他被朝廷任命為鄞縣知縣,就是現在的浙江寧波的鄞州區。在那個時代,王安石的工作作風非常罕見,那是真跑基層,真抓實干啊。比如,這一年的12月,他趁著冬季農閑,帶著幾位懂水利的小吏從縣城出發,跋山涉水,起早貪黑,花了整整十三天時間,跑遍全縣十四個鄉,為修建農田水利設施準備第一手資料。一邊跑,還一邊記日記,哪天到山上去看采石工人開鑿石料,哪天乘船考察地形地貌,哪天到工地檢查水利工程的進展,哪天深入村莊院落跟老百姓宣講為什么治水。這份日記,算是一份很難得的地方官員工作日志。
我們現在去看這份日記,就能分明感受到,王安石和那個時代的士大夫真是不一樣,他在日記里,只記工作,一句抒情和描寫都沒有。再過20年,他就要帶著這種不知疲憊的精神和20年間養成的巨大聲望,開啟那場一言難盡的王安石變法了。那將是我們下一季節目的重頭內容。
但是別忘了,我們下一季節目還有一對主角。那就是蘇軾、蘇轍兄弟倆。
他倆今年一個11歲,一個9歲。這一年,因為爺爺蘇序去世,他倆的爸爸蘇洵從京城開封返回四川眉州老家守孝。蘇洵考了幾次科舉,都沒成功,這次回家,干脆也就不走了,專門負責蘇軾和蘇轍的教育。所以從這一年起,中國文學史上的三蘇父子的群像就算是成形了。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讓人羨慕的父子組合了。你現在去四川眉州的三蘇祠,正堂上的那塊匾,寫著四個字:“是父是子”。意思就是,這樣的父親這樣的兒子。你看看,后人看到這樣的父子,好像只能這樣贊嘆,一個形容詞都是多余的:瞧瞧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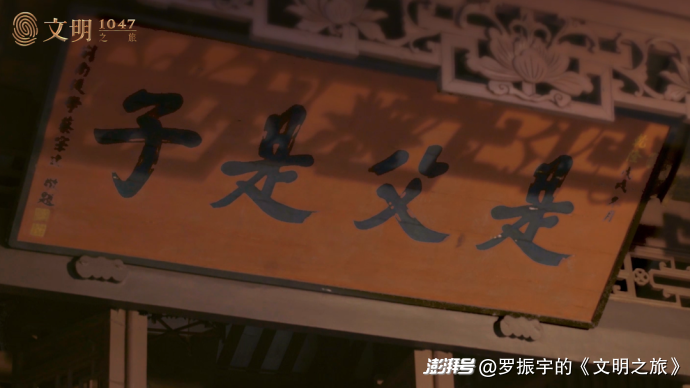
再過9年,蘇洵就會帶著蘇軾、蘇轍兄弟離開家鄉,踏上了前往京城趕考的旅程,此去是多災多難,此去也精彩紛呈,所謂“恩怨情仇皆嘗遍,不枉人間鬧一場”啊。下一季的《文明》節目,我們會不止一次地講到他們,敬請期待。
最后,我提前跟你講個關于蘇東坡的故事吧。那是紹圣年間,我們下一季節目臨近結尾的時候,蘇東坡被一路貶官,貶到了廣東惠州,只有一個小兒子陪在他身邊,其他親人都星散各地。
蘇東坡的長子當時在宜興,因為得不到父親的音訊,成天憂愁。一個叫契順的和尚,聽見了就說,你嘆什么氣啊?!你父親不就在惠州嗎?惠州又不在天上,不是走著就能到的地方嗎??“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
契順說:來,你現在就寫一封家書,我去替你問候父親。于是,契順和尚翻山越嶺,曉行夜宿,來到惠州。見到蘇東坡,交代家書之后,轉身就要返程。
蘇東坡愣了,說你這么辛苦跑這一趟,總該有所求吧?我能為你做點什么呢?契順說:如果有所求,我為什么不去開封去見那些達官顯貴,而要來見你呢?是的。彼時的蘇東坡什么也沒有,他只好苦苦追問,你這么辛苦跑一趟,讓我也為你盡盡心?我一定要為你做點什么。契順說,要不這樣吧?你給我寫一幅字吧。于是蘇東坡為他寫下了一幅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
因為這幅字和蘇東坡記下的這個事,我們才知道,1000年前,世界上有過這么一個俠肝義膽的契順和尚。這個故事給了我很大的力量。你看,一個人不一定要自己創造多大的功業,但是如果我們在自己的生活里有熱血的心腸,敏銳的行動,我們就有可能被周圍的人記住,被偉大的事業容納,被偉大的筆觸書寫,從而我們也借機進入歷史。
就拿我們這個《文明》節目來說,看起來很龐大。你想,從公元1000年講起,一期講一年,一周講一期,一直要講到1912年,總共是913期。這要花掉我生命中的從50歲到70歲的20年時間,才能完成這個工程。是不是有點一眼望不到頭的感覺?
但是,就在準備這期節目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48期節目上線了,這不已經完成了二十分之一了嗎?這就相當于在一個表盤上,秒針已經咔咔咔轉動了3秒。有了這3秒,一分鐘其實很快也就到了。一件事情,進度條只要開始動了,距離做完也就沒有那么遙遠了。這不就是契順和尚當年說的那句豪言嗎?“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
意識到這一點,1000年前的契順和尚,突然和我合體。我胸中又涌出了翻山越嶺、曉行夜宿的潑天勇氣。
感謝你的陪伴,我繼續加油。我們接下來要休整五周。這五周時間里,我們自己會加油充電,為第二季做準備,但是那幾個詞,會持續在我們心中回響,那就是:“發大愿、邁小步、走遠路、磕長頭、不停頓、不著急。”
咱們2025年3月5號,也是公元1048年,再見。

致敬
今天節目的最后,也是第一季節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一個時刻。
1047年,蘇軾的爺爺蘇序去世。11歲的蘇軾在爺爺的葬禮上,遇到了自己的堂妹“小二娘”。多年之后,蘇東坡寫下了一首詩,“羞歸應為負花期,已是成陰結子時。與物寡情憐我老,遣春無恨賴君詩。玉臺不見朝酣酒,金縷猶歌空折枝。從此年年定相見,欲師老圃問樊遲。”根據林語堂的說法,這是蘇軾對自己年少時情竇初開的追念。幾十年后啊,那一絲情愫啊,還是將斷未斷,欲說還休啊。
當然,即使是像蘇軾那么曠達的人,這樣的事,即使宣之筆墨,也是非常隱晦的。
不管它真假了,我寧愿相信林語堂的這個說法實有其事。
人類文明之所以可愛,之所以值得我們這么辛苦地去追溯,去辨認它的生長印記,就是因為有這樣的動情瞬間。那萬丈紅塵吶,我們舍不得啊,不是因為什么抽象的道理,說到底,不就是因為這世上有我們舍不得的人嗎?《文明》節目,我們下一季,再見。
參考文獻: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
(元)脫脫等撰:《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
(宋)司馬光著,鄧廣銘等校:《涑水記聞》,中華書局,1989年。
(宋)沈括撰,金良年點校:《夢溪筆談》,中華書局,2015年。
(宋)邵伯溫撰,李劍雄等點校:《邵氏聞見錄》,中華書局,1983年。
李仲生:《世界人口經濟史》,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年。
李筠:《中世紀:權力、信仰和現代世界的孕育》,岳麓書社,2023年。
趙冬梅:《寬容與執拗:迂夫司馬光與北宋政治》,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
崔銘:《王安石傳》,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
[英]弗朗西斯·魯賓遜主編,安維華等譯:《劍橋插圖伊斯蘭世界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
[法]羅伯特·福西耶主編,李增洪等譯:《劍橋插圖中世紀史(950-1250年)》,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
[法]雅克·勒高夫著,徐家玲譯:《中世紀文明(400-1500年)》,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英]伊恩·莫蒂默著,李榮慶等譯:《歐羅巴一千年:打破邊界的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英]提姆西·路特主編,顧鑾齋等譯:《新編劍橋中世紀史·第三卷:約900年至約1024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
[英]大衛·勒斯科姆,[英]喬納森·史密斯主編,陳志強等譯:《新編劍橋中世紀史·第四卷:約1024年至約1198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
[美]朱迪斯·本內特著,林盛等譯:《歐洲中世紀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年。
[美]韓森著,劉云軍譯:《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開端》,北京日報出版社,2021年。
[美]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著,夏繼果譯:《12世紀文藝復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