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觀察|長岡賢明那“長效設計”的眼光在徽州發現了什么

D&DEPARTMENT曾發起“60Vision”(開發與60年代原點商品相吻合的商品)、“d47”(以“長效設計”的視角重新審視日本47個都道府縣的個性,希望推動地域振興的系列活動),在東京的表參道,D&D曾有與川久保玲的合作店鋪;在澀谷,D&D有d47博物館、d47食堂和d47商店;在京都佛光寺,坐落在古色古香的建筑里的D&D京都店餐廳,小伙伴也曾向我安利過“D&D京都店”袈裟布料再利用做的環保袋——“D&D”的“LIFESTOCK”作品之一,即將織布工廠的“保存商品”,激活為“商品”實現繼續銷售。而這種“在地性”的轉化,也讓購買不單是一種簡單的消費行為,而稱為一種特別的記憶。

而在“D&D黃山店”,類似的環保袋所采用的是中國來自上海崇明的土布。如同很多曾經風靡的產物,隨著工業社會的到來,全手工制造的“土布”漸漸淡出人們的日常生活,傳統手工紡織技藝也瀕臨失傳。這批織造印染于20世紀60-80年代的提花布、印花布、格子布等,也因為尺寸原因很難再被利用,在變身環保袋后,有了新的價值。
除了環保袋外,長岡賢明還以“長效設計”的眼光發現了什么?在徽州的調研和考察中什么讓他印象深刻?

徽州黟縣姚師傅的竹編
當“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ditubang.cn)記者問長岡賢明對哪一件徽州當地產品印象深刻時,長岡指著柜臺上插著植物的一個竹編包裹的玻璃瓶。“我本來以為是中國傳統工藝品品牌開發的產品,后來細看,發現玻璃瓶口有用過的痕跡,才知道這就是個很普通的玻璃瓶,但外面竹編讓人感覺它不普通。最終我知道這個是當地一位師傅包的。”長岡說,“那位竹工師傅跟我們說,只要我們有喜歡的杯子或者器物,都可以拿去,他可以根據杯型來做,我覺得這個太厲害了。未來我計劃選一些常見的,但不會注意到的生活用品,給師傅加工,也許會形成系列。”

這位黟縣竹編師傅叫姚家駒,除了為玻璃瓶包裹上竹衣,“D&D黃山店”還售賣他手工編織的戒指、手鐲、籃子等。那天恰逢姚師傅來店里,他50來歲的樣子,一騎助動車,一個用了幾十年的竹編農具籃,里面放著他編的竹戒指和竹鳳凰。聽聞有記者要采訪,他頗感意外,從他黟縣普通話的只言片語中,大約知道竹編工藝花費時間,從選竹開始每一道工序都有學問,在最后編織中,如果竹絲斷裂,那么前功盡棄。姚師傅不善言辭,但一雙充滿老繭的手默默講述著竹編的故事。

“在皖南農村,竹編是最常見的一門手藝,家家戶戶都有竹編的用具。”左靖介紹說。2014年6月,“行動中的民藝:從黟縣百工出發”在安徽大學展覽時,左靖還特地從日本請來了年輕的別府竹細工清水貴之到現場與觀眾互動。雖說以前竹編最常見,但現在還操持這份手藝的人已經很稀少了。姚師傅住在縣城,也會去秀里的支攤,和“D&D”結緣是左靖和碧山工銷社的引薦,左靖還提供給姚師傅一些竹編的建議。在新一期的《百工》中,策展人顧青在回顧碧山工銷社開幕展“早春二月”時(該展覽通過設計師與手藝人的“共同創作”,尋找更多復興民藝的可能),也提到了竹工藝困境。在顧青看來,竹藝品牌“自然家”與姚師傅合作推出的竹編棋盤,針對碧山在地條件,是最有希望進行小批量量化生產的產品,但竹工藝卻成為期待最高,落差最大的領域。

“合作尚未開展的癥結不能歸于設計師或工匠的懈怠,也不能簡單問責于連接這兩端的環節沒有發揮效用。這其中能觀察到的,不僅有鄉村文創工作中極為有限的人力,也有在市場盈利前景暫不明朗的情況下,各方謹慎觀望的態度。” 顧青說。

“自然家”的易春友通過對碧山地區竹編工藝的調查發現,碧山竹編屬于竹細作,有歷史傳承,但因未受足夠的重視,式微在所難免。目前當地只有零星散落的年邁匠人,他們的技藝成熟,但生產設備及條件相對落后,又都是個人作業的狀態,不能量產就難以談及產業化。這些匠人閑暇時會做一些農具,還會承接一些個人客戶定制,無固定和長期的工作內容。

然而與凋敝現況呈鮮明對比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國家出口創匯時期,當地竹編廠有八百多人,廠里的竹編藝人負責產品研發還帶徒弟。不過改制后廠就解散了,從結局來看那個特定時期的興盛也有點像是工藝的回光返照。時光久遠,如今這些匠人不知去向。
在易春友看來,傳統工藝的生存現狀充滿艱難,生存下來是首要的。同時為了手藝“產品化”,必須要尋找更多竹編師傅。過程中發現,黟縣的竹編師傅并不少,幾乎村村都有。但因為這門手藝“斷代”30年,多數人都年近60,手上活多年未動,甚至連工具都已遺失。
“情懷落地、工藝轉化、設計介入”是碧山工銷社對于民間手工藝的思路,在實踐中也面臨著料到或料不到的問題,當然其中始終困擾的是“后繼乏人”。

對于源自生活的姚師傅的竹編作品,長岡賢明認為,在日本,大家把傳統工藝想得太嚴肅,導致大家拘泥于形式。反而不像徽州的匠人以比較輕松的方式,進行有趣的嘗試。“技術當然要保留,而且要進步,但是形式和樣式真的不重要,風格也不重要,這樣你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長岡說。

村口飯店的白酒杯何以成為“長效設計”品
在“D&D黃山店”中有幾種樣式的中國白酒杯,引起“澎湃新聞”記者的興趣,這就是中國人習以為常在酒席用的喝白酒的小杯子,但這種普通到幾乎不會被注意的杯子卻被長岡作為“長效設計”產品選入“D&D黃山店”。

回憶第一次見這種杯子,長岡說是在碧山村口的飯店,拿出中國白酒時,第一次看到那么小尺寸的杯子,覺得很可愛。“后來我們去黃山市批發酒店用品的市場,有很多類似的杯子。在那里,我選擇了在形式和美觀上我所認可的。雖然最后是以美觀性在選擇,但是我覺得這個小酒杯代表了中國文化,它是有價值的。”長岡說:“日本人在酒席上,大多憑自己的感覺喝酒,自以為樂。而在中國,喝酒有一種‘儀式感’,感覺每個人都要說一些什么,在認真聽完別人說的話之后,大家再來干杯,我喜歡這種感覺。大家不是為了喝酒而喝酒,而是有一個交流的過程。所以我覺得中國才會把白酒杯做得這么小,因為盡量一次少一點,你要跟別人交流多一點。我覺得這個酒杯的小和普通就是中國文化,也是中國食文化里面的一種習慣。”

而探究更多的“選物”方式,在“D&D黃山店”后坊正在進行的“另一種設計:長岡賢明的工作”展覽,似乎能找到一些端倪。
展覽分為10個部分:1、長岡賢明;2、發現;3、改變看待事物的眼光;4、起一個新名字;5、欣賞歲月留下的痕跡;6、制作是為了再利用;7、使用既有形式;8、挖掘與地域的“相似性”;9、以商務用品為基調;10、創作傳達的方法。

重新發現舊物的價值,使之投入新的使用循環,長期有效地利用它們的價值,是D&DEPARTMENT品牌的基本意義。18歲開始做設計的長岡賢明,在35歲逐漸對設計產生了一些疑問。他看著周圍的設計師們,日復一日的嘗試創作新的設計,開始對這種不斷地去為這個世界增添新東西的現象產生了一些擔憂。從那時候起長岡便開始考慮新的設計思路,是否有一種做好設計但又可以不用創造新東西的方式?

“好的設計,會不會有正解?”為了證實這一想法,長岡賢明開始收集各種深受世人好評的設計,通過不斷反復使用而去驗證其設計的正確性。逐漸的,這個過程與其成果也演變成了一家設計師視角的選物商店。同時也通過傳達,銷售長久以來被人們所鐘愛的設計與物品(長效設計),來為自己今后制作新的設計,進行一個長期的預習,并與更多的人一起合作創造屬于這個時代的好設計。

在長岡賢明看來,當下的日本和中國存在相近的社會現象,那就是像北京和上海這種大城市與地方存在的差異化比較明顯。在日本,東京與地方之間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化。因此,許多地方的工藝和文化會因這種落差而顯得沒有那么重要,這很可惜。日本是由47個都道府縣組成的,正是因為有了這47個地方的特色和個性,才組成了現在的日本。他認為,地域的差異,應當被平等地去看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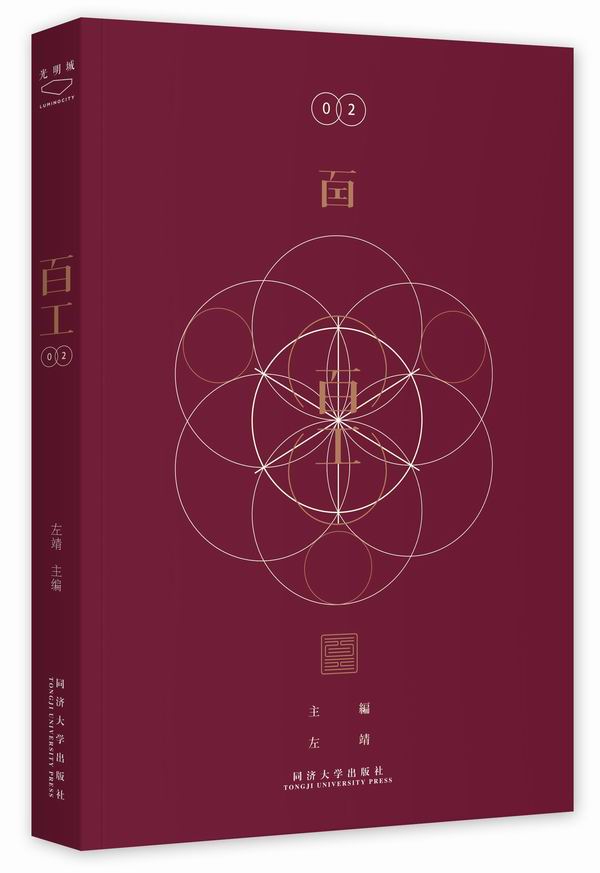
這或許就是D&D選址在遠離大都市的碧山村的緣由之一。對于D&D黃山店來說,如何不斷再發掘徽州地區的魅力與個性,以更寬廣的視角做出高水準的“地域發現”,是長效設計的一個新的課題,也是新的起點。
注:本文圖片均由“碧山工銷社”提供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