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讀|居住身份與“家”的邏輯
在2014到2016年間,《尋找住處》、《1990年代以來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下簡稱《居家生活》)、和《居住的政治》三項關于居住的研究相繼發表。這三項研究主要針對大城市中“無家”、“居家”和“保家”三種“家”的階段及相關群體的居住身份。這三項研究在內容上的連續性,有助于解釋“家”在當代社會的邏輯,并提供了洞悉居住身份的視角。
第一本書《尋找住處》是關于“無家”的流浪漢。這本書主要以田野深描的方式,記錄上海各個類型的流浪漢狀況。在這些案例中,令人觸動的是幾位在上海流浪的“上海人”。他們因為各種原因離開了上海,但是返滬時發現戶口難以遷回,也很難融入曾經的親友,最后只能在火車站區域徘徊。這其中值得強調的是“上海戶口”這個戶籍身份。
現在人們對于上海戶口趨之若鶩,但這一身份不是一直意味著某種優越,在歷史上也曾使人因其吃盡苦頭。比如在計劃經濟時代的支內支邊項目以及知青的上山下鄉運動中,擁有上海戶口的居民相較全國其他中小城市的居民,要更早地離開城市。一旦接受某種身份帶來的好處,也必然同時接受了其所帶來的潛在風險。在上海火車站流浪的上海人群體,因為戶籍的差異和切割而被阻擋在制度保障之外。如此,戶籍身份一旦斷裂,尋“家”就喪失了根基。

第二項研究關于當代上海青年的“居家”生活。這項研究主要使用問卷調查的方式,考察上海青年對于家庭要素的認知,以及業主和租戶在居家生活中的特點。這項調查揭示了一個現實與認知的差別:“(社交方面)‘基本每月都會招待’的比例,是未購房者(89.9%)高于購房者(14.0%)。這一數據說明是否擁有產權房,和是否利用這一空間招待親戚朋友、開展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交往活動之間呈負相關性。”
換言之, 上海青年業主擁有居住空間,但利用這一空間進行社交的積極性低于租戶,報告將之概括為一種“內縮”的生活狀態。這一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房地產廣告長久以來塑造的購房迷思。在私人生活領域,業主身份并不一定帶來“家”的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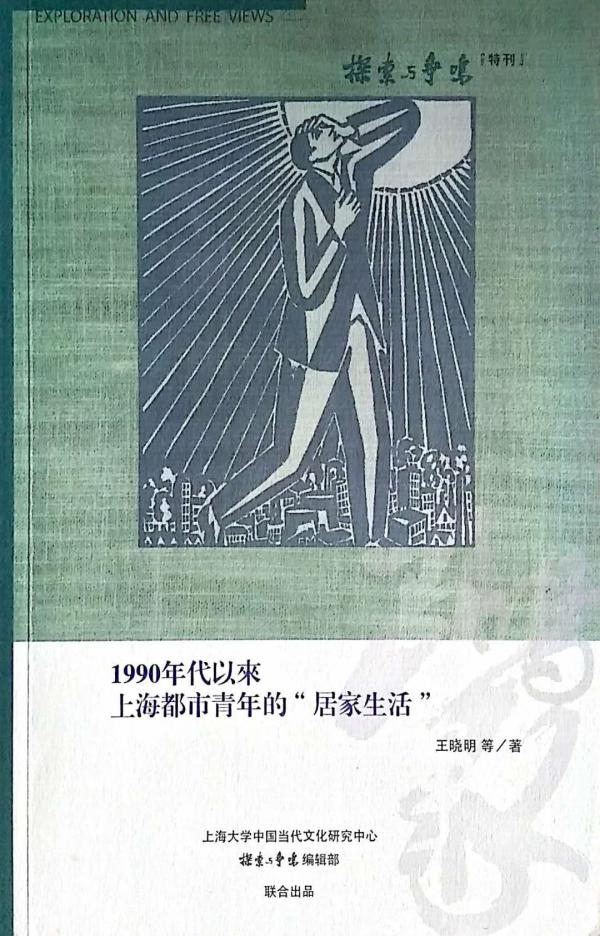
《1990年代以來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王曉明等著,《探索與爭鳴》(特刊)2016年。
第三本書《居住的政治》則是關于“保家”,更聚焦業主身份在公共領域中的作用。這是一本研究當代中國大城市業主維權的論文集。通過這本書中所集結的業主維權案例可以發現:在遇到產權糾紛時,業主身份并不能完全給予保障。業主所面對的侵權方往往是地方政府或者開發商。在這種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中,侵權方使用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雙重的組合,以權力的邏輯對業主群體進行打壓和分化。
而就業主群體本身而言,一方面物權法所賦予的業主權利,在面對權力邏輯時處于弱勢。另一方面業主身份帶來的更多是割裂而非團結。因為產權是可以不斷分化的,每個業主的產權都可以因為電梯、樓層、位置等財產邊界而被不斷切割。通過這些維權失利的案例可以發現,業主身份并不一定能夠保證“家”的穩定。

將這三本書連在一起,能發現在缺失均等“國民身份”的前提下,差異化的居住身份使得“家”呈現出“脆弱性”(陳映芳《房地產政策與當前社會生活秩序的脆弱性》[J]. 探索與爭鳴,2016/05)。《尋找住處》中無家可歸的上海人案例,揭示了戶籍身份的不均等和不連續,使居民因為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而難以重建家庭關系。在《居家生活》中,部分上海青年雖然可以憑借經濟實力在市場上獲得業主身份,但其結果則更有可能是一種內縮的生活狀況。這與住房保障的缺失,購房給家庭帶來的壓力過大不無關聯。在《居住的政治》中,業主在面對擁有權力的利益集團時很難維權成功,“業主身份”在權力邏輯中并不一定能保護房產。
不可否認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戶籍身份”和“業主身份”是當前“家”的兩重關鍵保障。然而如果沒有均等的“國民身份”支撐,“戶籍身份”、“業主身份”就來自于差別對待,而非平等的賦權。正是遵從了這種差異化的身份制邏輯,身份就成了一種特權而非權利。隨著權力結構的變化,曾經許諾的身份很可能就成了一紙空文,脆弱不堪。
相較于差異化身份的消極屬性,在這三項研究中也能發現以“家”為核心的積極實踐。《尋找住處》中無家可歸的上海人并非悲慘被動的生活,他們有權利意識,能主動的聯系救助組織改善居住狀況。他們能夠通過讀報、守信等生活細節,來維持自己作為“上海人”的體面。在《居家生活》中,租戶們雖然沒有產權身份,但卻能每年更多的邀請朋友到家里做客,過一種外向型的生活。在《居住的政治》中,雖然業主維權屢戰屢敗,然而產權身份促成了最初的集體行動,并能夠“跨區聯合”形成跨越產權邊界的組織。業主的“再組織化”是基于聲望、公正等更高的價值,實現了從保衛“小家”到團結“大家”的躍升。
在以上案例的行動中,“戶籍”和“業主”等具體的居住身份是不可或缺的肇因。然而行動者的主體性來自于實踐的過程。通過實踐,行動者才能調動起來各個不同的身份,打破邊界,明白每一個“家”都需要均等的國民身份作為公平的基礎。
“家”的邏輯是什么?將“無家”、“居家”和“保家”聯系在一起,會發現“家”是以居住身份為契機和載體的實踐過程。在這里,張少春提出的“做家”(family making)的概念很值得借鑒(張少春《“做家”:一個技術移民群體的家庭策略與跨國實踐》[J]. 開放時代,2014/03)。在當代新加坡華人工程師的移民過程中,家庭是一個在國民身份的基礎上不斷組合和選擇的過程。由于國民待遇的差別,移民家庭內配偶雙方一般會各自選擇不同的國民身份,從而實現最有利的福利待遇組合。最終,一家人都通過不斷的行動而維持著動態“在一起”的狀態。
“做家”這一表述,指出了在高速變動的時代,維持家庭關鍵是“營造關系”(working relation)。在這個過程當中,穩定而均等的國民身份是基礎,是一個現代國家的基本品格。然而身份只是實踐的開始,而非實踐的終點。只有家庭成員能夠不斷地行動,在血緣的根基上因為創造而不斷地“再組織”,這或許才能讓“家”打破差異身份帶來的命運幻象。
[此文首刊于《城市治理研究》(第三卷:家庭危機與生活秩序,陳映芳 主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經授權轉載。]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