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歸化、自由帝國與保守憲制——高全喜對話田飛龍(上)
【編者按】
理查德?博克(Richard Bourke)生于1965年,現任英國倫敦瑪麗女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學術專長為政治思想史,特別是啟蒙時代的政治理論。其專著《帝國與革命:埃德蒙?柏克的政治生涯》(Empire &Revolution:The Political Life of Edmund Burke)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5年推出,全書厚達一千頁,以伯克的全部印刷著述和手稿為基礎,鮮活呈現了傳主的主要思想關切。
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生于1729年,卒于1797年,愛爾蘭裔英國政治家、作家、演說家、哲學家、政治理論家,曾于英國下院擔任近三十年的輝格黨議員,在政治立場方面反對英王的北美政策,支持北美殖民地和北美革命,對法國大革命持批判態度,被后世視作英美保守主義思想的巨擘。其代表性著述多已譯為中文,包括:《自由與傳統:柏克政治論文選》、《美洲三書》、《法國革命論》、《關于我們崇高與美觀念之根源的哲學探討》等。
高全喜教授生于1962年,哲學博士,現任上海交通大學凱源法學院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憲法學、立憲史、法理學、中西法律思想史。主要著作包括:《自我意識論:<精神現象學>主體思想研究》(1990)、《法律秩序與自由正義: 哈耶克的法律與憲政思想》(2006)、《現代政制五論》(2008)、《立憲時刻:清帝遜位詔書》(2011)、《政治憲法學綱要》(2014)等。
田飛龍副教授生于1983年,法學博士,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及法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憲法與行政法,代表性著作包括:《香港政改觀察:從民主與法治的視角》(2015)、《中國憲制轉型的政治憲法原理》(2015)等。
2017年2月10日,高全喜教授在其北京西山寓所邀請田飛龍博士就英國學者理查德?博克有關埃德蒙?柏克的上述專著及相關話題展開思想性對話。《開放時代》2018年第1期以“歸化、自由帝國與保守憲制”為題刊發了本次對話。
澎湃新聞獲得授權,分兩部分予以轉載。以下為本次對話的上半部分。

一、歸化法與憲制保守性
田飛龍:高教授,您好,很高興再次有機會與您進行學術對話。我記得大概從2011年開始,我們圍繞政治憲法學、辛亥革命、“八二憲法”與政協問題相繼進行了四場學術對話,這些對話于我而言是思想學習與探討,于您而言則是思想表達與體系化。
您的學術路徑很有改革時代學人的典范性,從德國古典哲學轉入英美經驗哲學再進入法哲學與憲法學領域,近年來更是以一種糅合歷史、哲學與法學的方式開辟出“憲制發生學”的獨特路徑,作為中國政治憲法學的新樣式。我也很高興看到您這些年的學術成果有了某種“學術編撰”的結果,即您在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政治憲法與未來憲制》(2016年)和《自由政治與共和政體》(2017年)。今天我們對話的主題與這些學術脈絡是高度吻合的,您希望談一談柏克的保守憲制理性。
高全喜:是的。柏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與憲法理論上非常獨特,也非常重要。一般憲法學者很少談及柏克,確實柏克也不大好談,他的思想相對駁雜多元,缺乏體系上的明晰化,與憲法學者理論審美上的形式要求不大相合,但這不代表柏克不要談或者不需要深讀。
我很高興看到你在香港訪學期間翻譯出版了一本柏克思想傳記《埃德蒙?柏克:現代保守政治教父》以及你對柏克政治憲法思想的初步研究。那本傳記的作者是英國保守黨資深議員杰西?諾曼(Jesse Norman),他痛心疾首于英國當代政治對柏克傳統的某種遺忘或遮蔽,這表明柏克對于當代英國乃至于整個現代政治世界仍有重要意義。
我也曾指導過一位博士生張偉,他專攻柏克的政治憲法思想,后來還在中央編譯出版社出書了,即《埃德蒙?柏克與英國憲政轉型》(2015年)。
我們這一次的對話首先是與另一本新近出版的大部頭柏克思想傳記《帝國與革命:埃德蒙?柏克的政治生涯》(Empire &Revolution:The Political Life of Edmund Burk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有關,作者是理查德?博克(Richard Bourke),倫敦瑪麗女王大學(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的政治思想史教授。另一個機緣是與我最近關于美國歸化法的研究有關,我發現歸化法問題背后是深刻的政治人性論及保守憲制理性問題。
田飛龍:歸化法的視角,很有意思。這恰恰與美國憲法政治的當代走向密切相關。我注意到反移民是特朗普競選綱領的重要內容,而其就職后推行的針對穆斯林的移民禁令正是對美國公民資格與歸化法框架的憲制調整,但似乎美國社會對此有分裂意見,背后折射的是平權革命帶來的自由多元主義與特朗普代表的保守主義之間的規范性沖突。
美國盡管總體上是一個自由開放的“族群熔爐”,但排外法案與事件時有發生。我最近在閱讀美國愛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法學教授絡德睦(Teemu Ruskola)的《法律東方主義:中國、美國與現代法》一書,其中提及19世紀80年代的“排華法案”之憲法理據就在于中國移民生長于東方專制主義的文化與法制之下,缺乏美國公民所必備的權利、法治與美德觀念,不適合納入美國社會。如今,對華人的“東方主義”想象與排斥日益轉移到與異教徒及恐怖主義有關的穆斯林移民身上。特朗普試圖以保守主義的思維與行動維護美國的民族特性與公民宗教,反對無限開放的多元化立場對美國文化與社會的侵蝕和消解,這里面的價值張力很大,甚至觸及政治不正確。
高全喜:英國人也反對無節制的移民,尤其是缺乏技能、認同與美德一致性的難民,否則為什么要脫歐呢?
我的理解是,英國脫歐與特朗普當選反映了英美社會保守主義的某種回潮,其背后的預設是:什么人適合做美國公民或英國公民?什么人與英美憲制根植的社會觀念及美德傳統相一致?英美社會的身份政治邊界何在?如何通過政治和立法重新尋回英美社會的保守理性傳統?與之相對照,借助平等價值的人權革命帶來了越來越“無界”的多元主義,在普遍的相互承認與妥協中逐步喪失原則與美德立場,以毫無文化與道德標識的“裸人”作為政治與社會權利的前提,這種思維方式恰恰是柏克曾經明確反對的。
當然,我對美國歸化法的研究不是要呼應某種極端的種族主義或民族主義,也不是要徹底反對作為當代自由主義主流立場的多元主義,而是要提供一種必要的保守主義反思資源和維度。我覺得柏克是最適合的一種思想資源。不僅我這么想,我感覺到西方學術界也在這么想,需要共同追問:與保守主義有關的社會性、美德及身份政治在當代自由主義政治與法律秩序中還具有何種地位和作用?這樣的根本問題不嚴肅對待的話,將很難解決西方當代社會面臨的團結、凝聚與道德維系問題,也很難解決“東方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傳統與自由的平衡性問題。應該說,這是一個具有基礎性、普遍性的政治人性論與憲法秩序論的問題。
田飛龍:博克教授其人與其書就是您所稱的西方學術界的反思性現象。博克本人是學者,而諾曼本人是政治家,他們共同認識到了重溫柏克保守主義的重大意義。諾曼在書中將您所謂的自由多元主義稱為“自由個人主義”(liberal individualism),將之作為西方當代社會之權利泛濫、道德失序與社會崩解的思想根源。
當然,這種保守思想傾向或傳統本身并不新穎,因為我觀察到西方社會內部一直存在對啟蒙現代性的某種保守傾向的保留意見,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內部歷來有保守派與自由派之分,其某種較為激進的權利案件裁決每每處于風口浪尖,比如1974年的墮胎自由案以及近年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案。柏拉圖在《理想國》末段談及政體衰變論時,對民主政體經由“一切趣味平等”帶來的權利泛化與道德原則虛無化的情境描述,似乎得到了當代西方某些政治法律現象的印證。所以,我們討論柏克,不是在反對自由主義,而是重申自由主義的保守之維,亦即自由的德性基礎。
高全喜:自由當然應該稟有德性,但也不是那種特別“厚”的美德,與古典美德政體還是有區別的,但如果德性太“薄”,也會出問題。
對美國歸化法的研究還與我個人的旅行觀察經驗有關。我接觸過或聽人談論過中國去美國的移民以及其他國家的移民,有個印象是,這些人中不少人在原來的國家或者涉及犯罪,或者涉及腐敗,或者個人品行較差,或者宗教觀念極端,他們更多的是在消費美國文化,而不是學習和認同美國文化。不管他們持有的是綠卡,還是公民資格,他們仍然是美國文化與共和國的“他者”,是道德意義上的“外邦人”,甚至是潛在的“敵人”。
美國的自由民主與福利安排或許可以包容他們,這是美國文化與價值觀決定的,但我們似乎也可以反過來想一想:本土的美國人是否真的歡迎他們?這些人在美國越來越多,對美國文化與社會的品質到底是一種增進還是倒退?美國雖大,但資源空間也是有限的,而其政治與道德實際上也不可能是無邊界的。
所以,我看到你的譯作、張偉的博士論文以及博克教授關于柏克思想的巨著,非常欣慰,也激發了我深談柏克的興趣。
田飛龍:好的,我大體理解您的問題意識與討論旨趣了,那我們現在就從博克教授的這本巨著談起吧。
二、帝國與革命的雙重變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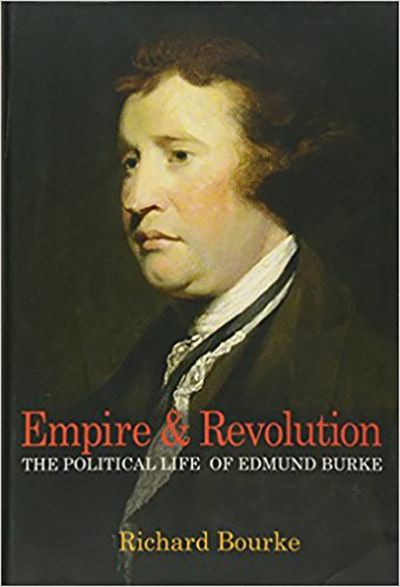
田飛龍:說起博克教授此書,跟我譯的諾曼的書還真有些淵源。諾曼議員在書的“致謝部分”明確感謝了博克教授研究文章的啟發,尤其提到了博克教授關于柏克1757年《論政黨》(On Parties)一文的研究。
當然,我覺得博克教授對諾曼議員的啟發不限于此。著名政治思想家波考克(J. G. A. Pocock)教授對博克此書的評價甚高,認為“我們對柏克作為政治家和哲學家的思想理解從此得到了無與倫比的加深與拓寬”(該書封底首則推薦語)。我想問您,這本思想傳記與以往的柏克傳記有何不同?(波考克,1924年生于英國倫敦,在新西蘭接受中學和大學教育,1974年起任教于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1994年退休至今。——編注)
高全喜:接觸這本傳記要特別感謝蔡孟翰教授,是他的推薦與溝通使得我們第一時間看到了這部巨著。就我的印象,包括你的柏克傳記譯作在內,博克此書是柏克思想傳記中最厚的一部,長達1000頁。我一開始比較納悶,柏克雖然重要,但并非體系化的思想家,怎么能寫成這么厚的思想傳記?讀完之后才大體明白了,此書完全配得上給人第一印象中的厚重感。(蔡孟翰是日本千葉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副教授。——編注)
大體而言,我認為此書對柏克之思想研究具有兩個主要特點:
其一,這首先是一部傳記,作者對柏克的人生史研究很深很全面,大體按照柏克的人生主要階段劃分,將柏克思想與大英帝國的時代事件緊密結合,史論互濟,不同于單純的柏克傳記或柏克的某個哲學主題研究,給我們的印象是實現了柏克之事業實踐與思想發展的深度關聯,以及政治家與哲學家身份的深度關聯,呈現了多重張力與復雜面向上的柏克。
其二,該書又有超出一般傳記的思想研究特征,因為作者同時還是政治思想史學者,不過因為所處理的對象是柏克這樣缺乏體系化以及側重“行動哲學家”定位的人物,其思想片段與政治事件之間分分合合,常有巨大跳躍,因而不能完全根據其思想文本來處理其思想,而需要在政治實踐與思想文本之間來回穿梭,反復比對,這無疑增加了柏克思想研究的難度,但博克教授駕馭得很不錯。
所以,我既將這部巨著作為柏克的又一本傳記來看,也當做柏克政治思想的研究著作來看。
田飛龍:您對該書的傳記性與思想性的把握很到位。我閱讀的體驗是,該書在人物傳記性上或許不如諾曼議員的著作,但在學術思想性上要超出,當然這與二者各自的職業定位也有關系。議員主要從政治家一側理解柏克,而學者主要從哲學家一側理解柏克,但他們都盡量做到了兩面兼顧。回到博克此書,我發現他從柏克一生諸多的思想關鍵詞中選擇了兩個,即“帝國”與“革命”,您覺得這是為何?
高全喜:這不是偶然的,可以說柏克本身就是帝國政治家和哲學家,一生主要時間供職于帝國權力的核心——議會平民院,但他又身處一個特定的革命時代,這個時代就是18世紀中后期,歐洲啟蒙運動正在經由資產階級革命實踐而主要在西方文明世界范圍內重新規劃和奠基“一種新的政治科學”(托克維爾語)及其憲制體系,人類歷史上兩場最為重大的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正在醞釀爆發。這兩場革命都與歐洲啟蒙運動直接相關,與人權及自決權的理論發現直接相關。
美國革命的直接意義在于成功挑戰了大英帝國的憲法秩序,開啟了“非殖民化”的自決先例,在大英帝國的龐大身軀與版圖上鉆出了一個巨大的豁口。當然,美國革命的意義并不限于“非殖民化”,更在于通過《獨立宣言》和1787年制憲而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科學”,美國憲法的典范性或者一種超越英帝國的民主憲法模型在北美大地成長成熟。法國革命在思想與歷史先例上對美國革命有所借鑒,但主要根植于歐陸自身的啟蒙激進主義思潮與建構主義的哲學傳統,其原創性、徹底性、顛覆性和破壞性遠遠超過美國革命。
可以說,這兩場革命挑戰了兩種帝國秩序:美國革命挑戰了光榮革命后的英帝國秩序,這是一個自由帝國,但在殖民地維持著某種支配性的威權統治;法國革命則挑戰了法蘭西的封建專制帝國,這個帝國無論是在內部秩序還是外部殖民秩序上均有專制成分。作為帝國政治哲學家的柏克深陷于兩場革命的洪流和攪擾之中,對美國革命之自由精神予以高度肯定,但對法國革命的激進性則予以徹底否定。柏克的《法國革命論》可以說是那個火紅的“革命時代”中孤獨的智者之聲,若干年后回望,我們不得不佩服柏克的政治洞察力與思想定力。如果沒有柏克聲嘶力竭的思想與政治平衡,英國議會改革走偏甚至模仿法國革命的激進運動未必不可能,輝格黨內部就出現過對法國革命的誤判與禮贊,這種黨內分歧甚至造成了柏克與黨友的政治決裂。
田飛龍:是的。實際上柏克研究者常面對柏克之思想不一致性的難題,主要的依據就是柏克對這兩場革命的立場。同樣是啟蒙運動背景下的自由革命,柏克褒揚美國革命而貶抑法國革命,表面看來似乎很不一致。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有過非常尖刻的批判,認為柏克是資產階級小人,其在兩場革命中的立場陡轉完全屈居于一種政治賄賂邏輯,在美國革命中被北美殖民者收買,而在法國革命中則被英國君主收買。
與柏克同時代的潘恩(Thomas Paine)原來對柏克頗有好感,但也因其對法國革命過分負面的立場而決裂,憤然寫下《人的權利》加以系統反駁。吊詭的是,為法國革命竭力辯護的潘恩最終卻差點死在雅各賓派專政的斷頭臺上,華盛頓總統沒有施救,法國革命當局也沒有寬宥,只是因為死刑執行的細節失誤而幸免。對法國革命的激進和暴虐本質,柏克的政治直覺超過了潘恩的自由常識。我重譯過潘恩的《人的權利》,感覺到其中融貫著一種歐陸氣質的激進人權觀與民主革命激情。(托馬斯?潘恩生于1737年,卒于1809年,美國政治活動家、哲學家、“建國之父”之一。——編注)
某種意義上,無論人們持何種立場及是否喜歡,柏克與潘恩都構成了無可取代的思想豐碑,成為現代政治世界之左右政治話語的經典來源,而現代政治秩序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對柏克與潘恩進行平衡與再平衡的結果。
高全喜:我覺得柏克在兩場革命中的一致性是可以證成的:其一,他是帝國政治家與哲學家,帝國主權及其利益自然是無法回避的出發點與思考原則;其二,他是英國式自由的捍衛者,因此無論是英國王權對自由的威脅還是英國議會對北美自由的威脅,甚至東印度公司的暴政,對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壓制,都是他反對的對象,他認為英國式自由應當是普遍和公正的。所以,嚴格而言柏克是一個服膺于英帝國憲法秩序、維護光榮革命傳統的“自由帝國主義者”。柏克以自由之名為北美辯護,同樣以自由之名反對法國大革命。
博克教授在書中正確還原了柏克思想的一致性:其一,柏克肯定征服者權利,但反對這種權利在“帝國化”過程中演變成的“征服精神”,認為這是一種歷史倒退;其二,柏克維護一種英國傳統下的“自由精神”,這是其政治人生的一根紅線與底線,誰觸犯就反對誰。博克教授的考辨與論證進一步印證了我關于柏克思想一致性的學術判斷信心。
我想再延伸一下關于柏克之帝國利益原則的思考。柏克認為帝國秩序與自由事業并不矛盾,甚至帝國權力本身應當成為擴展自由的基礎和保障,他內心之中是希望英國式自由在北美、印度、愛爾蘭等殖民地獲得憲制保障的。當然,這里有個限度,即殖民地自由的擴展不能損害帝國主權與帝國根本利益。柏克所期待的英帝國是一個“自由帝國”,他本身是“自由帝國主義者”,這是他對帝國政治學與帝國政治行為的理想性設定。
但是,現實并非完全符合理想,甚至與理想相悖,因為實際統治帝國的是各種政治派系,他們有各自私利,未必能夠自覺地理解和踐行一種自由帝國的政治理想。所以,盡管在帝國主權問題上柏克與其同僚們保持立場上的一致,但是當帝國議會通過北美征稅法案以及帝國放任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治理暴政時,柏克就以自己的方式展開了政治斗爭:前者體現為《美洲三書》式的議會辯論,后者體現為針對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漫長而艱難的彈劾。(沃倫?黑斯廷斯生于1732年,卒于1818年;1772至1785年任英國首任印度總督,回國后于1787年受到腐敗彈劾,但1795年被宣告無罪。——編注)
我們一方面看到的是柏克在政治事務上的洞察與務實,另一方面又看到了柏克在自由政治原則上的堅守,這種堅守即便付出再大的政治代價也無法令其退卻。
田飛龍:我很敬佩這樣的柏克。我愿意沿著帝國利益政治的角度再往下談。我覺得除了自由政治原則的融貫性之外,柏克對兩場革命的立場差異應該還與革命本身對英帝國利益與秩序的沖擊力度不同有關。美國革命遠在天涯,美國革命領導者只是追求殖民地獨立自治,無意于反向輸出“革命”,而且美國革命在其綱領與原則上對英國憲法借鑒和運用頗多,博克教授的思想考證印證了這一點。
所以,北美盡管獨立,但一方面對英帝國秩序基本盤沒有大的沖擊,多米諾骨牌的革命效應沒有在其殖民地即刻發生,另一方面,美國革命在原則上屬于英國憲法遺產的落實而非顛覆。柏克從美國革命者及其憲法實踐中看到的是一個英國的“復制品”,而不是相反。
當然,美國革命的結構性創新也是有的,《聯邦黨人文集》確實構成了一種“新的政治科學”,但美國革命的基本原則仍然是英國式的。
法國革命則不同。法國革命建立在抽象的人權論基礎之上,其所理解和追求的自由并非傳統秩序中的自由,而是一種嶄新的抽象自由。因此,法國革命實踐了一種不同于英國革命及美國革命的新原則,標志著革命內涵的新開端與創新意義。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論革命》中具體考察過法國革命的創新意義。(漢娜?阿倫特生于1906年,卒于1975年,德裔美國政治理論家。——編注)
柏克維護帝國,法國人追求解放,都是以自由為名。看來,自由的魔力或者歷史恩怨正在于其多義性。
高全喜:這里涉及一個對柏克的經典定位問題:柏克到底是自由主義者,還是保守主義者?柏克生前就與英國政治中的輝格黨、托利黨牽扯不清,但大體上是一個輝格黨人。柏克死后,兩黨都對柏克進行思想遺產的不同詮釋與爭搶。我國20世紀90年代也曾發生過柏克的屬性之爭,劉軍寧的柏克與蔣慶的柏克很不相同,但我覺得他們刻意放大了柏克的某一面向,未能完整理解柏克。(劉軍寧,生于1961年,現任文化部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蔣慶,生于1953年,曾任教于深圳行政學院,2001年于貴州修文縣龍場鎮創辦陽明精舍,任山長至今。——編注)
柏克是這樣的歷史站位:在英國政治內部,相對于維護王權的托利黨,柏克偏于自由的輝格黨立場;在歐洲政治對抗中,相對于法國式的激進自由主義,柏克偏于保守的英國憲法立場,此時無所謂托利黨還是輝格黨,而是一種克服了內部政治分歧的光榮革命式的英國立場。所以,柏克既是保守主義者,也是自由主義者,我稱之為“保守自由主義者”。
這里涉及對柏克保守主義的正確理解。柏克的保守主義是有特定語境和指向的,而不是毫無內容的、價值中性的保守主義,更不是與專制傳統有關的保守主義。具體而言,柏克的保守主義是英國自由傳統下的保守主義,柏克是要保守英國式的自由,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內容。因此,柏克保守主義不同于歐陸式的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主義,也不同于儒家式的文化保守主義。(約瑟夫?德?邁斯特生于1753年,卒于1821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保守主義思想家。——編注)
田飛龍:英國式的自由,這個概念非常重要,構成了柏克保守主義的實體價值內涵。不過我們似乎要適當區分保守主義的兩個層面:
其一,作為方法論的保守主義,主要是一種思維方式與治理哲學,處理的是傳統與變革的關系問題,柏克在這方面提供了具有普遍意義的教誨,支持一種改良主義的變法模式,反對激進革命,這一層面的保守主義似乎可以適用于一切人類社會,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某種意義上也符合這里的保守改良主義,在保持政治體制穩定的條件下“摸著石頭過河”,漸進式創新,增量式發展。
其二,作為價值論的保守主義,這就打上了濃重的英國式自由的價值觀標記,對英國這樣的“自發秩序”而言似乎理所當然,但對于其他社會,不僅是東方社會,也包括歐陸社會,則是需要經過較為激烈的革命才能造就英國式自由的具體內涵的。也就是說,為了獲得英國式自由的實體內涵,在手段上很難采取與英國式保守主義完全相同的方式和路徑。法國革命乃至于中國近代革命常被作為激進主義的典型加以分析乃至于批判,可似乎又有某種歷史必然性,因為法國與中國都不具備英國式的自由傳統以及英國保守主義的自發秩序。
作為方法論的保守主義具有人類歷史經驗上的普遍性,但作為價值論的保守主義要在英國與歐陸及東方社會之間通約,則有很大的難度。也因此,中國改革開放可以從容接受方法論的保守主義,但無法接受英國式的價值論的保守主義,無法在東方社會價值與英國式價值之間實現真正的和解與兼容。至今,我們在以方法論的保守主義“保守”著中國作為東方社會及社會主義社會的諸多價值與體制機制,但與英國式價值論保守主義有關的自由民主與規范法治進程仍然處于有限進步和艱難轉型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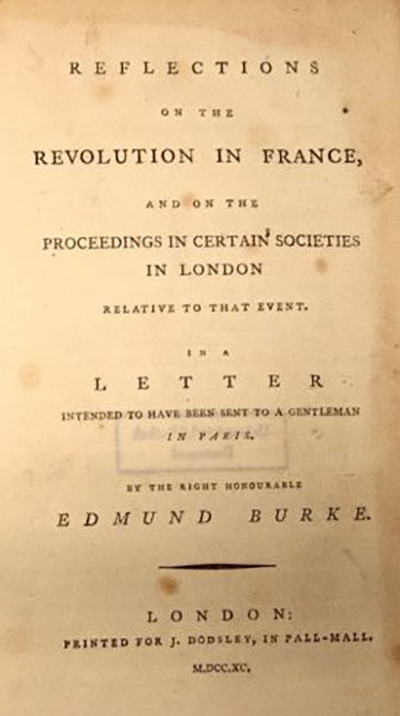
高全喜:價值上的梗阻確實是英國式保守自由主義在中國難以普遍化的重要原因。中國的改革邏輯與英國的保守主義“形似”而“神異”。所以,自由派里有人提出“繼續啟蒙”的命題,有人不回避“激進主義”問題而呼喚“大轉型”,也有人為法國大革命辯護,認為盡管存在種種缺陷,但如果不發生那場革命,法國的自由秩序難以生成。
自由不僅是一套理念,也需要具體的實踐技藝,柏克見證了英國、美國和法國三種主要的實踐模式,服膺英美方案而貶斥法國方案。當然,柏克思想在此是頗具張力的:他的《法國革命論》應對的與其說是法國社會的激進革命本身,不如說是法國革命“范式輸出”對英國式自由的直接而具體的威脅。
在博克教授的書中,柏克將法國革命的“原罪”歸結為對歐洲文明根基的摧毀,具體而言是在財產權、宗教權與慣例權三個層面加以激進改變。
在財產權層面,英國普通法和代議制的核心憲制使命就是保護私有財產,并認為這是社會團結與凝聚的基礎,是文明積累與演進的根據,但法國大革命肆意剝奪有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以革命的階級批判名義否定財產權的合法性,宣揚抽象人權與平等觀念,這主要損害了法國貴族的利益及美德。
在宗教權層面,英國保護宗教自由,而法國大革命卻以激進的人權教義否定傳統宗教的合理性,攻擊和鎮壓僧侶階層,剝奪宗教財產,過度張揚世俗主義自由,人為割裂宗教與社會的天然有機聯系。
在慣例權層面,英國對傳統社會秩序予以尊重和保護,對組成社會的主要利益集團及其慣例性特權予以法律化;但法國大革命以抽象人權和社會契約理論為基礎,將同意原則轉化為即刻的人民直接行動,將建制化、分層化的“社會”予以虛化,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建立“無社會的共同體”,并在道德上對慣例性權利一概作為封建特權予以批評和否定。
柏克認為,通過上述三個層面的摧毀行為,法國大革命造成了一個廢墟式的法國社會,而其政治承諾就是依靠當代人的理性建構可以塑造一個嶄新的理想社會,這種革命的激進主義變成了過度浪漫化的社會革命實驗,造成了法國社會長時段的動蕩失序與巨大的人權人道災難。
田飛龍:法國大革命的激進社會實驗思想來自于啟蒙的理性樂觀主義,認為人類的理性知識進步已經足夠掌握“宇宙真理”而能夠俯視和改造一切舊有傳統和秩序,逐步遺忘了歐洲文明史中日積月累的保守理性傳統。這種啟蒙理性主義甚至在霍布斯身上早有體現,他認為國家是“人造的人”,可以像大玩具一樣先拆卸成零件再重新組裝。
革命就是一種社會實驗,但傳統分類上存在“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之別,前者以英美為典型,后者以法國甚至中國革命為代表,區別在于是否承認和保全傳統社會。社會性在某種意義上確實構成了柏克的保守自由主義與盧梭或潘恩式的激進自由主義的本質差別:前者是一種關于自由秩序的社會本位,人性必須在具體的社會性與社會秩序中養成文明內涵并維護該種秩序,而不是一種脫離具體社會語境、自由自在的原子化個體;后者是一種關于自由秩序的個人本位,認為人性可以脫離具體文化和社會屬性而成為自足的“裸人”,社會實驗可以根據這樣的“裸人”標準按照理性契約論的方式進行。
此外,柏克保守主義將憲法秩序理解為“過去的人、現在的人和未來的人”的連續統一體,每一代人的立法主權是有限的,是需要受制于多代人實踐累積而成之保守憲制秩序的,但激進自由主義的理性根據完全與歷史無關,甚至歷史本身就是需要批判和虛無化的對象,從而為每一代人確立了無限的立法主權,可以與傳統秩序完全割裂,越徹底越革命,越革命越進步。可見,柏克對兩場革命之立場不一致背后恰恰反映了英國式保守自由主義與歐陸式激進主義之世界觀與哲學傳統的深刻差異。有意思的是,您原來是德國哲學背景,后來轉向英美經驗主義傳統而且深深服膺蘇格蘭啟蒙運動思想,應該對柏克與歐陸思想的差異有更深刻的體會吧?
高全喜:我的思想轉向對我而言既是一種學術資源的拓展,也是一種價值觀的重新選擇。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體系化偏好及內蘊的革命激進因素相比,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經驗主義更值得探究和守護。這里既有實踐政治意義上英美做得更好的原因,也有蘇格蘭啟蒙思想內在理性根據更充分的因素。
近些年,面對大陸新儒家“重新公共化”的挑戰和壓力,我作為同情儒家甚至中國之文化保守主義的自由派,一方面肯定儒家的某種道德與社會價值具有憲制意義上的補充性意義,另一方面善意提示了儒家普遍化的“蘇格蘭道路”,即如若要將儒家發展為一種普遍主義的道德哲學與政治理論,就必須如同當初“蘇格蘭啟蒙運動”那樣實現理論智識的結構性突破與真正的普遍化。目前來看,儒家保守主義的特殊主義、泥古主義甚至與政治權威的獻媚主義仍然占據主導,這樣的儒家是不符合人類文明發展潮流的,也是不可能具有普遍主義前景的。
你剛才提到了方法論保守主義,我覺得是一種“薄”的保守主義,雖可在全世界通約,甚至中國的改革邏輯中也有體現,但其中的“自由秩序”并不彰顯,所以我理解和中意的可能是一種偏于價值論的保守主義,那是一種“厚”的保守主義。當然,因為其“厚”,在實踐上就更加艱難,與東方社會的價值融合及學理貫通就更加復雜,但也因此更有學術和實踐上的重大意義。自由價值的生成需要代際選擇與揚棄,也需要立法者決斷,但更重要的是一種訴諸經驗和社會實踐的滲透與培育過程,英國式自由也不是天生的,也是多代人實踐與經驗積累的產物。真正美好的價值一定是有吸引力和生命力的,我確信這一點。
田飛龍:博克教授可能沒有那么強的“中國關懷”,而主要是呈現作為英國及歐洲語境的柏克。柏克產自英國,是那個時代風云際會之思想與政治復雜互動的產物,在跨國或跨文化語境中加以消化,必然有不同的側重與方向。
綜合來看,柏克之一生在政治上并不成功,在思想上亦不體系化,在單純的政治家與哲學家名單里,他都很難居于榜首,但就其自身定位的“行動哲學家”而言,他堪稱時代第一人。博克教授與諾曼議員都將柏克一生歸結為“五場戰役”的偉大斗士,其政治故事與思想故事是兩面合一、相互建構的,你可以說他的思想文本(常常是演講詞或宣傳小冊子)是政治實踐的一部分,也可以說他的政治實踐是思想過程的一部分。這“五場戰役”沒有確定的先后順序與時間節點,而是交互貫穿于柏克主要的政治生涯,哪個議題凸顯、急迫或有政治突破可能性時,他就即刻轉移到哪個議題戰場,像一匹沙場老馬一樣太過熟悉于政治戰場的具體味道與風云變幻,又像一個高妙的棋手一樣同時在人生格局上布下了五個棋盤。
博克教授的思想傳記亦追隨柏克本身的實踐歷史而在五場戰役之間輾轉跳躍,合拍起伏。這“五場戰役”分別是:
第一,英國憲法與議會改革,主旨在于限制王權擴張和濫用,推動政黨政治規范化,同時避免議會改革的激進取向,維持英國憲法秩序的內在平衡與穩定;第二,北美殖民地危機與革命,主旨在于維護帝國主權及北美殖民地自由,在價值沖突中優先為自由精神辯護;第三,愛爾蘭自治與宗教寬容問題,主旨在于推動愛爾蘭天主教徒的自由權利保護以及愛爾蘭自治的制度進展,但反對愛爾蘭的激進叛亂;第四,印度治理改革與黑斯廷斯彈劾問題,主旨在于通過議會立法確保印度的正當治理以及通過彈劾黑斯廷斯對東印度公司的殖民暴政加以政治問責;第五,法國大革命及英國憲法鞏固問題,主旨在于批判和揭露法國大革命的反文明本質,阻卻法國革命向英國的輸出,鞏固英國憲法的制度自信與自由秩序定位。
高全喜:同時下著五盤棋,不是一般人。博克教授抓得很準,首先將柏克定位為大英帝國憲法秩序中的“行動哲學家”,以其面對革命挑戰的政治與思想回應作為敘事主線,其次是根據柏克政治人生的“五場戰役”交叉敘事,從全書目錄來看,避免了“單一事件”敘述的單調與失準。柏克對帝國利益的維護是恰當而有限的,限度在哪里呢?就在“英國式的自由”那里。注意是“英國式的自由”,而不是其他意義上的自由。
革命前的北美殖民地主張和實踐的就是一種英國式的自由,因而柏克認為不必強制征稅并施加單方威權,而應當進行憲法“歸化”,柏克甚至提議了作為歸化方案的新聯邦制模式,但未獲采納。即便是美國革命也符合英國式的自由,所以他并不排斥美國革命,但法國大革命意圖摧毀英國式的自由,所以即便以啟蒙價值觀和自由革命的名義,本質仍然是暴政與極權行為。柏克在《法國革命論》中不僅預言到了革命后的秩序動蕩,甚至也預言到了秩序重新穩定需要出現“軍事強人”,拿破侖印證了他的先見之明。
當然,我們這里的對話主要是就《帝國與革命》的思想主旨展開深入討論,同時初步觸及了柏克思想定位、域外影響乃至于中國化的問題。其實本書皇皇巨著,有太多細節值得聚焦和賞讀,但限于篇幅很難一一展開。
事實上,由于柏克不是體系化哲學家,其具體的思想文本只是思想體系的顯性部分,如果不精通當時段的英國史細節以及對柏克政治人生有細致把握,閱讀本書就會有很強的隔膜與跳躍感。盡管博克教授盡量進行了思想語境的復原工作,但也只能是一種盡可能的而且必然也是主觀的、來自當代偏見下的有限的解讀與修復,是柏克思想世界的一次導游工作。所有導游都有時間與場景限制,都有路線偏好,博克教授也不例外。
因此,博克的“柏克”只是柏克思想的一種深度游模式,同樣不能替代我們對柏克原著的直接閱讀以及對柏克思想長期而艱難的自主探索與整合。但是,我們有充分理由感謝博克教授,他做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柏克思想導游。
田飛龍:若美國革命前之憲法歸化成功,或許就沒有后面無比恢宏的美國世界史了。其實美國革命不是一步抵達的,北美殖民者在訴諸革命之前相繼援引了憲章維權、普通法維權與帝國憲法維權等多種模式。我翻譯過麥基文(Charles Howard McIlwain)的《美國革命的憲法觀》,其中有非常精彩的歷史分析。(麥基文生于1871年,卒于1968年,美國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美國革命的憲法觀》英文初版于1923年,1924年獲得普利策歷史類寫作獎。——編注)
作為美國革命元勛的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在18世紀70年代初甚至以“馬薩諸塞人”的筆名寫作了大量論戰與策論兼具的憲法文章,設計并提議過一種在帝國憲法框架下區分“帝國主權事務”與“殖民地自治事務”的二元憲制模式,介乎聯邦與邦聯之間,類似于一種“一國兩制”的憲制構想,但在相對僵化的英國議會主權與殖民主義憲制邏輯下喪失了和解與實踐的機會。于是,探索新聯邦制憲法模式的歷史機會就給了革命后的美國。(約翰?亞當斯,生于1735年,卒于1826年,美國第二任總統及第一任副總統。——編注)
博克教授在書中提到,晚年柏克對美國憲法贊賞有加,對英國式自由在北美新憲法下的保障與擴展頗感欣慰,印證了柏克一生對“自由精神”融貫一致的理解與支持。
高全喜:呵呵,小氣的英國未能“歸化”美國,而日后的美國反而以“熔爐”憲制“歸化”整個世界,當然這種歸化是有條件和邊界的,是以認同和增進美國文化與社會價值觀為前提的。作為世界級的思想家,柏克未充分關注過中國,或許是因為當時的中國還處于“世界歷史之外”(黑格爾語),但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顯然注意到了柏克。在中國自由秩序原理與實踐的進展中,柏克不可或缺。(待續)
(本文原刊于《開放時代》2018年第1期,原題:“歸化、自由帝國與保守憲制”。略去文后注釋,正文有刪節并略加重新編輯,編注為澎湃新聞編者所所加。經對話者審閱,并經授權刊用。)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