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院士訪談 | 蘇州大學,潘君驊院士
欄目介紹
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和相關要求,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中國光學》自2021年第1期開始開辟《院士訪談》專欄。
本欄目將結合訪談、自述等多元化形式,記錄院士們在成長、教學、科研等經歷中難以忘懷的故事,以及他們對人生、科學、教育等問題的認識與思考,以此彰顯老一輩科學家的愛國奉獻與創新求實精神。
《院士訪談》欄目由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著名光學專家陳星旦先生悉心策劃和組織。陳先生雖年逾耄耋,但仍親自邀約各位院士,召集相關編輯人員進行匯編整理,逐字逐句審定終稿。陳先生的辛勤付出,實為本欄目之質量保證,深為本刊同仁所景仰尊崇。
《院士訪談》欄目將持續開展,衷心希望廣大讀者通過本欄目,認識他們、了解他們,從而有所啟迪、有所收獲。
《中國光學》編委會

人物小傳

潘君驊,1930年10月生于上海市。應用光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蘇州大學現代光學研究所研究員。
1952年清華大學機械制造專業畢業后分配至中國科學院儀器館(中科院長春光機所前身)工作。1956-1960年,到蘇聯列寧格勒普爾科沃天文臺學習,師從蘇聯著名天文光學專家馬克蘇托夫,獲副博士學位。1980年,調至南京天文儀器廠,主持2.16米光電望遠鏡研制工作。2000年受聘于蘇州大學現代光學研究所。長期從事光學元件及儀器研制、加工和測試工作,在組織大口徑光學工程項目實施、倡導非球面應用、推動光學檢測技術發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學習經歷
1 動蕩歲月,輾轉于十一所學校
我1930年出生于上海吳淞,童年時期相對還算太平。1932年淞滬戰爭爆發,我家就搬到嘉興,在嘉興北門秀城橋附近離外婆家很近的地方造了兩間二層樓房。因為離得近,經常去外婆家玩,有時也到嘉興南湖游玩。
小時候過得還算無憂無慮,思想比較活潑,很能自娛自樂,聰明但也淘氣。我是家里功夫最好的,尤其擅長踢毽子,有一次踢得滿頭大汗,脫了棉襖,著了涼,落下了咳嗽的毛病,一到冬天就犯,過了很多年才好。
小學到中學期間,時局動蕩,但父母非常重視子女教育,一直竭盡所能要我們上學。當時的政府也很重視,即使在日寇鐵蹄之下,也盡可能辦流亡學校,幾間茅屋就可以上課。所以八年時間里,我讀完了小學、初中和高中。不過讀過的學校就很多了,累計上了4所小學、3所初中、4所高中。
1935年,我上了嘉興中學附小,讀了兩年,學校比較正規,校舍也很好。那時姐姐已經上五年級了,我就每天跟姐姐一起上學、放學。小學時雖然識字不多,但很喜歡讀哥哥姐姐們的課外讀物。那時非常好奇,有次聽姐姐一個養蠶的同學說,吞吃活的春蠶夏天就會皮膚涼爽不怕熱,我還真吞了一只。那段時間里我記憶中最美好的,就是學會了《賣報歌》《總理紀念歌》《國旗歌》等歌曲。
1937年七七事變后,父親帶著全家逃難到莫干山。莫干山本來是有錢人避暑的地方,但時局混亂,上山避暑的人很少,空房子好找。我家在“陰山”下坡不遠處的一個房子住下,旁邊有一所公益會小學,正值秋季開學,我正好就讀三年級——也許大人就是沖著這所小學而選擇這里。小學三年級下學期又轉到崗頭村一所辦在“一統飯店”里的小學。
父母擔心在山上常住會影響孩子上學,于是1938年暑假后決定下山,但由于嘉興的房子被一個日本商人占用,我們只好去上海,在那里住了四年。
當時家庭經濟已經沒有保障了。父親先是租了間辦公室掛牌行醫,但沒有根基打不開局面,很快就撤了。后來到莫干山的武康衛生院,他一個人去工作,但小孩要讀書,家還在上海,開銷比較大,生活很苦。大哥二哥都在上海中學,開始是走讀,后來住校,因為家里經濟困難,他們一方面申請獎學金,一方面自己在雜志上投些翻譯稿掙些稿費貼補。
我上的是一所比較高檔的私立小學,叫“正志小學”,本來學費很貴,但通過父親的朋友減免了學費。小學時算術學得比較好,還在比賽中獲過獎。學課文也有點興趣,喜歡古文,有時候還配著音樂唱。最怕的是記日記和寫作文,因為教語文的老師很嚴厲,如果我成績不好還會挨打,不過她對工作認真負責,上學和放學時都站在校門口接送學生。
小學時我在學習上毫無自覺可言,而且因為很頑皮,老師常去家里告狀。大哥二哥學習成績都很好,母親最操心的是我的學習,經常對我說一定要好好學習,將來能找個好工作自立,否則只能去拉黃包車,或者去求大哥二哥討生活。她對我提出的其實只是最低要求,并沒有要我們靠讀書光宗耀祖。只是那時候太小,不懂事,管不住自己。
1941年夏天,母親帶我到父親工作的莫干山過了一個暑假,結果誤了考育才中學的時間,只好到不遠處的“京江中學”讀初一上學期,學校在法租界外。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后,日寇進入租界,京江中學停辦,我又轉到博文中學讀了半年。1942年,家里經濟愈來愈困難,父母決定搬到父親工作的安吉縣小村(后改為曉村),就讀武康縣立初中。
當時開設的課程很多,包括國文、代數、英文、史地、物理、幾何、音樂、體育等。印象最深的是教物理和幾何的老師。他很有學問,教學方法也很好,多是啟發式的,經常提出問題但不馬上解答,而是留出點時間引導學生多思考。他愛讀書,也喜歡釣魚,我對他在村邊小溪邊看書邊釣魚的印象很深。我和小伙伴們也經常到村邊的小溪或小池塘中抓蝌蚪、捉魚蝦,有時候還自制些工具抓,提升效率。
抗戰時的國民政府對辦學還是很重視,許多臨時中學都是在逃難過程中臨時組建的,雖然條件比較簡陋,但學生仍然不少。教師背景差異很大,既有大學的教授,也有私塾的老先生,但總體還是不錯的,許多優秀的教師也是一邊逃難一邊教學。
1943年夏,武康縣中和武康衛生院從安吉縣的小村搬回莫干山,從家到學校要走很長的路。也是大概從這時候開始,我才有點讀書的自覺性,已經能夠很專心地聽課,思維緊跟老師講解。上學時很認真地記筆記,經常得到母親的夸贊,這個習慣給我以后的工作也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初中畢業后,進入孝豐縣境內的中正中學。學校條件很差,校舍也是借用的民房。在那里讀完高一上學期后,本來打算寒假后繼續讀,結果1945年春節后傳來消息學校不能開學。父母一直想盡辦法讓我們讀書,但那時條件實在不允許,我只能在隨后的一年里失學在家。其間,母親不斷要求我復習之前學過的課程,我也在樓下弄了個固定的位置,計劃每天自學,不過因為玩心太重,堅持得并不好。
日本投降后,我家搬回了嘉興。1946年春,由于嘉興中學只有浙西一中的學生可以轉學入讀,我只好插班進入私立秀州中學讀高一下學期。后來通過插班生考試進入嘉興中學,讀高二、高三直到畢業。當時國民政府浙江省嘉興專員很重視人才培養,以個人名義在學校設立了專項獎學金,專門授予高三物理、高二代數的第一名,我高二時正好得了一次。
1948年我在嘉興中學畢業,準備參加高考。因為一直以二哥為偶像,我的第一目標是上海交大機械系,志愿報了交通大學、同濟大學、浙江大學,都是機械系。
我那時自認為考取的把握很大,無心復習,暑假時還經常去旁觀大人們打麻將,結果一所理想的大學也沒有考上,只考上了同濟的預科。沒辦法,只好去同濟大學預科學了再說。學了一個學期后,回家對父母說感覺學不到東西,就不再想去了。
父母也同意,于是我插班到南洋模范中學讀了高三下學期。南洋模范中學是全國有名的中學,高水平教師薪資很高,一些老師寧愿放棄交大講師,甚至是副教授的職位到南模任教,因此聚集了一批學術淵博的名師。比如當時的物理老師就直接用英語授課,讓我們不僅學到了物理知識,還提高了英語聽力水平,一舉兩得。我雖然只在南模讀了半年,卻深感受益匪淺。
這段時間我一心要考上好大學,洗去落榜之恥,暫時不能回家時就在校認真復習功課。第二次高考,我收到了交大、清華和浙大的錄取通知。
2 北上清華,與天文結緣
本來我是決心要上交大的,第一批南方新生已乘火車出發,我還在等交大的報到日期。后來哥哥接到北大的錄取通知,他是一定要去北京的。這時候我做了一個重大改變,就是我也要去北京,上清華大學。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交大是工業管理系錄取了我,而清華是機械系,可以免去轉系的麻煩。這個決定對我的人生軌跡是影響深遠的。
于是我就參加了清華第二批南方新生的集體北上行列。火車過長江需要專用渡輪,整個過程大概要兩個小時。在浦口等車時,一個清華老生還用上海話給新生講天文知識。
一年級的課程都是基本課,我除了規定的幾門正課外,還慕名聽了華羅庚先生的數論課,甚至放棄機械系的木模課去聽物理系葉企孫先生的光學課。
當時我對大學普通物理有個錯誤概念,認為和高中物理差不多,不大當回事,結果第一學期小考沒有及格,到大考時有點急了,下功夫復習了一番,考了90多才把平均分扳回來。
清華物理系高年級學生自發組織了“天文學習會”,我也參加了,并且很認真的聽報告,做讀書筆記,有時候也翻譯英文雜志上的文章,甚至還用父親的老花鏡和二哥的近視鏡做了個低倍率伽利略望遠鏡。
二年級開始有了機械課的主要課程,后來又分了機械制造、汽車和熱工三個專業,我選的機械制造。那時我開始有點鉆研意識,自發到圖書館去找機械制造方面的雜志文章,還翻譯了一篇關于“無心磨床”的文章。
大學三年級時,由于國家建設需要,要提前畢業。在畢業前,我看到報上消息,王大珩先生等人向政府建議成立儀器館,我想這個機構很符合我的目標。分配前,中科院到學校招人,當時的思想教育主要還是服從分配,我抱著試一試的心態第一志愿填了儀器館,第二才是服從分配。后來正式公布,我被分到儀器館,只不過有點小遺憾,地點變成了長春,而不是之前了解的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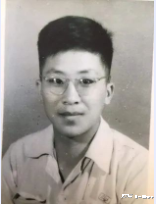
大學畢業時的潘君驊
二、蘇聯留學
分配到儀器館后,我們先在科學院本部學習了兩個月左右,期間繼續參加天文學習活動,參觀了泡子河古觀象臺的古代天文儀器,后來才到長春。儀器館在鐵北,相當荒涼,只有三個研究室和一個試制車間。
我剛到時先是被分配到技校教書,包括代數和金工。備課很認真,講到游標卡尺時,我為了更嚴密,還自己推導了數學表達式。后來被安排做沼氣檢定儀、氣體流量計等工作。當時大量的科技文獻都是蘇聯的,學俄文是技術人員的必修課。1952年剛到儀器館不久,科學院就要求長春的單位組織突擊學習俄文。儀器館比較重視學術交流,東德蔡司廠的專家、英國的教授、美籍華人等都來作過報告。后來儀器館為了進一步培養俄語人才,指定了包括我在內的6個人脫產學習,期間還到北京為國家的“十二年科學規劃”做了一段俄文翻譯。
1956年5月,我和同事接到所里通知,準備去蘇聯學習。我有點受寵若驚,也有點壓力,工作已經4年,不知道還能否適應讀書生活。
我被派到蘇聯科學院的普爾科沃天文臺,導師是馬克蘇托夫系統的發明人——馬克蘇托夫院士。他給我定了研究題目和要看的書,安排好了車間的實習內容——磨一塊160毫米、F/6的拋物面鏡。

留學蘇聯時在光學工廠學習磨鏡片(右)
我學習上很努力,主要想的是至少不給國家丟臉。第一年研究生的四門課都得了5分滿分,工廠實習也很努力,磨玻璃得心應手,老師評價我磨好的拋物面鏡“好得很”。
初到蘇聯的前一兩年,我住在郊外,感覺十分孤單,好在那時住城里的留學生都愿意到郊外玩,星期日經常有熟人來。我也很樂意在國內來人訪問時去做翻譯,陪他們訪問蘇聯國家光學研究所和國家光學機械廠。
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普爾科沃天文臺也組織了人工觀測,我出于新鮮也認真地參加了觀測,還獲得了天文臺發的積極觀測者證書和紀念章。
國內天文界和蘇聯聯系多,到普爾科沃天文臺實習和訪問的人很多,很多蘇聯的天文學家也到過中國,對中國印象很好。比如做天體測量的一個教授非常關心中國留學生的學習以及生活,有一次把好幾個學生請到家里做客。
1956年留學生國慶獻禮,我和另一個實習生向老師提出要做一個200毫米口徑的天文照相物鏡,老師聽了很吃驚地說,“要做這樣一個光學鏡頭,這個小光學車間只怕全得交給你們了”。經過幾次交涉,他也替我們著想,建議我們做一個馬克蘇托夫系統,相對要簡單很多。這時紫金山天文臺的一個實習生正好過來,我們非常賣力,加班加點,我3天內搞出了光學設計,他們2個人一個星期就磨好了鏡頭。
第二年起就進入課題,導師給我的題目是“大望遠鏡二次凸面鏡的檢測”。他的期望是對Hindle方法做一個全面計算和分析研究。
檢驗凸面鏡最頭疼的是必須要有一束能包容被檢鏡的會聚光束,而這束會聚光束要由一個輔助的凹面鏡產生。我在做的過程中發現,包容被檢鏡的會聚光束,最小的應該是與它的法線重合的,只要讓這束光帶有和被檢鏡法線一樣的像差,就可以實現檢驗光路。Hindle方法中會聚光線不和法線重合,因此它的輔助凹面鏡就較大。于是我就推導如何計算這個輔助凹面鏡的公式,實際上就是將反射檢驗的補償原理用在凸面檢驗中。公式分析和計算結果都表明,這個輔助凹面鏡必須是一個橢球面鏡,詳細計算得到的最佳尺寸是被檢鏡的1.5倍左右。而Hindle方法的輔助鏡是被檢鏡的2.2倍左右。當然我這個方法有一個缺點就是輔助鏡是非球面,但老師認為這個缺點問題不大,因為橢球面鏡可以自檢,而且非球面度也不大,容易做,但對大口徑鏡面而言,縮小檢驗鏡的口徑十分有利。這樣就找到了一個新的檢驗方法,比Hindle方法有一點優越性,論文重點也就移了位置。我用這個新的檢驗方法檢驗并磨出了天文臺正在做的PM700望遠鏡的凸面鏡,既加強了自己的論文,也為臺上解決了一個不小的問題。
我把這個新的檢驗方法寫成文章,先投到國內的《天文學報》發表,想使國內先受益。一個蘇聯女研究生知道后,叫我馬上寫成俄文在普爾科沃天文臺臺刊上發表。蘇聯研究生實習期間需要在所內做一次學習報告,我就把已經做好的和下一步要做的想法作為報告內容講了一通,結果被評為優秀,還獎勵了一個月的研究生津貼。
老師說起我這個方法,指著自己說“我自己怎么就沒有想到呢?”。我心想,要是老師全都想到了,那學生還做什么?
后來我回國后,老師來信說城里的工廠按照我的方法加工、檢驗了6米望遠鏡的凸面副鏡,工廠里的人稱我的這個方法為“潘氏法”。
還有一次老師高高興興地來講他新近推導出的一個公式,是用于最后收斂馬克蘇托夫式光學系統設計的,是手工計算。我抱著學習的心態自己推導了一遍,結果發現有一點小錯誤,就去和他說了。正好他在用這個公式時,發現總不能一次到位,心里很不自在,后來用了我改正的公式,非常利索地一次解決問題。他很高興,表揚了我,還對其他研究生說“你們只知道聽,聽過就算了,應該像潘那樣……”,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1960年7月末,我順利通過了論文答辯,按時完成了四年學習任務。老師在我的畢業鑒定上寫道:“帶這樣的研究生感到一種愉快,一種滿足”。看來他對我這個學生還是滿意的。離開普爾科沃天文臺時,他還到公交車站送我,和我貼面告別。
主持我畢業論文答辯的麥爾尼科夫院士在一次采訪中也對我的工作大加贊賞,通過塔斯社進行了報道。回到國內后,《中國青年報》和《北京日報》還根據這篇報道專門刊登了一條關于我在蘇聯學習不錯,得到蘇聯好評的短消息。
三、科研生涯
1 參與150-1,建立大口徑光學儀器制造基礎
回到長春不久,受時局影響,加上本身性格原因,我的基本想法是要多做點技術工作。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在蘇聯的研究課題屬于光學檢驗的關系,我被分在光學室的檢驗組,但沒有給具體的題目。
不久后,長春光機所開始接受靶場光學測試儀器研制工作,開始是仿瑞士的EOTS,后來所里對科研任務有了新的打算,要接更大的靶場儀器任務,也就是150-1,我的主要工作也轉移到了150-1項目上。
參加150-1時接到的具體任務有兩個,一是做王大珩先生提出的實驗,實測在一定的對空張角下,天空背景在地面的照度隨太陽不同夾角的變化。為此我專門做了一個木框架的紙管,用我自己的一個照相測光表測了數據。二是要我通盤考慮光機所做150-1,在光學技術方面還應做哪些準備。這件事涉及的問題多,因為光機所過去都是做小口徑的,200毫米的已經是最大的了。我考慮主要問題有三個:一是沒有磨大鏡子的機床,包括粗磨和拋光;二是沒有檢驗大口徑光學部件和系統的方法;三是沒有檢驗需要用的專門儀器。
我遇到的第一個具體問題是,所里科技處問我,為磨60厘米中間試驗望遠鏡而專門設計的、剛組裝起來的磨鏡機,是不是能用來磨150主鏡?我實地看了這臺機器的試車情況,只覺得開動起來就像開動蒸汽機車,噪聲和振動都很大,而磨光學元件最犯忌的就是磨鏡機本身的振動。原來設計這臺機器的人自己不懂磨鏡子,他沒有用傳統的皮帶輪,而引入了新的無級變速機構,即兩個相互倒置的鋼錐體,外面套以鋼環,靠摩擦傳動,用撥叉移動鋼環就可以實現無級變速。而皮帶輪可以吸收掉齒輪減速機構帶來的振動,這個鋼輪無極變速反而自身產生了極大的振動。科技處要我直接向所領導匯報,所領導聽完后立即放下手頭工作,親自到現場看。看后立刻表示同意我的意見,還要我提出另做機器的設計方案。我根據在蘇聯和國內紫金山天文臺看到的機器,提出了設計方案,最大可以磨直徑800毫米。
所里也有人在研究刀口檢驗,并做了一臺很笨重的刀口儀放在實驗室,但無法實用化。刀口儀的關鍵在其頭部,一定要本身很輕巧,便于隨時挪動,基座不能也不需要大而厚重,不能要求待檢件去湊近儀器,所里設計的恰恰違反了這點。于是我根據蘇聯刀口儀的記憶,提出了設計方案,做了好幾臺。后來天津光學儀器廠問光機所要了圖紙去,略加修改變成他們的產品,生產了一大批。使用刀口儀,根據陰影圖判斷待檢對象好壞,不是任何人稍微學學就能會,而是要有一個學習和熟練的過程的。所里要我對光學車間和裝校車間的一部分人員做系統培訓,我就先寫出講義,再專門講了幾次。
150-1的光學部件中,它的前端保護窗的磨制是一個難題,直徑有630毫米,厚度只有30毫米。雖然只是保護窗,但光學質量要求同樣很高。對它的平面,只能采用Commom法檢驗,就是要有一個長半徑標準球面鏡。為此我先花了很長時間和工人一起磨了一個曲率半徑12米的標準球面鏡,為了使這塊保護窗從機器上取下時不變形動足了腦筋。兩個表面分別磨好后,還要做一個透過檢驗,這要求有一束大口徑平行光,但大口徑平行光管還沒有,我就考慮能否利用那個標準球面鏡,在小角度的匯聚光束里檢驗,通過簡單的光學計算,表明引入的球差很小,完全可以忽略,這樣我對這塊保護窗的光學質量就完全可以控制了。
150-1進入裝校程序后,科技處要我考慮光學系統的最后檢測問題。對這樣的口徑不算太大的系統,一臺大口徑平行光管是必不可少的。科技處在我的建議下,決定做一個口徑700毫米的大平行光管以及一塊標準球面鏡。平行光管的主鏡是球面鏡,焦點前加兩片改正鏡,這樣的設計磨制周期最短。這個平行光管在裝校車間發揮了很大作用,2005年,我有一次回長光所到裝校車間參觀,看到還在用。我堅持要做標準球面鏡、標準平面鏡和大平行光管的思想,是在蘇聯時老師馬克蘇托夫反復講過而形成的。
2 主持216工作
1959年,紫金山天文臺提出自主研制2米級大望遠鏡。為了世界排名可以在前5名以內,定下的通光孔徑是2.16米,并組織南京工學院機械系師生,以蘇聯正在研制的2.6米望遠鏡為藍本,很快完成了設計。后來牽頭單位轉到長春光機所,所里帶了一套藍圖到蘇聯,要我聯系2.6米望遠鏡的機械設計負責人,請他提提意見。蘇聯2.6米望遠鏡的總設計是亞米尼亞人,在普爾科沃天文臺兼職,每周四到天文臺來。我通過天文臺和他聯系好,把全套圖紙給他看,他看后認為圖紙上問題太多,沒法一一指出,但從機械設計的角度提了一些意見。后來圖紙放在我在蘇聯的辦公室里,都沒有帶回去。
2.16米望遠鏡因為經濟困難暫時下馬,改為先做60厘米的“中間試驗望遠鏡”,為做2.16米主鏡向蘇聯訂購的鏡坯不久后運到了光機所。150-1任務開始后,長春光機所決定放棄做2.16米望遠鏡的牽頭單位,將60厘米望遠鏡和一批技術人員分到西安光機所,由龔祖同先生負責。還有幾個原機械所的,已接觸60厘米中試望遠鏡的技術人員則直接去了南京天文儀器廠。
1975年,216工作重新啟動,經王大珩先生推薦,我以出差方式參加,而且當了技術組長。從1976年到1980年,我出差到南京的時間很多。那里條件很差,住在天儀廠的招待所,吃食堂,有段時間甚至就住在食堂前的一排平屋內。一方面我是想調回南方,另一方面也是喜歡天文望遠鏡,所以一直堅持了下來。
1980年,我正式調到南京。我介入的時候總體方案已經經過開會確定,不需要我考慮總體方案的問題,也根本不可能再改方案,幾個大件的加工已和上海的廠家談簽合同,所以如何進入角色是個問題。我立定的主意是只有排除一切干擾,踏踏實實做好工作一條路。我全面考慮之后覺得應該從看圖紙著手,一是看設計上有沒有原則錯誤,二是看各部分之間有沒有矛盾。
看過圖紙后,感覺問題最大的是“中間塊”的重量太重,達到9噸,鋼板沒有必要用20毫米厚,但具體設計人員堅持不同意減薄。其次是赤緯軸的剛度不夠,以致其彎沉導致的光軸指向精度達不到要求。而這兩者又是有關聯的,如果中間塊減輕,緯軸變形也就小了。
當時管理上還是計劃經濟年代的模式,院機關組織了“八大件”的設計審查會,還專門針對中間塊的設計開了一次會,請了力學所的一位研究員做力學計算。他也覺得原設計過重,當時還沒有有限元分析軟件,他用材料力學的解析公式做了計算,建議將中間塊的內層改為10毫米厚的鋼板。在此基礎上,設計者才同意將內層鋼板由20毫米改為10毫米,于是中間塊的重量也由9噸降到了6噸。緯軸方面也盡量縮短緯軸的長度,加上中間塊的減輕,緯軸的變形也就達到設計指標。
原設計的主鏡罩是十幾片的花瓣狀開合機構,但局部組裝試驗時,開啟后閉合時,有的葉片總是不能按序動作,因而沒法用,多次修改也不能解決,設計者也很無奈。1980年我去澳大利亞考察時,看到他們2.2米望遠鏡的主鏡罩是對開門式,外觀上雖然不及花瓣式好看,但動作很可靠。因此我建議改為對開門的方式,設計者接受了這個意見,很快解決了問題。
主鏡室設計負責人因為年齡問題,突然提出要退出216技術工作,因為圖紙已經下到車間準備開始加工,部分大件已經鑄出了,暫時找不到合適的人接替工作,這個難題便又落到了我的頭上。我找人協助,技術上仍然是我負責,從仔細檢查零件圖著手,也發現了一些圖紙設計上的錯誤。
主鏡的中間孔要和機械軸的球形面精密配合,但主鏡中間孔加工時沒有到位,有錐度,導致球頭裝到一半就進不去了。有些人主張要修球頭,但這樣一來主鏡孔和球頭的軸向位置就固定了,沒有一點點調整的余地。我力主修主鏡孔,并設計了研磨工具,利用大車間的行車,通過彈簧吊起工具,非常平穩地研磨好了中孔,順利解決了問題。
主鏡坯最初選的是1959年從蘇聯進口的玻璃鏡坯,熱膨脹系數比普通玻璃低,但不及微晶玻璃,而且由于是分層澆成,有明顯接合面,內部雜質也比較多,表面有幾處硬度不均勻,下手再修難度很大。后來上海新滬玻璃廠為216研制的微晶玻璃也有了一塊合格的,于是就著手開始加工。本來一切都做得很好,到了要將鏡坯翻身,精密加工面形時,出了驚天事故。由于廠里管理制度不完善,承包加工的人采用的吊裝鋼絲過細,不小心把大玻璃打碎了。收到消息時,我正準備去機場到武漢參加一個激光應用研討會,當場驚呆了,立刻退掉機票。后來才了解到,工作人員用的鋼絲直徑是10毫米,他只簡單計算了垂直狀態鋼絲繩的拉伸強度,而實際情況是繩的兩端對吊點的張角非常大,受的拉伸力遠遠大于垂直狀態。更嚴重的是在吊鉤下用夾子把鋼絲繩夾了起來,對鋼絲繩產生了很大的剪切力,等于一把剪刀在剪拉緊的棉花繩,這個狀態哪有不斷之理。這塊玻璃打碎后,216望遠鏡只能用那塊不太好的蘇聯玻璃,由于表面層硬度不均勻,只能加手修,造成一些高頻誤差,影響了光能集中度指標。
到了要考慮望遠鏡在南京廠里初裝時,首要問題就是裝配場地。北京天文臺的意見很明確,就是在廠里要能看到星,按常規思維就要建一個能打開屋頂的裝配車間,需要新建。廠里向中科院打報告,從長遠考慮,計劃建一個能裝5米級望遠鏡的裝配車間。科學院也同意了,廠里在四大件車間對面空地上也挖好了預備豎車間基柱的好幾個水泥沉坑。但后來科學院一時拿不出錢,說要等等,這就很被動了,難道216也要停下來等?有人建議我起草寫報告給中科院,說明建裝配車間的緊迫性。我考慮還是得積極想辦法,我原來意見是在四大件的車間里裝,為了能進行觀星,先將屋頂的一部分改造成活動的。但廠里很多人,包括基建部門都反對,主要是怎么防雨漏的問題,這也確實是很困難的事。我又仔細看了四大件車間的圖紙,上面有詳細尺寸,再對照我畫的216總裝圖,發現四大件車間有一排采光玻璃窗,有可能通過它來觀察天空,于是做了具體設計,算出在我們將要觀察的月、日和晚上時段,通過天窗能看到的天區,再從星圖上找,有沒有可供拍照的較亮的星,并專門寫了一個報告,說明利用四大件車間裝調216望遠鏡的可能性。
望遠鏡機械零件基本加工好之后,就要考慮部套組裝,我在長春時弄過經緯儀,雖然尺寸小很多,但基本原理是一樣。我在思索一番后,分了六七個步驟,做了書面準備,給廠里檢驗組的人講了幾次。極軸在大車間吊到基墩上時,也發生了驚險的一幕,因為吊裝動作很大,風險也很大。極軸放在車間比較中間的位置,而行車在靠邊墻的地方。在行車未到極軸正上方時,指揮吊裝人員就指揮起吊,結果行車一邊自己在滑行,極軸也被拖著往邊上移動,這就相當危險了,幾十噸重的大軸碰到任何東西都是事故。我看情況不對,立刻叫停,并叫司機利用行車剎車一點點的讓行車自行滑到大軸正上方,然后慢慢起吊,解決了危機。
216望遠鏡在大車間架起來之后要做的第一步是調好光軸和找到焦點,第二步是測試指向精度,第三步是拍照看星像質量。在廠里主要是測指向精度的重復性。主鏡沒有條件鍍鋁,只能化學鍍銀,銀層很快氧化,反射率立刻就降到30%以下。所以第一次找星、找焦點位置相當困難。幸好我有調光學系統的經驗,還有事前計算很準,晚上天黑后在能觀察的天區有一顆三等星,比較亮,容易找。調好之后進行拍照,短時間曝光,放到視場中間得到星像很圓,沒有彗差,說明光學系統裝調沒有問題。至此216望遠鏡在廠內的調試基本完成。
望遠鏡運到興隆山上后,拆箱、進入圓頂室、吊入觀測層、初裝等工作都很不容易,還好沒有出大的問題。接下來到裝光學件和調光學系統的時候,負責人到合肥學英文,但北臺和法國人的國際聯測計劃早已排好日期工作,不能等他學完再做,我又不得不擔起責任。好在這時大家配合很好。調光軸時發生了一個問題,就是軸上有點彗差,總是去不掉。時間節點到了,北臺說這次是光譜觀測,剩點彗差關系不大,結果216是帶病開始工作的。幾天的觀測工作結束后,繼續調試,后來發現望遠鏡上有一根上桁架底部的一塊墊板是楔形的,即有方向的,改正后軸上彗差立刻就消失了。之后望遠鏡又做了一次仔細精調,在鉗工的協助下,我將主鏡背后的18個獨立支承系統調到了理想狀態。
1989年12月末,北臺舉辦了216望遠鏡落成典禮,周光召院長、王大珩先生等都參加了,可惜對216工作付出極大心血的龔祖同先生已去世,未能親眼見證它的誕生。

2.16米望遠鏡落成后與研究人員在圓頂室內合影
216望遠鏡運轉了幾年后,進行成果鑒定。鑒定會上王大珩先生對項目評價很高,他認為216望遠鏡好比光學界的長江大橋,鑒定會之后可以申報國家科技獎。后來寫材料、去北京答辯,在答辯會上很輕松地得到了一等獎。
3 推進非球面光學技術應用
我從蘇聯剛回來,就遇到非球面加工技術問題,當時所里正在做紅外分光光度計,其中有兩個不大的非球面鏡,大約70-80毫米,一個是離軸拋物面鏡,一個是較深的橢球面鏡,他們始終磨不好,儀器性能達不到指標。我介入后發現原來是加工方法和檢測方法都不對。他們根據拋物面體數學上的一個特性,即任何平行于該拋物面子午面的平面和該拋物面的相關曲線,與原拋物面的子午曲線完全一樣。這樣理論上就可以用一塊零厚度的刮板,平行于子午面來回平移,就自然刮出一個拋物面。但實際上刮板不能沒有厚度,這就引入了誤差。在檢驗方法上,他們做了一片凸的拋物面金屬刀口樣板去看縫隙,再靠人工修凸出部。說穿了就是用機械方法來做光學鏡面,先做了一個200毫米口徑的平行光管,因為離軸拋物面的線拋物面小于200毫米。那個橢球面,相對口徑比較大,檢驗時需要一個大角度點光源,我提出方案,請光學檢驗組設計了一個廣角光源,設計上它發出的光張角為180度,這樣就順利地解決了橢球面的檢驗問題。在誤差尚大,還不能進行刀口檢驗時,我提出做幾塊頻率不同的線條板,進行目視朗奇檢驗。這樣就順利解決了這兩塊非球面的光學工藝,使紅外分光光度計能達到設計指標。
解決非球面光學加工工藝后,我又陸續將非球面技術應用到微光管、空間相機、車載大口徑光學設備、輪胎面光學元件制造、天文望遠鏡等多個項目與技術領域,取得了不錯的應用效果。
微光管做出來后,最初用的是一個全球面的大相對孔徑Bouwers同心系統。我在蘇聯時就知道這個系統有很大的帶球差,非常影響分辨率,于是提出應該在入瞳處加一塊非球面校正板,光學上和機械上都不需要改動原有結構。做成后效果很明顯,測試時效果比沒有時要清楚得多。后來不知道通過什么渠道,鏡頭轉到南京的華東光學儀器廠生產,他們為了做這塊校正板,還專程到長春來找我幫他們解決非球面制造問題。
在做216望遠鏡同時,我也參與921-1任務中是否采用非球面的討論。經過長達一年多的討論,最終921任務的光學系統還是決定采用非球面。此外空間監視敵方遠程導彈的紅外預警系統,需要有較大的視場,我查了一些資料,看到有報道美國的類似衛星,采用三反射鏡系統,但還沒有設計三反射鏡系統時解初始結構的方法,于是我就在二鏡系統的基礎上,推導出了解三鏡系統的公式。
車載大口徑光學設備方面,解放軍某部需要一種車載戰場偵察設備,口徑比較大,白天夜間兩個鏡頭,攝取圖像后傳給后方指揮部。開始問天儀廠時,被搞光學設計的人一口回絕。后來找到我,我分析了他們提出的要求,認為完全可以用非球面系統解決,就接下了這個任務,一共做了二十幾套。
輪胎面光學元件主要是給合肥中科大同步輻射實驗室做的,當時他們需要幾個輪胎面光學件,只給出兩個方向的曲率半徑,二者相差懸殊,子午面曲率半徑以米計,而弧矢面的曲率半徑只有幾十毫米,我以前也沒有碰到過,初步了解后同意考慮一下。我先分析了這種面形的光學-幾何學問題,認識到如果只給出兩個方向的曲率半徑,真實的表面可以有三種不同形式,并推導出了相應的表達式,我采用了其中易于光學檢驗的一種,即旋轉橢球面的短軸頂點區。從工作嚴謹出發,我又找人實際計算了光束成像后的像斑是否符合用戶要求。這個計算很麻煩,沒有現成程序。做時還要解決如何細磨成形問題。我先加工一根金屬圓柱體,其直徑是弧矢曲率半徑的兩倍,然后切割出略大于所要光學面的一片,以加力使之變形的方法,產生子午曲率半徑,作為研磨工具,實踐證明這套辦法很成功。
1993年,我在南京天文儀器研制中心退休后,仍然繼續從事科研工作。2000年以退休身份受聘蘇州大學,到剛剛成立的蘇州現代光學技術研究所工作,承擔的一些橫向課題也都轉到蘇州大學。期間為南京紫金山天文臺解決了他們1.2米近地小行星課題的一個技術困難,就是1米施密特非球面改正板的制造。因為這時我在南京天儀中心為上海技物所做的1米平行光管還未交貨,正好可以派上用場,解決了他們課題可能被終止的危機。這臺望遠鏡是我國當時光學成像巡天領域里探測能力最強的望遠鏡之一,就是用它發現了編號為216331號小行星,后經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準,紫金山天文臺用我的名字將之命名為“潘君驊星”。
上述這些非球面相關的工作都有一定的開創性,完成以后應該寫出文章。例如:非球面三鏡系統的消像差理論、非球面二鏡偏軸系統的設計理論、輪胎面的加工檢驗方法、單件加工離軸拋物面鏡等。在老伴的積極鼓勵下,我將這些內容整理寫了《光學非球面的設計、加工和檢驗》一書,1994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很受本專業的人歡迎,有幾位年輕人對我說這本書對他們的幫助很大。
我本身是學機械出身,但成果更多的體現在光學方面,這與我對天文的愛好是密不可分的。從大學的天文學習會,留學蘇聯的自制望遠鏡,再到后來的150-1、216等,包括非球面技術的推廣應用,對天文光學的愛好與我的工作相伴一生。因為愛好,我才肯不斷地去用心鉆研,在鉆研的過程中,從機械到光學設計、加工檢測,逐步涉及到光學儀器的方方面面;因為愛好,我才能心無旁騖地專心做好每一件事情,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學習、研究上;因為愛好,我特別喜歡獨立自主的干好每一件事,在實踐中磨礪真知;因為愛好,我更加享受解決問題的樂趣,而不會過分計較個人得失;因為愛好,我也更樂于分享我所掌握的知識、技術,甚至是所謂“絕活”,讓技術造福更多的人。也希望現在及未來的科研工作者都找到自己真正喜歡、愿意為之努力奮斗的興趣所在,并取得更加優異的成績。

在實驗室指導學生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