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蒙古大夫”的形象為何會一落千丈
今天不少人用“蒙古大夫”來稱呼庸醫,而這個錯誤的概念甚至在流行文化中被不斷復制。例如2001年紅極一時的電視連續劇《大宅門》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劇中人物老福晉生病,家人為她找來醫生,孰料老福晉怒斥道:“我不要這些蒙古大夫看病,叫他們治牲口去吧!”而同年7月4日晚間,中央電視臺《夢想劇場》演出的小品中,劇中人物所飾演的“蒙古大夫”,以刀鋸給人看病,把病人嚇得落荒而逃。這些扭曲的信息,盡管在不同程度上娛樂了觀眾,但也嚴重污蔑了蒙古醫學,引發了正牌蒙古醫師的不滿,也因此造成一百多位蒙古醫生聯名控告《大宅門》作者的司法案件。然而十多年過去了,“蒙古大夫”被妖魔化的形象,不僅沒有銷聲匿跡,反而再度躍上電視屏幕。如去年造成收視轟動的電視劇《瑯琊榜》,其原本設定的時代背景為魏晉南北朝,尤其與梁朝(520-557)相符,而劇中主角梅長蘇便將醫者藺晨戲稱為“蒙古大夫”。吊詭的是,蒙古人正式登上歷史舞臺已是十二世紀末,距離梁朝滅亡已逾六百年之久,不曉得《瑯琊榜》的主人公是如何穿越到六百年之后,認識到“蒙古大夫”的存在呢?
上述流行文化中對“蒙古大夫”的蔑視,雖在有識者眼中純屬無稽之談,卻極有可能造成社會大眾對蒙古文化的錯誤認識,甚至嚴重傷害蒙古族同胞的情感。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蒙古人在歷史時期通過與漢、藏、突厥與伊斯蘭文明的交流,形成了豐富而多元的醫學傳統。歷史記載中的蒙古大夫,不僅并非形象惡劣的庸醫,反而是以醫術精湛的神醫聞名于世。究竟蒙古大夫真實的歷史面貌為何?而“蒙古大夫”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負面形象,又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這些都值得人們思考。
元代蒙古人的醫學實踐
根據文獻記載,蒙古人最初的醫學實踐與宗教傳統具有密切的關聯。《蒙古秘史》中便描述了窩闊臺(1186-1241)在1232年攻打女真人時,疑似患有中風而口舌麻木的癥狀,請巫師占卜后,認為是金國的山川神靈所下的詛咒,在拖雷(1192-1232)自愿代替承受詛咒的情況下,窩闊臺遂而痊愈。這種巫醫不分的現象,實際上并非蒙古人所特有,而是普遍存在于人類文化中,如先秦的儒家文化甚至是孔子本人,便深受巫祝傳統的影響。除了巫祝傳統外,蒙古也有獨特的醫療文化,如《元史》記載成吉思汗(1162-1227)西征之時,隨軍將領布智兒與郭寶玉曾負箭重傷命危,成吉思汗命令手下宰殺牛只,將傷者放入牛腹中,遂而得愈。窩闊臺也曾經以同樣的方式,治愈在攻打山西時中箭的漢將謝睦歡。伯顏(1236-1295)在進軍湖北時,部屬李庭被宋軍的炮火重傷幾死,伯顏也用了一模一樣的法子將其治愈。
隨著蒙古帝國的建立與擴張,蒙古統治者在中原各地選拔醫官,在中央與地方成立醫療機構;又編纂《大元本草》等醫書,推動醫療教學。此外,元朝對于醫官設有明確的制度,《元典章》云:“濟世之道,莫大于醫術”,足見元朝官方對于醫學的重視。另一方面,元代蒙古人又通過回回人獲取了來自波斯、阿拉伯與中亞的醫藥知識,如元人忽思慧于1330年撰成的《飲膳正要》中,便融入了不少回回醫學的知識。而成書于十四世紀下半葉的《回回藥方》,更證明了在蒙元的統治下,阿拉伯與波斯醫學知識曾在中國蓬勃發展。由此可見,中國的醫學在蒙元統治時期獲得了積極的發展,可見十三、十四世紀的蒙古人,并不盲目崇拜巫祝治病,而是大力發展實務醫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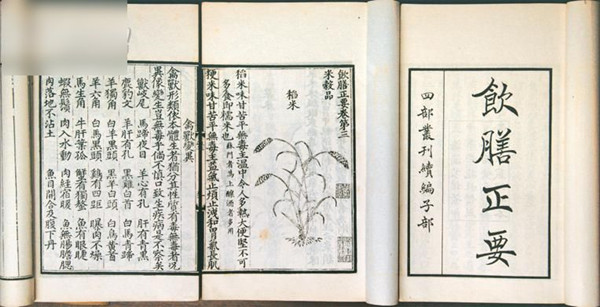
或許有人會問,那么除了蒙元統治者本身善用中原與回回醫生外,蒙古大夫對于中國醫學的發展,又有什么歷史貢獻呢?事實上,即便在元朝滅亡后,蒙元的遺產對中醫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如此,在明清時期的歷史文獻中,蒙古大夫往往以神醫著稱。李時珍(1518-1593)于1578年編纂完成的《本草綱目》,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中醫經典,然而多數人或許不知道,《本草綱目》曾大量引用元人薩德彌實編著的《瑞竹堂經驗方》。不僅如此,《本草綱目》更直接汲取了蒙古人的醫學智慧。例如《本草綱目》記載了牛血的效用:“牛血。傷重者,破牛腹納入,食久即蘇也。”而在《本草綱目》的另外一段落中,李時珍再次說明了牛血的功效,并注明這個方子來自《元史》中成吉思汗以腹罨療法醫治布智兒等人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蒙醫以獸皮包裹治療嚴重外傷的方子,其效用之神奇,在清代廣為世人稱道。
滿人入關以前,就認識到蒙醫腹罨療法與接骨術的精妙。魏之琇《續名醫類案》中記載,在努爾哈赤時期有名叫墨爾根綽爾濟的蒙古人前來投靠,此人精通醫術,在天聰年間先后救治正白旗前鋒參領鄂碩(?-1657)與鑲白旗梅勒額真吳拜(1596-1665)。如吳拜身中“三十余矢,已昏絕。濟令剖白橐駞腹,置拜其中,遂甦”。此外,墨爾根綽爾濟又善于正骨法,曾治愈清初著名隱士苗君稷(1620-?)的關節疾病:“黃冠苗君稷之徒,臂屈不伸,濟先以熱鑊熏蒸,次用斧椎其骨,手揑有聲,使骨穴對好,即愈。”入關以后,蒙古醫生依舊隨著八旗軍南征北討,運用腹罨療法拯救傷患。如雍正九年(1731)和通泊之戰,清軍為噶爾丹策零包圍,幾乎全軍覆沒,副都統塔爾岱(?-1756)突圍而出,“中槍穿脛,血殷征衫,蒙古醫以羊皮蒙之,三日始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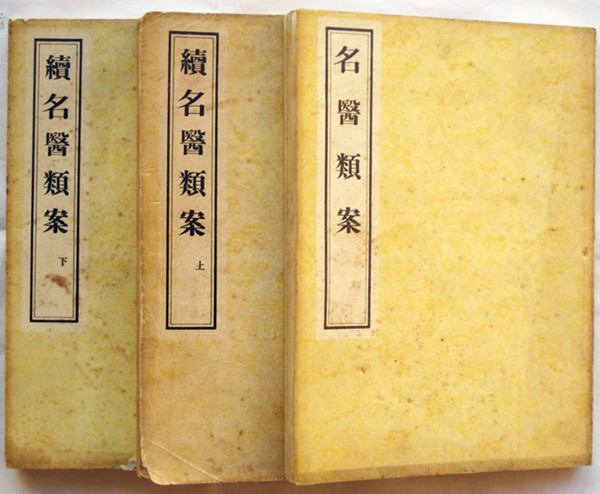
蒙古醫學對傳統中藥知識的擴充
除了以腹罨療法治愈重癥外傷外,蒙醫也擴充了中國醫學在藥物方面的知識。《本草綱目》中記錄了一種名為“鲊答”的藥物,主治“驚癇毒瘡”。所謂的“鲊答”,即蒙古語“Jada”的漢文音寫,指的是一種動物體內的結石。在藥用功效之外,李時珍記載了一條有趣的故事:明嘉靖十九年(1540),湖北蘄州有一位侯屠戶宰殺了一頭黃牛,從牛肚子里得到了一塊晶瑩的石子,沒有人知道這是何物,后有喇嘛答曰:“此至寶也,牛馬豬畜皆有之,可以祈雨;西域有密咒,則霖雨立至。”關于蒙古人使用“鲊答”的記載,可以追溯到1202年的闊亦壇之戰。根據《蒙古秘史》記載,成吉思汗聯軍與札木合聯軍在闊亦壇進行決戰,札木合聯軍中,有人使用“札荅”(Jada)施法招來暴風雨,企圖借此消滅成吉思汗的軍隊;不料暴風雨竟然反倒向札木合聯軍襲來,札木合的手下認為遭到天譴,從而紛紛潰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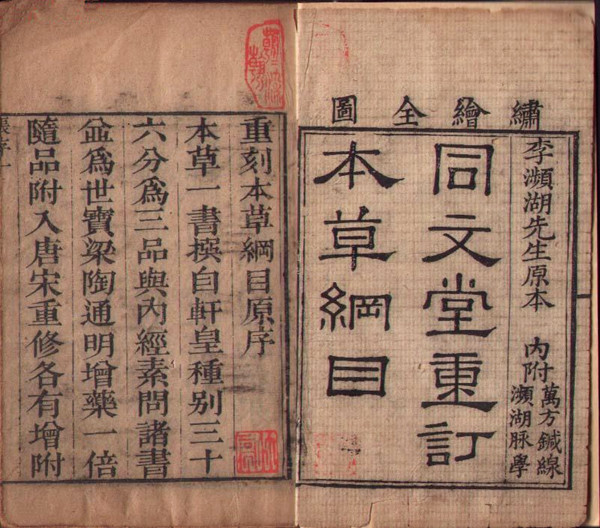
蒙古大夫在清宮醫療體系中的重要性
有清一代對蒙古醫學的重視,不僅反映在醫藥知識的流傳,還落實在具體的制度層面。清朝在內務府上駟院設有蒙古醫士職銜,從上三旗兵丁中選取精通正骨法之人擔任。蒙古語稱接骨大夫為“bariyaci”,字面意思為“捏(骨)者”,在清代文獻中有時譯為“獸醫”,而這個不精確的漢文翻譯也造成了現代人的誤解。今天的人們或許以為,蒙古大夫既然是上駟院的獸醫,醫術自然高明不到哪里去,又怎么能治人的?殊不知上駟院管理的是皇家馬匹,身價非凡,好比今日的超跑豪車。根據《大清會典》記載,皇帝、皇后、嬪妃、皇子與公主在什么場合使用多少馬匹,以及馬匹等級的評選,都有很嚴格的規范;而皇家馬承載的是皇家貴人的生命安全,馬兒平日的健康,自然需要有良醫看管。另一方面,滿洲人自馬上得天下,強調騎射為立國之根本,而上駟院所飼養的皇家御馬又多由外藩所貢,無疑是朝廷重要的門面。這也難怪清朝要謹慎地從出身較高的上三旗兵丁中,挑選善于接骨之人充當蒙古醫士,來照顧這些身價不凡的御馬。
值得注意的是,蒙古醫士除了負責治療御馬外,還有一項特殊的職能,即醫治宮內與戰場上的緊急外傷病患,尤以神奇的接骨術為人所稱道。清朝以蒙古醫士兼治人馬,實際上反映了清朝繼承自蒙古文化的內亞性。在戰場上馬兒可以說是人類最好的伙伴,戰爭的成功與否,馬匹的素質具有重要的決定性。因此在軍隊中配備技術良好,能夠兼顧人、馬的外科醫生,對滿洲和蒙古文化來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由此可見,滿蒙文化中所謂的“獸醫”,往往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處理戰場上的緊急傷患,同時保全戰馬的機動能力,其醫術水平要求甚高;并不像農業文化中的獸醫,僅負責治療一般家畜。
滿人在入關之后,也將這種兼治療人馬的內亞醫學傳統,帶入中原。《嘯亭雜錄》曾明確記載蒙古醫士經常為宮內人員進行緊急接骨手術,“凡禁廷執事人有跌損者,咸命其醫治,限以日期報愈,逾期則懲治焉”。任錫庚《太醫院志》里更明言:“國初依明制,術分十一科……(嘉慶)六年奉旨,以正骨科劃歸上駟院蒙古醫生長兼充。”由此可見清宮的骨科,此后正式由蒙古醫生負責,蒙古大夫顯然并不是只能醫馬的獸醫。如嘉慶九年(1804)曾召原任川北鎮總兵薛大烈(1760-1815)入宮為干清門行走,不料在扈從入禁城時墜馬,跌傷甚重。嘉慶帝立刻“派蒙古醫官前往診治”,同年不久薛大烈病愈,即擢為直隸提督,賞黃馬褂。嘉慶帝之所以指派蒙古醫官救治朝廷重臣,將太醫院的骨科交予蒙古大夫全權處理,顯然是出于對蒙醫的信任。

正因為蒙古人具有優良的緊急外科傳統,不僅清朝皇室對蒙古醫士經常委以重任,漢人士大夫對蒙醫也有極好的評價,甚至往往視為“神醫”。根據黃宗羲《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志銘》及蔣學鏞《鄞志稿》記載,康熙六年進士袁時中(1630-1684)隨同寧南靖寇大將軍勒爾錦前往湖北征討吳三桂,途中因積雪不小心滑落山崖,肋骨嚴重斷裂,而幸有“蒙古醫人,震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其竅,使壯夫接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內陷者還所故。而后纏之以藥,得不死”。在《松鶴山房詩文集》中,陳夢雷(1650-1741)自述曾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夏天“墮馬傷臂”,蒙誠親王胤祉派遣蒙古醫者巴君治療,療效驚人,“眾皆神其技”。陳夢雷為了表示謝意,特別在扇子上題了一首詩,贈予蒙古醫者:“華氏當年技最良,何如俞跗佐軒皇。知君盡得囊中秘,不向龍宮覓異方。”陳夢雷的這首《贈醫者》,不僅充分表達了對蒙古醫術的贊嘆,更見證了蒙漢文化之間的友好交流。陳兆侖(1700-1771)在《紫竹山房詩文集》中也曾自道:“甲申(1764)六月,退直墮馬,傷頂及左支(肢),中指骨折,蒙古醫者為摩其節,族得少差,戒曰須靜息百日。”汪師韓《韓門綴學》正面評價蒙古醫學:“今蒙古醫治跌打損傷有神效,不知其術所由來。”從黃宗羲、陳夢雷與陳兆侖等人的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些飽讀經書、崇尚考據的儒學大家,不僅從未排斥蒙古醫學,反而對蒙醫的接骨術極為贊賞。
蒙醫在漢人士大夫中的正面形象,一直維持到清末民初。1872年5月23日《申報》刊載了一篇題為《醫論》的文章,作者認為西醫雖然長于用藥,但其外科技術“實不如蒙古醫士之良也”;并進一步提出結合西藥與蒙醫的主張:“以西醫之良,若再加以蒙古醫士之術,則天下無廢人。”《清史稿》甚至為乾隆年間醫術精湛的蒙古醫生覺羅伊桑阿立傳,稱其“以正骨起家至鉅富”,并生動描述了覺羅伊桑阿教授正骨的方法:“削筆管為數段,包以紙摩挲之,使其節節皆接合;如未斷者,然乃如法接骨,皆奏效。”
清代士大夫對于蒙古醫學之精深嘖嘖稱奇,而文人墨客更是為蒙古醫生增添了神醫的傳奇色彩。《松江府志》與許仲元《三異筆談》中,提到了刑部尚書張照(1691-1745)曾在承德避暑山莊扈從,不幸“墜馬,仍折右臂,得蒙古醫,療之而痊”。袁枚《續子不語》更是繪聲繪影地描述蒙醫的神效:“京師某官奸仆婦,被婦咬去舌尖,蒙古醫來,命殺狗取舌,帶熱血鑲上,戒百日不出門,后引見奏對如初。”徐珂《清稗類鈔》對于蒙醫的療效也有生動的記載:雍正年間直隸永平知府吳士端(1691-1773)的一位幕賓,在長城邊上車馬翻覆,大腿骨碎裂,“遇蒙古醫,置股于冰,令僵。徐剖肉,視骨,粉碎,為聯綴。緝桑皮紉之,飲以藥,五日而能行矣”。這些記載雖出自稗官野史,難以考察真偽,卻充分反映出清代蒙古大夫的“神醫”形象,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廣為流傳。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是什么原因導致蒙古大夫的形象,從妙手回春的“神醫”轉變為不學無術的“庸醫”?這與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對“東方”的妖魔化不無關系。事實上,在十七、十八世紀時,俄羅斯甚至還派人前來學習蒙醫。《朔方備乘》載:“俄羅斯有學蒙古接骨大夫者,僅康熙年一至。”然而雍正年間,其實也有俄羅斯人來中國學習蒙醫。《張文襄公奏議》:“世宗時,俄國官生來學,于是建俄羅斯館,于是立俄羅斯學。學醫,則遣蒙古醫往。”俄羅斯人不遠千里前來學習,可見當時西方人對蒙醫并不反感。而十八、十九世紀,可以說是蒙古醫學借鑒藏醫理論而蓬勃發展的時期,諸如伊希巴拉珠爾(1704-1788)《甘露四部》、敏如爾占布拉(1789-1838)《方海》與占布拉道爾吉(1792-1855)《蒙醫正典》等集大成之蒙醫經典,均是在這個時期形成。那么為何在十九世紀西方人的心中, “蒙古大夫”的形象竟會一落千丈呢?
十八世紀末,西方興起科學種族論(Scientific Racism),德國人類學者Johann F. Blumenbach(1752-1840)首先建構出“蒙古人種”(Mongoloid)的概念,將東亞人歸類為“黃種人”。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為合理化其在東亞的殖民統治,因而主張優勝劣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高加索人”在演化程度上比“蒙古人種” 更加進步,故而“白種人”有領導“黃種人”的天賦使命。西方生物學家因而開始尋找蒙古人種的體質缺陷,如1866年,英國醫生John L. Down(1828-1896)將遺傳性智能障礙命名為“蒙古癥”(Mongoloid),正是因為患者的面部特征近似當時西方人刻板印象中“蒙古人種”的愚笨形象。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西方帝國主義更是建構了“黃禍”(Yellow Peril)的政治話語,利用重塑西方人對中世紀蒙古人入侵的恐懼,將中國人扭曲為殘酷而陰險的民族。1913年英國小說家Sax Rohmer(1883-1959)創造了一個虛擬的角色“傅滿洲博士”(Dr. Fu Manchu),用以諷刺中國人卑鄙與狠毒的形象。而隨著中國移民人口的增加,美國在二十世紀初也興起了排華浪潮,并且具體反映在庶民文化中,1934年,美國漫畫家Alex Raymond(1909-1956)創作的連載漫畫《飛俠哥頓》(Flash Gordon)中,虛構了一個統治“蒙戈星球”(Mongo)的大反派“冷血魔王明”(Ming the Merciless),用以影射中國人的無恥形象。需要注意的是,二十世紀初的“黃禍論”,往往使用“蒙古人種”的概念泛指“中國人”,因此他們揶揄諷刺的對象,既可以是邪惡的“滿洲博士”,又可以是統治“蒙古”的“明魔王”。由此可見,在二十世紀初“黃禍論”對“東方”的妖魔化之下,“蒙古”一詞開始被貼上“野蠻”、“僵化”、“不科學”等負面標簽。而西方帝國主義對東亞世界的妖魔化,也正符合薩義德(Edward Said, 1935-2003)所批判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話語。
與此同時,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正面臨亙古未有的思想變局。晚清革命黨為了推翻清朝的統治,開始借用西方的人種劃分,試圖借此區分滿、漢,發起種族革命。如鄒容在《革命軍》中接受了“黃種人”這個西方概念,并進一步將“黃種人”劃分為以漢人為代表的“中國人種”與以滿蒙為代表的“西伯利亞人種”,從而建構“皇漢/夷狄”的種族對立論。革命黨人對滿人的攻擊,固然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卻也將東方主義式的“蒙古人種”觀念引入中國,并將其轉化為對滿蒙民族的污名化。在種族主義與革命浪潮的席卷之下,“蒙古”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幾乎成為“野蠻”與“落后”的代名詞,而“蒙古大夫”的形象也從妙手回春的“神醫”淪為顢頇無能的“庸醫”。如此說來,蒙古大夫的庸醫形象,不僅不是“自古以來”的歷史事實,而無疑是一種“東方主義”的歷史建構。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