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人為何還在使用南市盧灣這些消失的地名
6月7日,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孫瑋、潘霽在“全球城市與地方性知識:網絡力量”討論會上以去年上海靜安閘北兩區合并引發的討論為個案,共同研究了不同群體對于空間意義的理解分歧。
他們發現:“政府與決策專家等主流話語的空間意識主要局限于經濟理性框架,將城市發展視為空間的首要價值。而大眾話語中的空間意義包含歷史、文化、集體記憶、城市認同等更加豐富的內涵。”
“大眾通過自身的話語實踐,努力地把官方話語中偏重經濟屬性的‘空間’轉換成多重意義的‘地方’。”
政府與專家的空間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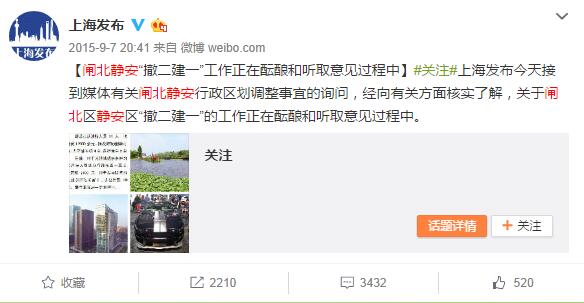
此消息一經發布,當天就有評論數千條,且網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過網絡輿論并未使這一公共決策發生變化,2015年底新靜安區成立。
自“上海發布”發布9月7日的消息后,孫瑋、潘霽便對主流媒體的報道進行分析。他們發現,媒體對“主導城市發展的決策方(政府及專家)如何理解空間意義”的呈現高度一致。以下這則中國青年網的報道頗具代表性:
環上海經濟圈課題組負責人于今認為,此次上海撤區并區,有利于對現有的空間資源進行有效整合,推進核心區均衡發展;有利于提高閘北區的承載能力和服務水平;有利于加強核心區在城市更新中的整體建設和有效保護;有利于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水平,降低行政成本,提升行政效率;有利于推動構建環上海經濟圈,自覺帶動環上海經濟圈同城化和滬江浙一體化發展。
“這五個‘有利于’流傳甚廣,以各種方式在媒介報道中反復出現。”孫瑋說,這類話語呈現的空間意識包括幾個意涵:第一,空間是城市發展的重要資源,尤其是對于城市核心區而言;其二,政府是城市空間的主導者;其三,空間資源的價值主要體現在經濟方面。
聯想2011年黃浦盧灣“撤二建一”,當時政府主要領導者所闡釋的理由幾乎完全一樣。孫瑋認為:“這集中體現了政府及決策咨詢專家代表的主流輿論所認識的空間意義。”
來自民間不同的聲音
為了了解民眾觀點,孫瑋與潘霽還分析了2015年9月7日21點01分至10月16日16點18分中針對“上海發布”消息的3220條評論。這一時間段里的信息討論最為密集。
他們比較意外的發現是,對合并提出不同的看法者中居然有眾多閘北市民。
“如果從現實經濟角度出發,閘北區市民應該是此項政策的高度擁護者,因為預想中的合并會帶來很多現實利益,比如房地產價格上升、靜安區教育、醫療、文化等優質資源的分享。但似乎不合常規情理的是,可以經由合并獲得現實利益的閘北區市民卻高調反對此項政策。”
細看網友的評論,兩位學者發現“人”出現在民間輿論對空間意義的敘事中:空間并非只是一個供城市事務得以施展的物理容器,相反它突出的是人與物理空間承載的社會內涵之間的關聯。
比如評論“閘北的表示不想并入靜安,歷史文脈斷了”。
又比如“盧灣、靜安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她更是一種文化符號”。

“網絡輿論的主要視角不是經濟,而是歷史、文化,以及大眾的城市文化認同。在這些大眾意識中,城市空間的意義絕不僅限于經濟層面。”孫瑋如此總結。
上海具有頑強的“小尺度認同”
孫瑋與潘霽進一步分析,此番靜安閘北兩區合并的社會背景是上海自2000年始在十五年間經歷四次行政區劃調整:南匯、南市、盧灣、閘北漸次消失。
“上海的小尺度認同在民間有著頑強生命力,深深地潛藏于普通市民的意識中。自2000年以來,上海因行政區劃消失的地域仍然存活于市民的記憶中,甚至此次上海發布引發的討論中,被撤銷的南市區、盧灣區仍然被廣泛地提及。”
“這座城市本身是非常特別的。”孫瑋說,經歷了“一市三治”近百年歷史的上海,更讓這座城市擁有極高的異質性。“此次‘撤二建一’所涉的靜安區與閘北區,在百年租界歷史中,分屬英租界與華界。這也是網友在此次網絡公共討論中著力呈現的內容。”

如今的上海市政區
“其實政府與民間都明確地意識到空間對于城市而言極具重要意義與價值。但究竟是何意義與價值,官方與民間存在巨大差異。”在孫瑋、潘霽看來,地方性不僅指經濟利益,也不單是行政機構,更重要的是給予人“家”的感覺。人和地域之間的歷史、文化、情感的聯系,才是空間的主要意義。
同時,“上海城區的小尺度認同,與上海城市認同非但不矛盾,反而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內容,是體現上海城市多樣性的強有力證明。”
空間理解背后的城市認同
當然,中心城區的合并絕非上海城市規劃的孤案。曾有學者指出,近幾年來,中國國內已有數個大城市陸續進行了大手筆改革調整行政區劃,包括北京、天津、重慶、深圳、廈門、沈陽等。
“這顯示著,在急速展開的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空間的價值與意義成為一個核心議題,其重要性持續高漲,由此展開的資源爭奪與意義競爭,也已上升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問題。”孫瑋說,“但在中國現有的城市研究中,相較于城市整體研究,城市群以及城區研究兩個層次較為薄弱。這種狀況已經不能適應當前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大型城市的發展現實。”
孫瑋提及,早在二十世紀初,城市研究者就發現,現代大都市在空間分布上不是均值的,而是呈現一種不平衡的狀態。這種物質空間的狀況,也反映了社會組織形式的基本態勢。城市內部多個地域的存在,也被視為社會多樣性的重要表現,如紐約的曼哈頓、布魯克林、哈林區、東村的并存,構成了紐約城市的多樣性。在美國社會學家莎朗·佐京看來,“就是這種社會多樣性,而不只是建筑物和使用的多樣性,賦予城市靈魂”。
孫瑋與潘霽得出結論,對于空間價值和意義的不同理解正是官民意見不同的主要原因。“城市想象在不同群體間出現了差異、斷裂。這種斷裂常常直接呈現為公共決策中的分歧,而更深層面的議題則是,城市認同、集體記憶、城市文化傳統延續的問題。”
“如果撇開空間元素,單講公共利益平衡并不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政府認為,他們是從大眾利益出發的,城市經濟發展會帶來城市利益的最大化;但普通市民不買賬,因為他們看待城市的著眼點是‘家’的感覺。這并非是說,家的感覺與經濟無涉或者沖突,而是說經濟發展并不足以構成家的感覺,它還需要考量其它因素,如城市歷史與文化傳統、市民的地方認同。”
盡管這次網絡輿論并未在政策層面發揮影響,孫瑋與潘霽認為大眾表達并非毫無意義,它又一次伸張了地方性的價值,喚起了人們的城市記憶,加固了大眾的城市認同。
“它也打破了一些關于全球化與地方性的慣常認知。比如在傳播與全球化的議題中,新媒體經常被指認為是消解地方性的罪魁禍首。這個個案也顯示了與這個常規論斷不同的可能性,那就是,新媒體卻常常是與本土化、在地化的大眾訴求連接在一起的,在這個意義上,相較于傳統主流大眾媒介,新媒體反而顯示了與地方更加緊密的連接。”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