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陳雁丨挑戰成見:中國婦女/性別史的研究革命
文_陳雁(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婦女/性別史進入中國學界已有四十余年,但關于婦女史與性別史的定義仍有諸多爭論。我很喜歡美國歷史學家凱倫·奧芬(Karen Offen)為《牛津世界婦女史百科全書》(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Women in World History)所寫的“婦女史”條目,她在對婦女史進行定義的同時,也說明了性別史是什么以及婦女史與性別史之間的關系。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Women in World History
Bonnie G. Sm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婦女史包括了男性在內的全人類的歷史,但從女性中心的視角處理問題。它突出女性的活動與觀點,宣稱在講述人類故事時,她們的問題、觀點與成就與其兄弟、丈夫和兒子的共同處于中心地位。婦女史把各性別(sexes)或社會性別(gender)之間的社會政治關系置于歷史考察的中心,質疑女性的從屬地位。它檢驗了在一種或多種文化中,女性特質與男性特質建構的密切關系,為其連續性和演變尋找根據。婦女史揭露并遭遇了早先以男性為中心的歷史編纂方式的偏見,質疑為何某些特定的學科與研究主題特別受到偏愛,并提出新的研究問題。時間上,從史前到現在,空間上,從西方到全球,從事婦女史研究的歷史學家極大地擴展了婦女和社會性別的研究范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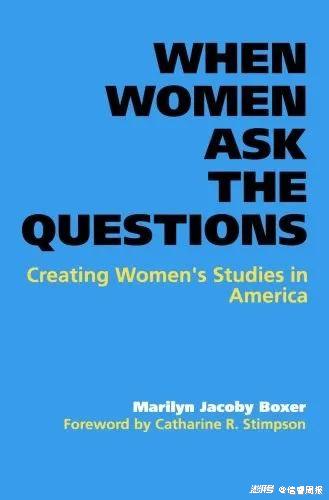
When Women Ask the Questions
Marilyn Jacoby Boxe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婦女/性別史研究不只是把研究對象轉向婦女,而且從女性中心的視角提出新的研究問題,為人類漫長的性別不平等歷史找到原因,開出解方。美國婦女史學家瑪麗琳·J.波克塞(Marilyn J. Boxer)1998年出版的專著,記錄了美國婦女學研究從萌芽到發展的歷程,書名《當婦女提問時》[2]來自詩人艾德麗安·里奇(Adrienne Rich)的詩句——“我們不是別人提出的‘婦女問題’;我們是提問的婦女。”[3]不管是歷史學家波克塞還是詩人里奇,都是從20世紀70年代起就投身美國婦女運動,也是美國婦女研究這一學術領域的創立者之一。在她們或學術或文學的寫作中,都注重婦女的個人體驗和生活經驗。半個世紀前,美國學界的性別生態與今日大相徑庭,當歷史學家關注婦女史,當女性學者基于性別經驗提出新的問題、引入新的視角,當婦女能夠提出問題,而不只是被當作問題來研究時,新的或以往乏人問津的史料受到關注,新的或修正性的研究范式得以提出,婦女/性別史前所未有地挑戰了歷史學的一系列成見,并開墾了大量新的研究領域。本文不是對婦女/性別史研究作整體性的學術回顧,而是對中國史研究領域內婦女/性別史學者已經取得的學術革命的致敬。

1928年,時為北京大學學生的陳東原出版《中國婦女生活史》一書,開啟了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范式——在對傳統中國習俗、制度、規范等方方面面對婦女的壓迫展開論述之后,陳東原提出了“壓迫—解放”這一范式,“我們有史以來的女性,只是被摧殘的女性;我們婦女生活的歷史,只是一部被摧殘的女性的歷史!”陳東原聲稱要“燃著明犀”,照亮壓在婦女頭上的巨石,把婦女從封建的壓迫中解救出來,“然后便知道新生活的趨向了”。[4]這一范式多年后被哥倫比亞大學的高彥頤(Dorothy Ko)教授稱為“五四婦女史觀”,如果傳統婦女不是生活在暗無天日的壓迫之中,那所謂“婦女解放運動”也就無從說起了。而如果沒有解放運動,又從何建構一幅現代的、新中國的藍圖?傳統中國社會只有受害、受壓迫的封建女性,高彥頤認為,這一分析結論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為缺少從女性自身的視角來考察其所身處的世界,從而造成了將標準規范直接等同于歷史發展實際情況的混淆。[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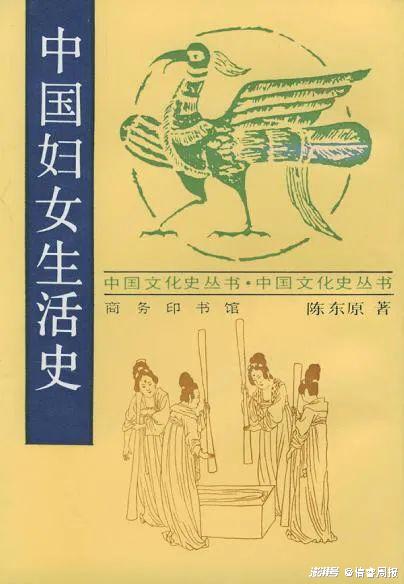
中國婦女生活史
陳東原 / 著
商務印書館1998
其實對“壓迫—解放”范式,中國學者早在20世紀末就已經有過檢討。比如中國婦女史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之一、曾任北京大學婦女學研究中心主任的鄭必俊教授,她在檢索《四庫全書》搜獲千篇宋代婦女墓志銘后發現:女人作為母親在家庭生產、理財和人情交往上都扮演著主導性角色;而在家庭之外,她們還是市井文化的傳播者、創造者和創作源泉。[6]近二十年來,海外學者在這方面也有大量成果涌現。比如,李國彤的著作《女子之不朽》通過大量的文本解讀,讓讀者看到傳統中國女教的發展,絕不僅僅是“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女子無才便是德”這些大而化之的僵化教條所能代表的,即便是男性話語主導的旌表制度、墓志銘等對現實生活中女性角色給予的肯定,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那些被陳東原視為巨石的壓迫婦女、摧殘婦女的規范教條。[7]曼素恩(Susan Mann)教授利用大量女性寫作完成的《張門才女》一書就旗幟鮮明地提問:“張家才女們的生活是被其后的中國改革家們視為愚昧和落后的。但現在傾聽她們的故事時,我們不由要問:20世紀的‘新女性’究竟‘新’在何處?”[8]正是常州張家的女兒們——這些生活在帝國時代的中國婦女,憑著自己的持家能力、文學藝術修養,才使式微的士紳家庭得以生存和發展。這些婦女史家筆下的傳統中國婦女史并不只是一部“被摧殘的女性歷史”。

張門才女
曼素恩 /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
處在新舊轉型期的中國婦女史也遠比我們想象的豐富,近代以來中國本土的女權資源值得好好挖掘與繼承。維新志士金天翮1903年在上海租界以“愛自由者金一”之名出版的《女界鐘》一書,被認為是國人撰寫的第一部關于婦女解放的著作。為紀念《女界鐘》出版100周年,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在2004年舉辦了“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吸引了來自四大洲十個國家與地區的120余位海內外學者,并發表64篇論文。在新中國的話語體系中,中國的婦女解放與女權主義在以往的研究和表述中是被截然分開的,而這次大會成功地搭建了歷史的鏈接,把過去百年間中國婦女事業的發展置于世界女權主義的大背景下來展開討論與重新評價。這次大會的成果對于中國婦女/性別史研究的意義是持續的,大會發表的部分中文論文在復旦大學出版社結集出版,另有8篇論文作為Gender & History(《性別與歷史》)雜志2006年的專號在英國出版。[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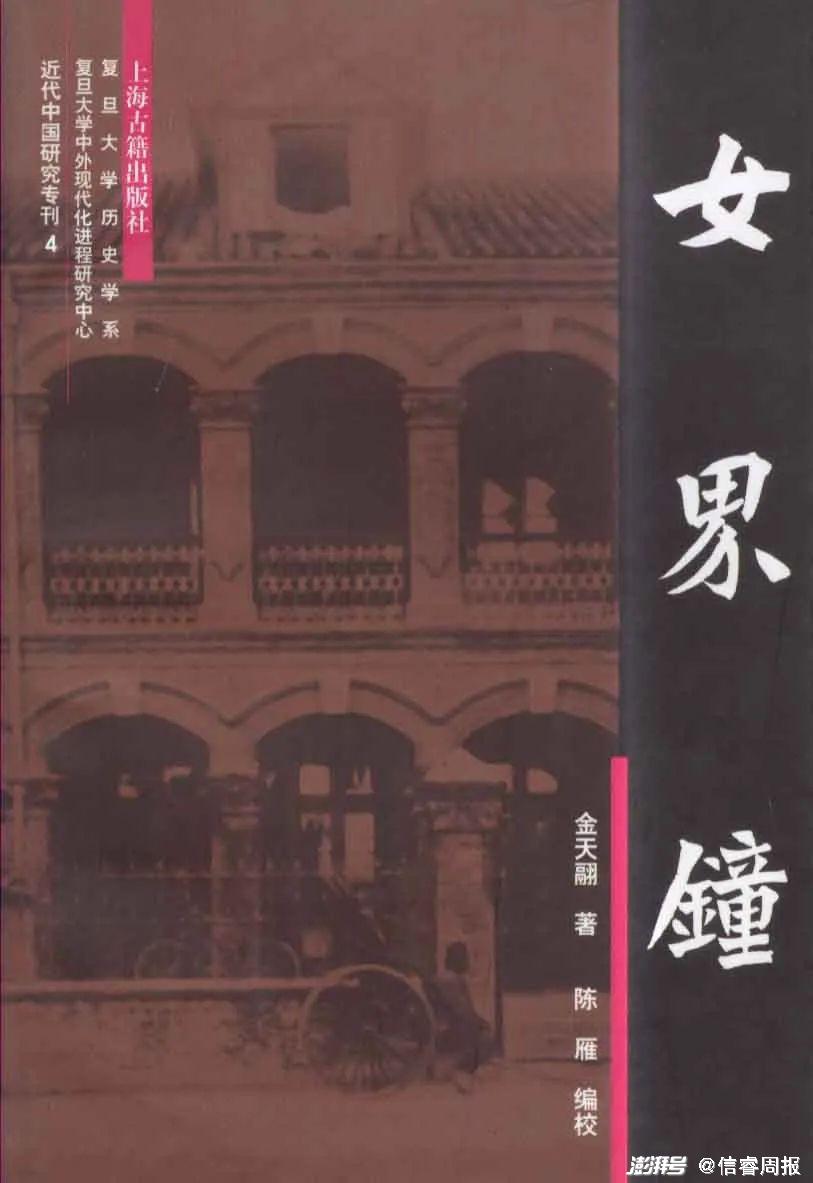
女界鐘
金天翮 / 著
陳雁 / 編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在《女界鐘》發表110周年時,婦女/性別史家又有了鼓舞人心的發現。劉禾、高彥頤和瑞貝卡·卡爾(Rebecca Karl)三位學者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發現了全套的《天義》報,并在讀到何殷震的女權寫作后興奮地合編了《中國女權主義的誕生》一書,指出在五四運動之前中國已有女權主義者明確地剖析了古代中國父權國家在政治、經濟、哲學、社會、學術和家庭體制諸領域的“男女有別”,進而對資本主義國家在民族國家形態、私有制度、社會勞動中的性別歧視提出了富有洞見的批評。要知道,在何殷震寫作的20世紀初,資本主義正被當成世界文明新方向受到中國男性精英的熱烈歡迎。何殷震提出的分析方法對于當今跨國女權主義的理論建設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10]
中國人民大學的宋少鵬教授沿著這條研究道路完成的《“西洋鏡”里的中國與婦女——文明的性別標準和晚清女權論述》一書,再次肯定了何殷震“女界革命”理論的重要性,在無政府主義的框架下,何殷震的女權思想明顯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婦女解放思想的影響,超越了西方殖民主義的“文明論”,提出了“男女間革命”的方向。當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受限于政經體制而陷入瓶頸時,以何殷震為代表的中國女權先驅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為我們指出了新的方向,誠如宋少鵬所言,“無政府主義女權以及與這條脈絡密切相關的馬克思主義女權開啟了對另類現代性的探索”[11]。

女權活動或女權主義學術在中國的發生、發展當然深受西方的影響,但正如上述幾項研究對中國自發的女權主義思想的發現與肯定,值得被重新發現和再研究的還有來自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女權資源。
將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socialist state feminism)這一研究范式率先用于中國現代史研究的,當推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王政教授。早在2005年發表于Feminist Studies(《女權主義研究》)雜志的“State Feminism”? Gen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國家女權主義”?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性別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形成》)一文中,王政就將原本用于研究北歐國家性別平等事業的“國家女權主義”范式挪用來討論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內的女權努力。[12]
在2017年出版的《在國家中尋找婦女》(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64)一書中,王政說明了為何要將這些拒絕被稱為“女權主義者”的中共干部命名為“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第一,是為了指出他們對五四運動以來男女平等觀的堅守;第二,是要強調他們以婦女的“徹底”解放和為婦女“群眾”服務為目標;第三,強調他們在黨內或政府中的位置,是為了聚焦他們的女權奮斗是如何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改造,如何富有成效地促進了千千萬萬中國婦女的社會進步。王政對20世紀50年代城市的“婦代會”、全國婦聯、中共文藝實踐等的研究,將五四運動以來的女權實踐與1949年以后的婦女工作有機聯系起來,認為中共黨內以鄧穎超、蔡暢等人為代表的女權力量,巧妙地利用了體制內的資源,致力于解決性別和階級的等級問題,并通過婦女組織發展有力地改造了男權文化。[13]
與王政主要關注城市和精英階層不同,美國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賀蕭(Gail Hershatter) 教授的著作《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是在陜西農村進行了長達10年的田野研究,與合作者高小賢共同完成了對72位農村婦女的訪談后寫成的。農村+婦女,使這一數量巨大的研究對象成為共和國歷史上雙重邊緣的群體,而衡量社會主義革命與婦女解放之間的關系,農村婦女又是非常重要的變量。依托口述完成的研究,呈現了以往的共和國史研究全然不關注的農村婦女的農事、家務、婚姻、分娩、育兒、道德觀念等,展示了在基層農村黨和國家的政策如何影響(或者不影響)婦女生活的方方面面。顯然,賀蕭的研究早已超越了20世紀七八十代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婦女史時常常追問的“黨和國家的政策對婦女是好還是壞”等問題,她讓我們意識到,如果我們不關注性別,就無法理解中國革命;但性別絕不是簡單的個人問題,應該將性別放到一系列的權力關系中去理解。[14]
近些年來,國內學者對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在婦女運動、婦女解放和婦女工作上積累的經驗展開歷史性研究的努力,亦取得了不少成果。上海師范大學董麗敏教授擅長通過將近代以來豐富的文學素材與歷史實踐相結合展開分析,2016年、2017年她在《婦女研究論叢》發表了兩篇討論“延安經驗”的論文,提出“家庭統一戰線”的概念,并以延安時期的婦女紡織生產運動為例,肯定了當時婦女解放路徑的有效性。中共在陜甘寧邊區探索出的“家庭統一戰線”模式有效地將性別與階級議題相結合,集體合作生產模式一直延續到1949年以后,正是在“新婦女”建構的過程中,也正因為“新婦女”的參與,“新社會”才得以成立。[15]
北京大學的賀桂梅教授則從“人民文藝”出發,通過《白毛女》《小二黑結婚》《劉巧兒》等我們熟悉的社會主義文藝作品,來總結社會主義婚姻家庭敘事與婦女解放的歷史經驗。她特別強調中國婦女解放理論與西方當代女權主義理論的差異性與綜合性,從多重交互的社會生產關系和社會性別制度出發,討論女性群體的獨特性,提出要重新理解人民政治實踐從內部改造婚姻家庭制度的婦女解放路徑。[16]從性別視角發掘這些“中國經驗”正是對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寶貴資源的繼承。與賀蕭一樣,這些國內學者也主動地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歐美學者提出的“未完成的革命”論進行對話,指出西方理論在解釋中國革命和婦女解放現實之間的不洽。首都師范大學的秦方教授在總結過去五年中國婦女史的知識路徑后認為,“中國革命歷程中的婦女解放并不是一個未完成的、延遲甚或是失敗的過程,而恰恰是一個通過摸索和探討,能夠形成有效的、切合實際的婦女動員和解放的模式(盡管也存在很多的挑戰),這一模式反過來亦促成了中國革命的極大發展”。[17]所以,當我們從婦女/性別史的視角來考察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及其演變時,新的解釋框架誕生了,女性活動的譜系得以重建。
王政在對全國婦聯的研究中提出了“隱埋的政治”(politics of concealment)這一概念,認為上自鄧穎超、蔡暢,下到基層婦聯干部,共和國的婦女干部都甘當幕后英雄,擅長在黨的中心工作名義下推動婦女工作、提高婦女權益。《婚姻法》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頒布的第一部法律、男女同工同酬的迅速實現、社會主義勞保制度下56天產假的實行等都證明了“隱埋的政治”的成功,但也正因此,這一代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者的努力在共和國歷史中是隱形的。
今天繼續這一策略是否仍能成功十分可疑。美國紐約大學的朱迪思·斯泰西(Judith Stacey)教授在1983年出版的《父權制與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一書中認為,中國革命對父權制的挑戰是極其有限的,但十多年后在對中國家庭與革命的關系進行再研究之后,她提出,“如果女權主義者想要成功地推動這場革命,就必須把‘后現代’社會中的革命轉型放在中心位置,女權主義要在一開始就處于中心位置,成為半自發的力量。這種女權主義立場表面上看有種戰斗性,但也具有反諷意義的效果:它證明了經典馬克思主義關于革命的一些中心論斷是有效的。它認同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是之前資本主義未能實現的承諾——在這場革命中,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富足應該從少數特權人的手中轉移,變成所有人的權力”[18]。今天的婦女/性別史研究,除了要深入發掘中國女權思想與實踐的寶貴資源,還必須同時關注女權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對造成歧視、形成不平等權力關系的社會制度進行全面的、歷史的檢視。

2000年,曼素恩教授為《美國歷史評論雜志》(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組織了一個中國男性史研究專題,并撰寫導讀《中國歷史與文化中的男性紐帶》(The Male Bon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她指出,中國的性別史研究需要大力發展男性史,并認為以下原因阻礙了這一領域的發展:首先是中國史學界有待發展“性”的歷史研究;其次是中國學者對男性研究和男性歷史研究的價值認識不足;第三是對婦女史的強烈興趣反而造成了對男性歷史的忽視,過度地關注父權制和男性支配的問題,其后果就是使得“性別史=婦女史”。在曼素恩發出這些批評之聲的21年后,中國史學界中的這些現象仍然沒有得到本質的改變。沉迷于婦女史研究的學者往往很容易將男人視作鐵板一塊,但實際上不論是男人身份還是女人身份都是歷史形成的,我們不能把男人身份當成與生俱來的本質——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就犯過這樣的錯誤,男人身份、男性特質都是持續變化的。在歷史變化的過程中,男人因為擁有雄性的身體而爭取到了某種至今無法摧毀的權威,但這種權威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任何一種文化中又是由各種彼此矛盾的觀念構成的。今天對這些構成男人身份/男性特質的過程、觀念進行具體而深入的研究,對于我們解構父權制的性別文化、拓展性別史研究的領域,都具有深刻的意義。要在這一領域有更多的突破,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這也是曼素恩曾經提醒過的:中國的歷史學家要注意發展對性研究(sexuality studies)持續的興趣,性研究也是歐洲和北美男人歷史和男性特質研究的起點。
目前史學界最熱門的概念非“全球史”莫屬,婦女/性別史研究者能為構建全球史做些什么呢?當我們跳出民族國家的窠臼,以“全球史”的規模來寫作婦女的歷史時,可以關注哪些問題呢?以我熟悉的近代歷史為例,女權觀念的跨國流動(中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女性的全球旅行(來華的女傳教士、到歐美日去留學的亞洲女性、跟隨父兄在美洲打拼的女性華僑等)、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婦女,都會是重要的研究課題。近代以來,女權運動本身就是一個全球化的過程,在全球史的視野下展開婦女/性別史研究,對這一領域的意義不言而喻。
婦女/性別史研究者倡導研究視野下移,不只關注精英階層,女工、農婦、家庭主婦、性工作者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對象,并且已經取得了出色的成果。我在此想強調的是另一種視野下移,那就是要讓這些挑戰歷史成見的婦女/性別史研究成果進入中小學的歷史教科書,在各種層次的考試中納入與婦女/性別史相關的內容,培訓和賦權歷史老師,將學術成果改寫為普及讀物,用這些挑戰性別成見的研究成果來激勵年輕一輩的思想與生活,這樣才有可能改變以男性為中心的歷史觀與歷史寫作習慣。
當婦女不再只是問題而是提問者,當歷史寫作將婦女的問題、觀點與成就和她們父親、兄弟、丈夫、兒子的一視同仁,當性或性別相關的社會政治關系被置于歷史考察的中心,當婦女的體驗和敘述——哪怕只是農村婦女的口述,成為歷史的核心組成部分,長期以來以男性為中心的歷史編纂方式所帶來的成見就會受到有力挑戰,婦女/性別史領域就一定會成為知識生產的熱點與增長點。
注 釋
[1] “History of Women”,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Women in World History, ed. Bonnie G. Smith. 4 vol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B O X E R M J. W h e n Women Ask the Questions: Creating Women's Studies in America[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該書的中文版《當婦女提問時》由余寧平、占盛利等翻譯,于2006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3] RICH A. Blood, Bread, and Poetry: Selected Prose[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6.
[4] 陳東原. 中國婦女生活史[M].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8: 18-20.
[5] 高彥頤. 閨塾師[M]. 李志生, 譯.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5: 2-5.
[6] 鄭必俊. 兩宋官紳家族婦女—千篇宋代婦女墓志銘研究[M]//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國學研究·第六卷,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117-140; 鄭必俊. 宋代婦女與市井文化[M]// 李小江, 等. 主流與邊緣.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9: 222—237.
[7] 李國彤. 女子之不朽:明清時期的女教觀念[M]. 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4.
[8] 曼素恩. 張門才女[M]. 羅曉翔, 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 8.[9] 王政、陳雁. 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M].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4; Ko D, WANG Z. Translating Feminism in China, A Special Issue of Gender and History[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該專號由陳雁組織翻譯并于2016年在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文書名為《女權主義在中國的翻譯歷程》。
[10] LIU H, KARL R E, KO D. The B irth of Ch inese F e m i n i s m [ M ]. N e w Y o r 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三位教授為該書合寫的導言已譯成中文發表, 參見: 劉禾, 瑞貝卡·卡爾, 高彥頤. 一個現代思想的先聲: 論何殷震對跨國女權主義理論的貢獻[J].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14(5)。
[11] 宋少鵬. “西洋鏡”里的中國與婦女—文明的性別標準和晚清女權論述[M].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
[12] Wang Zheng. "State F e m i n i s m" ? G e n d e r a n 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 Feminist Studies[J]. 2005, 31(3): 519-551.
[13] Wang Zheng. Finding W o m e n i n t h e S t a t e : A S o c i a l i s t F e m i n i s 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M]. Berkeley: UC Press, 2017.
[14] 賀蕭. 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5] 董麗敏. 延安經驗:從“婦女主義”到“家庭統一戰線”—兼論革命中國婦女解放理論的生成問題 [J ]. 婦女研究論叢, 2016(6); 董麗敏. 組織起來:“新婦女”與“新社會”構建—以延安時期的婦女紡織生產運動為中心的考察[J]. 婦女研究論叢, 2017(6).
[16] 賀桂梅. 人民文藝的“歷史多質性”與女性形象敘事:重讀《白毛女》 [J]. 文藝理論與批評, 2020(1); 賀桂梅. 人民文藝中的婚姻家庭敘事與婦女解放的歷史經驗[J]. 婦女研究論叢, 2020(3).
[17] 秦方. 在歷史與性別之間—大陸地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的知識史路徑 [J]. 婦女研究論叢, 2020(11). 相關的研究成果還可以關注《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集刊第8輯“婦女專刊”,該輯由宋少鵬主編,收錄的10篇論文集中討論了過去百年中國婦女解放的議題,尤其關注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婦女解放之間的關系。
[18] 朱迪思·斯泰西. 尋找關于家庭與革命的新理論: 思考中國案例[M]// 馮芃芃, 等譯. 社會性別與社會讀本,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2010: 45-56; 她關于家庭研究的成果還可以關注Judith Stacey. In the Name of the Family: Rethinking Family Values in the Postmodern Age[M]. Boston: Beacon Press, 1997.
(原載于《信睿周報》第54期)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