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對談︱我們的閱讀趣味正在不自覺地受到性別文化的塑造
【編者按】
5月22日下午,南京萬象書坊舉辦了一場題為“英語文學史中的性別角力——《如何抑止女性寫作》”的對談,與談人分別為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徐蕾、但漢松和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劉慧寧。澎湃新聞經主辦方授權刊發對談錄音整理稿。因內容過長,便分上下兩篇摘發,此為下篇。
講座現場(點擊圖片可查看對談上篇)
劉慧寧:拉斯在《成就個別化》這一章提到,這種現象會讓女作家的二流作品被當成她最好的作品,由此一些女作家的優秀作品以及一些作品較少的優秀女作家就被忽略了。比如說她尤其推崇夏洛蒂·勃朗特的《維萊特》《雪莉》《教師》、艾米莉·勃朗特的“貢代爾詩”、瑪麗·雪萊的《最后一個人》、奧斯丁少年時代的作品。不知道兩位老師是否讀過這些作品?如果讀過的話是否認同她的“翻案”?
徐蕾:的確,在英國文學史上,即便是受到關注的那些作家,包括夏洛蒂·勃朗特、伍爾夫等大作家,她們被關注的作品都只集中在幾部。伍爾夫的情況可能好一些,大家會讀她的《達洛維夫人》《到燈塔去》,甚至《海浪》《雅各布的房間》,那么像《一間自己的房間》已經成為女性文學的經典了。但是反觀夏洛蒂·勃朗特,《簡·愛》好像就是大家唯一能想到的她的作品,而實際上勃朗特的作品不僅有《簡·愛》,還有剛才劉編輯提到的《維萊特》《雪莉》《教師》等三部小說。我覺得,這三部小說遭到忽略也是有原因的。
我認同拉斯的這個觀點,作為夏洛蒂·勃朗特的成名作,《簡·愛》其實不是她最優秀的作品,畢竟這是她發表的第一部作品——嚴格意義來說,其實也不是她的第一部作品:她的第一個作品是《教師》(The Professor),然后當時出版社收到了她和她兩個妹妹的稿件之后,發現她兩個妹妹的作品,也就是《呼嘯山莊》(Wuthering Heights)和《阿格尼絲·格雷》(Agnes Grey)好像更好一些,所以就接受了后兩人的投稿,而拒絕了夏洛蒂·勃朗特的《教師》。作為姐姐,夏洛蒂內心上是有些焦灼的,她感到了一種壓力,所以在短短幾個月內就寫出了《簡·愛》這部小說,結果一下子就得到了編輯的認可。所以到最后,她的這部作品比她兩個妹妹更早一步出版。這當然是后話。《簡·愛》確實一下子就走紅了,可是在背后我們看到的是,她花在這部作品上的時間并沒有那么多,小說是在看到妹妹的成就得到認可這一應激之下的倉促之作。所以她的最后一部作品,發表于1853年的《維萊特》(Villette)——Villette在法語中的意思是“小鎮”,這個小鎮就是指布魯塞爾,比利時的首都——在很多評論家一致看來,是夏洛蒂·勃朗特的巔峰之作,她最成熟的作品。然而這部作品沒有能夠被大眾所認識,我想一方面誠如但老師所說,我們的文學史的線索已經非常緊湊了,有很多鴻篇巨制,再塞進來一部,讀者也很難立刻接受,況且《維萊特》的篇幅可能比《簡·愛》還長,小說人物的復雜關系遠遠超過了《簡·愛》里相對單一的線索。
但是為什么在拉斯以及眾多女性評論者看來,《維萊特》是更加成熟的作品呢?我想跟這部小說的情節設計有很大的關系,那就是說作者沒有給這個故事一個完滿的結局。同學們可能會說:難道沒有完美的結局,就是一個更成熟的或者說更有藝術品味的作品嗎?也不盡然,這不是唯一的標準,但它至少反映了《簡·愛》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已經不再把大團圓結局看作唯一的、可以給予女性的一種自我救贖之路。為什么這么說?因為這個小說更加緊密地結合了夏洛蒂·勃朗特年輕時到布魯塞爾求學的個人經歷,包括她在求學期間同一位法語教師的情感糾葛。當然在現實生活中,那位法語老師可能也已經有了家室,兩個人不可能違背公序良俗,所以夏洛蒂就只好回國,內心也非常痛苦、壓抑。那么在夏洛蒂·勃朗特最后的歲月里,她把她所有的精力都奉獻給了這本小說,所以這部小說可能更多地凝聚了她個人的情感經歷和她內心的一種折射。
《維萊特》很有意思,在很多情節上蠻像《簡·愛》的:也是講了一個6歲的孤女,從小到一個有錢人家去寄養,在寄養過程當中也遇到了很多好心人或者沒那么好的人,隨后在遠方親戚的資助下去布魯塞爾求學,學習法語,并在求學過程當中遇到了一個比她年齡大的法語老師,這個老師脾氣暴躁,相貌丑陋,跟這個女主人公露西·斯諾一樣,二人都是相貌平平平——可以注意到,夏洛蒂·勃朗特不喜歡她的女主人公光彩奪目,而是一向以一種非常樸實、接地氣的面貌示人,夏洛蒂·勃朗特本身也不是美女,她的主人公也不是什么美人,所以這部小說依然延續了以相貌平凡的女性為主角的傳統——在此期間,他們兩人在宗教意見上有些不合,男主人公叫保羅·伊曼紐爾,是一個天主教徒,他希望露西皈依他的宗教,而露西·斯諾不愿意,兩人之間產生了誤解,但在最后又達成了共識,準備重修舊好,要在布魯塞爾相聚。可就在這個當口,一場大的暴風雪把伊曼紐爾困在了途中,而他到底是死是活,小說沒有給我們一個非常清晰的回答;但是也在這兒,我們看到了露西作為一個獨立的女性,最終在周圍親朋的資助下,開辦了一所學校,為那些來自普通家庭的女孩子提供良好的寄宿制教育,實現了她的人生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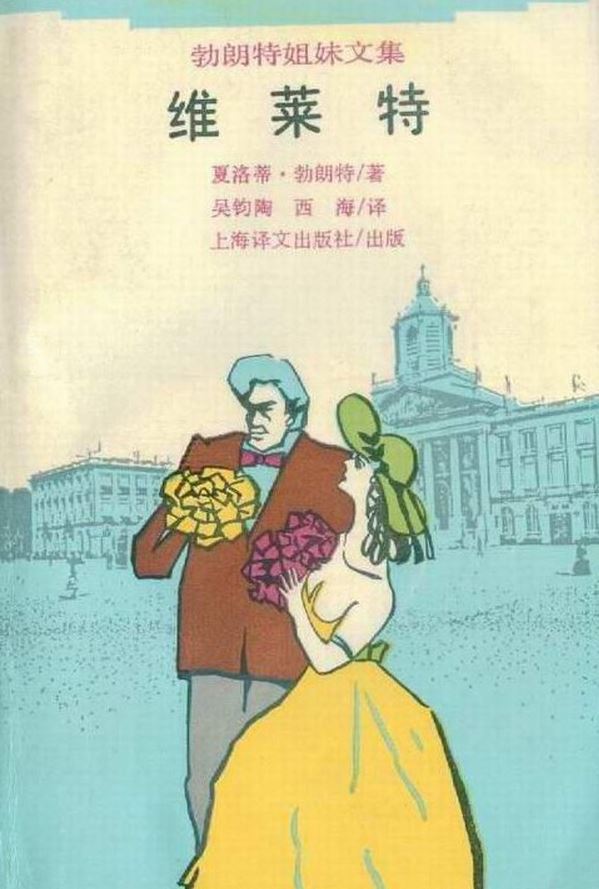
《維萊特》
所以在這種人生發展軌跡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沒有一個男性的拯救者,比如羅切斯特先生,來讓露西·斯諾的人生達到至善至美,女性仍然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構建自己的理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想《維萊特》應該是比夏洛蒂·勃朗特的早期作品《簡·愛》更加成熟、更加有藝術魅力的。
但是說實在話,這部小說你們若要讀的話需要有耐心,因為它分三部,只有到了第三部才進入故事的主線,進入露西·斯諾和這位法語教授之間的非常復雜揪心的戀愛關系,前兩部都是在講述她從6歲的小姑娘到少女成熟期的漫長線索,故事的進展比較龐雜。所以在情節設置上,我個人覺得《維萊特》可能不如《簡·愛》那么集中,那么有感染力,因為《簡·愛》的節奏發展非常快,而且我們知道故事一定是奔著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結婚——不斷地往前滾動的;但你在看《維萊特》的時候,你的內心是不安的,因為你看到《維萊特》的世界沒有那么多規律可循,沒有“灰姑娘等待白馬王子出現”的模式可依循,所以在這個時候你的內心是隨著露西的成長而不斷上下起伏的。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它超越了夏洛蒂·勃朗特的舊作《簡·愛》,所以如果同學們感興趣,對夏洛蒂·勃朗特想要有更多了解的話,我強烈推薦大家去看一看小說的中譯本,《維萊特》在1980年代就已經被翻譯成中文了,譯文還是很可靠的。
但漢松:很佩服徐老師,剛才講了這么多,其實慧寧就是問我們看沒看過《維萊特》。要我說就是我沒看過。常常有這樣一種誤解:你是學英語的,你是教文學的,那這個書你肯定看過;別人這么問的時候我很尷尬,所以后來我就臉皮厚,說我真的沒看過,因為你沒有時間去看所有值得看的書,你的生命其實是非常短暫的,你選擇一些書就要排除其他的書。
說到這個地方,我想把話題稍微延展一下:為什么《維萊特》沒有成為一部像《簡·愛》那樣著名的小說?真的是因為男權的、父系的或者是性別的因素和偏見在作祟嗎?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為什么這么講?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座的這些讀者們,你們知道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最好的小說是哪部?他最好的小說是他的晚期作品《金缽記》(The Golden Bowl)、《鴿翼》(The Wings of the Dove)等等,這些被批評家看作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但是你知道亨利·詹姆斯被閱讀最多的小說是什么?是《黛西·米勒》(Daisy Miller),是《一位女士的畫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是他早期寫的那些更加簡單、更加具有可讀性的作品。這個事兒你上哪說理去?亨利·詹姆斯本人對此也很不滿意,他認為我剛開始寫作就寫了《一位女士的畫像》,這只是我小試牛刀,稍微屈尊地迎合一下你們普通讀者,結果我后來真的用心寫的作品怎么沒多少人看?所以讀者的趣味很多時候具有非常復雜的成因。
《簡·愛》這個故事,它的流行有其必然因素,它里面有一個女性,她在尋找自己的靈魂,尋找自己的伴侶,尋找自己的實現,如此動人的一個故事,當然有很多女性能在里面找到共鳴。我記得在我小時候,譯制片頻道有一個非常經典的場景:簡·愛向跟羅切斯特先生吃醋,然后又告白,她說你憑什么這樣說我?你不要以為我丑,長得不好看,我就怎么樣。我告訴你,我跟你是平等的,我們死的時候,我們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我也可以愛你,我們的靈魂是平等的——很多女性,尤其是那些情竇初開的女性,看到這樣的句子是會淚流滿面的。小說之所以能恒久流傳,其實是因為當女性的人生、靈魂置于其中時,它變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引。
另外還有一方面,大家可能平時不會注意到,就是一本小說的永恒性,除了普通讀者對它的熱愛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學術界如何去評價它。學術界為什么會認為《簡·愛》比《維萊特》更值得評價呢?因為學術界的標準不是說這本書寫得好不好或者你覺得好不好,而是這本書有沒有可以評論的角度,有沒有可批評性。那有同學可能會好奇了:簡·愛最后又跑到羅切斯特那里,小三轉正了,這明擺著是一個大團圓的結局不是嗎?并不是這樣的。《簡·愛》這本書在后殖民文學批評當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像薩義德、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這樣的后殖民理論家,在《簡·愛》這樣的英國文學經典當中通過一種對位閱讀,發現了夏洛蒂·勃朗特的偏見。這個偏見是什么呢?就是將一個來自第三世界、來自海外殖民地的一個女性當作自己的敵人,她的靈魂的尋找、她同羅切斯特先生的愛的結合,是以犧牲那個閣樓上的瘋女人為代價的,那個瘋女人是一個絆腳石,所以最后她放火自焚了。這樣一種與文化、帝國主義共謀的特點,引發很多后殖民理論家的思考。另外還有一部,它的前傳叫《藻海無邊》(Wide Sargasso Sea),也非常有影響力。斯皮瓦克就是研究女性文學的,從《簡·愛》到《藻海無邊》再到《科學怪人》,她寫了一篇非常經典的論文,叫《三位女作家的文本和一種對帝國主義的批評》[校者注: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Critical Inquiry, 12:1 (Autumn 1985), 235-61],我也讓我的研究生在課堂上去讀和討論。這些就是前后接力的一些學術探討。包括像《文學事件》里面也有一章是專門研究《簡·愛》的。所以《簡·愛》的這種豐富的闡釋性、議題性決定了它會一直留在文學批評的中心地帶,這并不是因為教授們覺得它寫得多好,而是說它能反映出一些非常深刻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兩方面,就決定了拉斯所不滿的那種現象。你們為什么不讀《維萊特》,你們為什么就只讀《簡·愛》,你就以為她只有這一部作品嗎——很多東西不能完全歸結于男性的偏見。
徐蕾:我補充一句,但老師剛才的意思好像是,它之所以不太被學界重視,是因為相比起《簡·愛》,它可能不太適合被后來的后殖民理論、新的文化理論所接納,成為一個新的闡釋的坐標。但是我們僅僅就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研究來講,如果評論家要去分析夏洛蒂·勃朗特的話,那么除了《簡·愛》,《維萊特》是他們一定會去研究的一部小說。語境不同,每一個文本的重要性或許也會不同。所以在這點上我的意見稍有不同。
劉慧寧:這個讓我突然想到之前有讀到說,安吉拉·卡特死前正在構思一部《簡·愛》的續篇,非常遺憾的是,她后來得癌癥去世了,沒有完成這個作品。如果她能寫出來,我真的是很想看的。
徐蕾:《簡·愛》有續篇。2000年英國作家D.M.托馬斯寫的《夏洛特:簡·愛的最后旅程》(Charlotte:the Final Journey of Jane Eyre),被認為是《簡·愛》的續篇。《簡·愛》有點像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化符號,但當你走進這個文化內部的時候,你可能會被琳瑯滿目的作品所進一步吸引;而《維萊特》是在你走進維多利亞時代以后可以打開的第二本書。這兩個作品之間其實不需要角力,但我認為在不同的坐標系里,它們的重要性有不同的呈現。
劉慧寧:那像這類不太知名的優秀女性作品,老師們還有什么想推薦的嗎?
徐蕾:“不太知名”是指歷史上被淹沒了的?
劉慧寧:對,就是想特別推薦給大眾讀者的。
徐蕾:同學們可以讀讀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的小說,她算是哥特小說的一個先鋒。她有一本書叫作《尤道夫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Udolpho)。如果你們對哥特小說、對古堡、對美麗善良的女性如何落入陷阱又如何遇到了拯救她的力量——不管是來自男性還是自我力量——感興趣的話,我個人覺得可以去看一看,小說本身也不是很長。而且我想指出的是,其實這種所謂的哥特小說的傳統,到了當代,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的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這就回到拉斯,還有包括美國著名的女科幻小說家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Le Guin),她們都是寫科幻小說的重要女作家。我覺得這個傳統其實是可以追溯到18世紀晚期的哥特小說傳統的,如果你們希望更了解這個傳統的話,就可以看看《尤道夫的秘密》。
另外還有一本書我覺得也可以推薦給大家,就是《如何抑止女性寫作》里提到的,人們會對女性擅長的某一種類型小說進行壓抑,即“sensation novel”,我們可以翻譯成“奇情小說”。它興起于19世紀70年代,有點像我們現在的丑聞小說,比如說大家族里面,有一些奇怪的、混亂的兩性關系,或是某一個人物身上背負著罪孽的過去。奇情小說非常重要的一位鼻祖叫布拉頓(Mary Elizabeth Braddon),她有一本書叫《奧德利夫人的秘密》 (Lady Audley's Secrets),這本書有電影改編版,非常地過癮。奇情小說在現在有新的延續,就是所謂的“新維多利亞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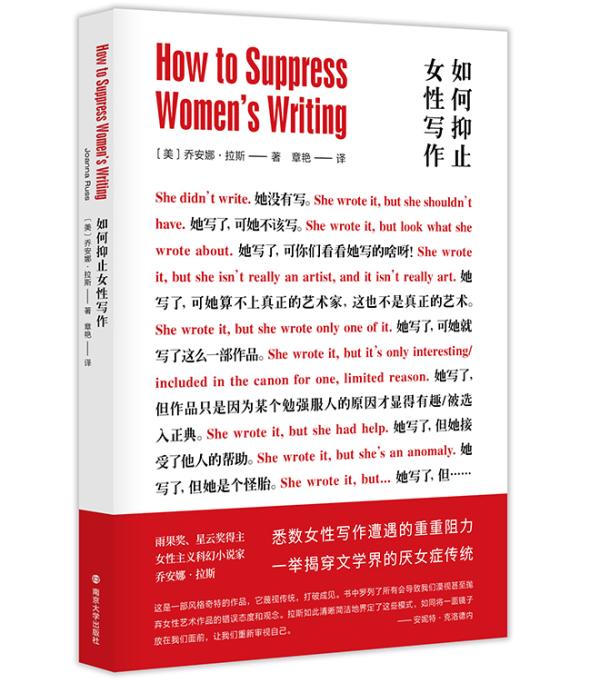
《如何抑止女性寫作》
那些被壓抑的所謂類型文學,包括哥特小說、奇情小說等等,到了當代,其實都在以不同的面貌重新浮現出來,而且在女性作家的這種接力當中,不斷地更新、發展。這兩本書可能都有點古舊,一個是18世紀晚期,一個是19世紀晚期的,大家如果感興趣可以找來看看,都有中譯本和電影改編版,還是比較接地氣的。
但漢松:我現在還處于女性文學正典的補課過程中,所以沒有精力再去讀那些遺珠了。不過我最近的女性文學閱讀中,我發現很多20世紀的經典作家,其實現在國內引進的還不太多,或者說國內的那些書評人談得還不太多,不經常上報——我們不要只去看那些報刊文章的推薦書,或者是哪個著名知識分子推薦的今年必讀書,他推薦然后你就去跟風,其實不必如此——這里面其實有巨大的寶藏可以去挖掘。我自己就認為像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艾麗絲·門羅(Alice Monroe)、尤多拉·韋爾蒂(Eudora Welty)這些作家已經跟我長相廝守了。我在學生時代還特別迷戀一個作家,就是加拿大的瑪格麗特·勞倫斯(Margaret Laurence),她的作品在當時都是暢銷書,但是國內已沒有人再去翻譯、談論它,可是勞倫斯當年就像阿瑟·黑利(Arthur Hailey)一樣,是重要的暢銷書作家。所以可以讀的女作家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大家要有一張自己的文學閱讀地圖,因為并不是每一個時代的每一個好作家你都有精力去追蹤她,你的生命畢竟是短暫的。
劉慧寧:下面一個問題還是關于推薦作品的:伍爾夫曾說,偉大的靈魂是雌雄同體的。而我們之前在北京的一場對談里,北師大的張莉老師提到世界級的作家是可以易形易性的,女性主義文學不應以作家的性別去定義,男女不是二元對立的。那么在兩位老師看來,英語文學史上有哪些男性作家的作品是易性的?
徐蕾:這個問題挺有意思的。說“易性”指的是可以變換性別,男作家可以寫一個女性的聲音,其實拉斯是非常反對這種說法的,也有不少女性作家對伍爾夫的這個觀點持不同意見。但是拋開這些學術界的爭論,你講的意思我大概能夠理解,就是某個男作家寫出來的東西讓你讀起來有一種親切感,感覺不到隔膜,不是一個男性強行把自己變成一個女性。
我個人感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就是一個比較擅于易性的作家。我很喜歡他。剛才但老師提到的《金缽記》(The Golden Bowl)和《鴿翼》(The Wings of the Dove),都是兩部非常出色的小說。但是看他的小說要有足夠的耐心,因為他的句法比較復雜,行文極其繁復,而且他在講述男女關系的時候所用的隱筆是需要你細細體味的。也正因為如此,你能感覺到這是一個對于細節,對于人和人的關系,不僅僅是兩性關系,洞察入微的一個作家。在這一點上,我個人覺得亨利·詹姆斯是一個讓你在閱讀的時候,你不太清楚或在意他的性別的一個作家,他的作品里沒有強烈的作家存在感——比如告訴你事情是怎么回事,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或者對這些事件的未來走向做出預判——他深深地隱藏在他的行文當中,甚至當你覺得需要把他給使勁拽出來的時候,你都不知道從哪入手。他的文字就是如此綿密,讓你感覺到這是一個化于無形的高超的故事講述者。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他算是易性的作家。
然后還有一個作家,當代的愛爾蘭作家,科爾姆·托賓(Colm Toibin),被譽為當代的亨利·詹姆斯。你們去看他寫的《大師》(The Master),它就是仿寫了詹姆斯的寫作方法,講述了詹姆斯的情感故事。如果你們想看他寫女性的話,那么可能《布魯克林》(Brooklyn)值得看一看。這兩個作家是我想到比較有說服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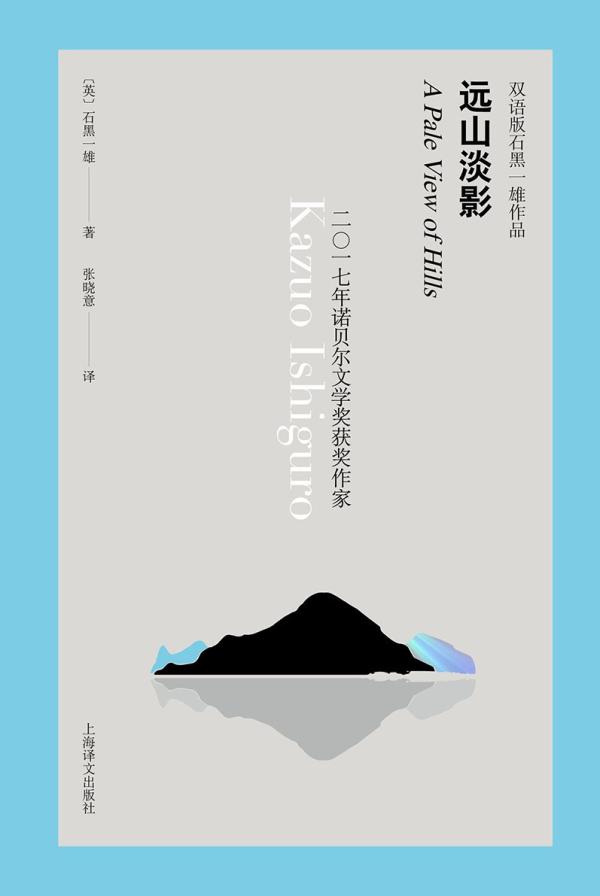
《遠山淡影》
還有就是石黑一雄。順便說一句,石黑一雄是對我們中國人來講特別有親近感的一位作家,尤其你看了英文的原文,那種文字表達之洗練,畫面之清晰,情感描摹之細膩,我覺得在男性作家當中是很難找到的。有些作家也很善于模仿女性的口吻,但是你能感覺到是模仿出來的。可是你們看石黑一雄的第一部作品,《遠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那他對女主人公那種回憶口吻的模仿——都不能說是“模仿”了,你覺得他就是一個女作家,你覺得那個聲音就來自他靈魂的深處,他在跟他自己溝通,在進行一種自我的救贖。你們看了就會理解了。他的敘事其實是一種通過講話來治愈內心創傷的方式,而那樣的一個聲音居然是一位年輕的日裔英國作家講出來的,我感到非常非常震驚。雖然這本沒有《長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那么有名,但作為處女作來講,他的寫作功底可見一斑,強烈推薦。
但漢松:剛才你說的那幾個都是我想說的。那我再稍稍講一個。
我比較贊同徐蕾老師的一個觀點,就是拉斯在這本書中和伍爾夫的對立,其實本質上就是說,該不該將女性的特質進行本質化的提煉。我們強調女性文學,有兩個方向:一個方向就是將女性的特質放到一個神龕里,或者把它用一個玻璃罩罩起來,甚至將它神話化——“那就是最女性的最真實的女性的東西”;另外一個方向就是像一些女性主義者說的那樣,應該去消除這個差異,而不是去堅守或推崇這種性別差異。
相對來說,我可能更贊同伍爾夫,我認為雌雄同體可能會是一種更好的寫作狀態。我比較反感那種“老白男式”的寫作,里面完全是男人的聲音,男性的意識。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還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也寫不好女人。這些都是飽受批評的。我記得好像是馬爾克斯(Márquez)還是誰,厚顏無恥地說過,他希望以后能住在妓院里面,晚上喝酒和女人玩耍,白天很安靜就可以坐下來寫作。這種話的男性意味其實就很強了,因為貞操這個東西只屬于女性,男人是沒有貞操的,男人只有風流,他這樣說的話,大家都覺得,這個作家還蠻放浪形骸,或者說有名士風度對吧?但是一個女性不能說我想住在這樣的場所,她會被千夫所指,蕩婦羞辱就會出現在這種地方。
另外有一個法國的女性理論家其實非常重要,她的名字叫愛蓮·西蘇(Hélène Cixous),她提出了“陰性寫作”。她認為,“陰性寫作”跟“陽性寫作”是不一樣的:“陽性寫作”很多都是分析性的,或者是由理性驅動、具有概括性的;而“陰性寫作”使用白色的墨水,它更多是一種散播的、聯想的、由情感驅動的書寫,以認同為主,而不是突出批判的姿態。對應這種所謂的“陰性寫作”、“陰性閱讀”、“陽性閱讀”等等,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愛蓮·西蘇她認為陰性寫作不一定就是女作家才能寫的,有些女作家其實也能寫很很陽剛的東西,反過來有些男作家也可以進行真正的陰性寫作。她舉的一個例子就是詹姆斯·喬伊斯。喬伊斯被拉斯看作是不懂女性的,但實際上我覺得在《都柏林人》(Dubliners)的一些篇目里,比如《伊芙琳》(Eveline)、《姐妹們》(The Sisters)等,喬伊斯其實非常細膩地刻畫了女性的主體狀態。

電影《時時刻刻》劇照
所以我固執地認為,真正好的作家,都應該具有雌雄同體的特質。亨利·詹姆斯、科爾姆·托賓,他們本身的性向也不是那種“直男”的形象,大家懂我的意思嗎?酷兒理論家塞吉維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在《叢林猛獸》(The Beast in the Jungle)中讀出了一種“深柜”的恐懼,所以她終身未婚。科爾姆·托賓則已經出柜了。那你可以想象一下,這樣的同性戀作家,他本身天然就身處于一個性別的中間地帶,他并不是絕對的女性,但他也不具有絕對的男性思維,他可能比較容易進入愛蓮·西蘇所說的“陰性寫作”的感覺。所以我認為大家可以多關注我說的這些LGBT作家。《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續寫,叫《時時刻刻》(The Hours),《時時刻刻》后來又拍成了電影,原著得到普利策獎。有一次我在美國時還專門參加了一個作家的讀書會,邁克爾·坎寧安(Michael Cunningham),他是一個男作家,但他同時是一個出柜的同志,這樣一種形象讓他能夠在酷兒的文本當中游刃有余。正是因為他的這種居間性,有時候寫出來的東西可能顯得比女性更懂女性,比男性更懂男性。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非常值得關注的作家群體。我其實蠻反對二元對立的——把一些作品圈出來,這是最有女人味的,這是最真實的女人的東西,你要選擇站隊——我認為女性氣質也好,男性氣質也好,都是在一個流動的過程中的,是不斷被建構的過程,它所謂的本真性,實際上大有疑問,所以我們應該以一種更加包容、開放的心態來看待“陰性寫作”和“陽性寫作”的可能性。
劉慧寧:我也非常認同徐蕾老師說到的石黑一雄。寫女性很像女性。我最近讀了他的新作《克拉拉與太陽》,就特別關注到這個問題:它是以克拉拉這樣一個女性機器人陪護的視角來敘事的,購買者是看重克拉拉的聰明、敏銳、體貼所以購買了她,整體的敘述感覺非常自然、溫柔、敏感;不是說敏感才像女人,而是說克拉拉的想法和動機符合她的社會身份,因為克拉拉是一個陪護機器人,具有正常的思維能力。這就不像其他一些能力欠缺的作家,寫的女性人物不符合她的社會身份邏輯。
我還聯想一下,我知道石黑一雄是天蝎座,也許這個星座會有更多的共情特質。剛剛老師們也說到同理心這方面,而我最近了解到神經科學的一些解釋,就是同理心跟催產素有關系:如果一個人體內的催產素水平很高的話,那她就會是比較有同理心的人。而關于男女的大腦是否天生具有較大差異的問題,這也是現在神經科學界在爭論的,有一部分女性科學家就致力于證明,女性的大腦和男性的大腦其實區別沒有那么大,一個可供證明的事實就是我們的大腦是在不斷發展的,尤其是從嬰兒到青少年這段時期,外界的影響是在參與大腦的塑形的。
下一個問題是:女性文學逐漸成了出版界的一個賣點,但有的評論認為部分打著女性文學旗號的作品實則水平不佳。不知兩位老師怎么看待這個觀點?這可能還涉及到另一個問題,我們該如何去評判作品的水平?拉斯也在書中提到抑止女性寫作的一個方面,就是以男性為主導的評價標準。我們該如何突破這樣的標準去評判作品?以及突破之后就真的可以得到一個男女公認的標準嗎?
徐蕾:就國內的出版業而言,水平當然是參差不齊的,在這里我也就不展開說了。但是這個標準的問題還挺有意思的,因為來之前我也簡單搜索了一下英語文學界比較有分量的文學獎項,它們最近幾年頒布的情況。在英語文學界、英聯邦國家這個文化圈里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學獎,就是布克文學獎,它從1968年設立以來已經有很多年的歷史了。布克獎歷史上的獲得者幾乎都是大家公認的英語文壇的大家。簡單統計下來,一共接近六十幾屆了,但女性獲得者只有21個,不是很多,但是這個比例在近10年,也就是2010年開始到2020年,發生了很大變化,基本上是一半一半了,這個比例提升還是挺快的。去年是蘇格蘭籍的男作家,2019年的話是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和伯娜丁·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一個族裔背景的女作家,在英國出生的尼日利亞裔作家,這也是布克文學獎歷史上第一次同時兩個作家獲獎,之前也有過但其中一個作家會拿全額獎金,另外一個作家只有名沒有獎。但2019年出現的是雙花,兩個人平分了獎金。所以至少從文學獎來看,對女性文學的偏向越來越強了。
而且在英語文學界還有一個專門的女性文學獎“The Orange Prize for Women's Fiction”,曾經叫橘子獎。這個橘子獎設立之后,也有蠻多人表示懷疑,因為這個獎項既是對女性文學的一種推進,但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存在偏見,“為什么沒有男性文學獎,非要立一個女性文學獎?”不管這個文學獎的標準能不能在業內得到認可,但毋庸置疑的是,這個獎項所認可的當代女作家,比如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薩拉·沃特斯(Sarah Waters),都是英國文壇的新銳女作家,那顯然這個獎項起到了推波助瀾、引領文學品味取向的作用。至于標準是不是能夠達到一致,我覺得恐怕很難。
我還想再舉一個例子:也是英國文壇挺有分量的一個獎,叫科斯塔文學獎,它分五個序列,包括小說獎、處女作獎、傳記獎、想象文學獎和兒童文學獎。2013年的時候,五個獎項的所有提名人全是女性,當時英國文壇一片嘩然,就好像是說英國文壇難道已經是女性成為絕對的主導了嗎?大家示質疑。那一年所有的獎項無疑都頒給了女性作家。

扎迪·史密斯
所以我是感覺到,現在的這個文學市場非常偏向女性作家、女性讀者,而且很大程度上也被女性讀者的趣味所影響。至少在英語文學界,我們看到布克獎非常青睞那些來自跨文化背景的女作家:一方面,她們的文學作品的確有獨特的敘事方法;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能不承認,她們確實代表了整體的審美趣味越來越向女性傾斜。
總體來講,我對于女性文學在21世紀的發展是持非常樂觀的態度的。不僅如此,就我自己指導的研究生的論文,寫女性作家的應該占絕大多數,這個跟我們的研究者絕大多數都是女性也有關,我們研究生的隊伍顯然是女性占了四分之三。女性的學習者,就像慧寧所說的,可能會對女作家的作品更容易產生認同感,這也是為什么女性作品受眾越來越廣,然后在文壇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大多數是女性,因為天然的原因,會對女性作家的作品更容易產生共情感。其實很多男同學也是,我今年指導的一個男性碩士研究生,他寫的是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前幾年有男同學寫薩拉·沃特斯,還有男生寫的石黑一雄,剛柔兼濟的一個男性作家。所以現在我感覺那種純陽的男作家——海明威,福克納,反正至少在我指導的學生當中,研究他們的比較少。大家還是喜歡那種給人一種認同感、慰藉感的文字作品,而不是讓你去產生“必須要去戰斗”這種比較有陽剛色彩的作品。這是我的一點小小的看法。
但漢松:我贊同徐蕾老師的觀點,講到男女平權這個問題,文學這個圈子是最近300年做得最好的。你可以比較一下:比如說在科學的圈子,在飛行員、海軍或哲學家的圈子,還有藝術界畫家、建筑家的圈子里,男女比例是畸形的,絕大多數人都是男性。只有在小說家領域,女作家才占有非常大的比例。這其實有一個歷史原因:從一開始女性讀者就是閱讀的主體,因為女性有閑暇的時間。當社會出現了公域和私域的區分,女性在家里持家,做天使的同時照顧孩子,但是她有閑暇時間,可以去閱讀。奧斯丁開始寫作的時代被認為是一個女性作家頻出的時代,女性作家進入寫作對她們來說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而且是她們為數不多的幾個選擇之一。你想象一下,在18、19世紀,像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這樣的女人,寫信要一張郵票都沒有錢去買,需要爸爸給她錢,因為女人不可以賺錢,女人沒有經濟權,女人不可以去簽合約,女人不可以去借債,女人沒有繼承權。老公死了以后,這一切的家產都要給兒子。那寡婦怎么辦?寡婦要搬出去,要搬到另外一個房子,如果這個兒子對你很好,他可能在旁邊再給你買個小房子,寡婦就住那兒;如果他對你不好,你可能就掃地出門了。包括你跟你丈夫共同購置的家具、床這些東西,都歸你兒子,不歸你所有。在那個時代,女性為平權奮斗意味著面臨很多東西,包括穿褲子的自由、簽合同的自由、騎自行車的自由、騎馬的自由等,要去爭取它們都是很艱難的——但唯獨寫作這件事情,因為它很私密,你不需要進入一個行會體系里面,找一個師傅,經歷漫長的學徒期;你只要有一個自己的房間,稍微有點錢,比如說冬天寫作太冷了,還要點燈、點蠟燭,那么窮人家的女性可能都沒有這樣奢侈的條件。大量中產的女性開始投入小說、文學的創作中,她們已經構成了那個時代的文學里相當大的一部分。以至于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說我要以小說為業的時候,大家都在鄙視他,因為那個時候小說家是一項過度女性化的職業,因為都是女人在寫,你一個大老爺們,你畢業了,你不當律師,你不當政府公務員,干嘛要去寫作、寫一些哭哭啼啼的東西呢?所以在文學創作中,我一直認為女性的聲音從來都沒有缺席,它是非常強大的一股存在。當然了,在學院派或者是正典化的過程當中,如何將一些女作家排除在外,如何把少數遴選為正典,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那么這個問題可能還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涉及政治正確的問題。現在有這么多女性開始去寫作,這么多的女性讀者也關注這種細節問題,我們該評價好還是不好?這個我跟徐老師一樣還是有一點點擔心的,因為文學獎其實是現在作家能夠脫穎而出的最重要的模塊,大家都寫作,憑什么你出的書就可以上榜?比如豆瓣上有大量的女文青天天都在寫短篇小說,但是無人問津,可是為什么有一些女作家一下子成了明星?那這里有資本的運作在里面,什么樣的作家能夠得到這樣的文化資格,能夠成為年度推薦的新銳女作家,能夠獲得橘子獎、普利策獎?在這樣的過程中,因為女性平臺運動的發展,一些政治正確的因素就已經潛移默化地在其中運作了。大家會覺得,如果一個獎不給足夠多的女性或者是年輕的女性,尤其是少數族裔的女性,那么這個獎本身的公信力就會有問題,評委的道德感就會是值得指摘的。很多文學獎項,尤其是布克獎體現得尤其明顯,他們會故意找一些“老白男”大作家去陪跑,然后找之前只有一部作品的年輕新銳女作家入圍,我一看這樣的提名名單,我都不用想,肯定是年輕作家勝出了,老作家就是來陪跑的。她在比賽中干掉了“老白男”作家,于是就一下子躍升成為一個文化偶像。我的看法是:有時候過度的政治正確,的確會妨礙我們的文學審美。現在美國流行一個文化叫“廢棄文化”(cancel culture),比如說菲利普·羅斯去世以后,很多人就說羅斯生活不檢點。說他找一些女學生或女記者去他家,嘲笑她們讀的書,或者把她的錢包扔到垃圾堆里,說“我給你買個新的”,等等。還有塞林格(J.D. Salinger)也在年輕時的女情人的回憶錄里受到了批評,說他非常大男子主義等等。但我們不能夠因為我們在老作家身上發現了一些不利于女性平權事業的東西,就把這名作家廢掉,從我們的書單上挪掉,“羅斯對女性這么不友好,他的書就一定是垃圾”,這樣的一種導向現在還蠻突出的,不斷在文學上“弒父”,不斷去將一些有重要性的作家挪出我們的文化中心地帶,只是因為性別標準的這樣一個排他性,最后其實是我們的損失。因為我們就越來越立場先行,越來越標簽化地閱讀,那么我們的閱讀趣味就不自覺地就受到了一種性別文化的塑造,我們被告知讀這樣的女作家是進步的,那么我們有時就放棄了對審美的要求,或者是另外一種思考的能力。所以這是我的一點不合時宜的擔心。
劉慧寧:關于政治正確,徐老師還有什么想說的?
徐蕾:我剛才聽了但老師講的這個“廢棄文化”,在我看來它可能是最近幾年進入我們的語匯中的,但其實它的出現可以一直回溯到70年代。凱特·米利特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把D.H.勞倫斯(D.H. Lawrence)這樣的男作家批得一塌糊涂,說他是“phallocentrism的代表”,因為里面的女性人物無一例外對男性的陽剛之氣充滿了崇拜。事實的確是這樣,從她所節選的勞倫斯作品片段來看,勞倫斯至少是跟女性站在對立面的一個作家。但是我們能夠因為他有這種所謂的男權中心主義的思想,就把他從文學史上一筆勾銷嗎?這么做有點矯枉過正。勞倫斯作品啟發的性解放意識及其對兩性的洞識在他那個年代恐怕是獨有的一座巔峰。你不能因為米利特在1970年代的這么一本書——這本書也成為女性主義第二次浪潮中號角式的作品——就把勞倫斯打入另冊。結果也很明顯,勞倫斯在今天依然被我們研讀,雖然我們評判他的目光會帶著一絲絲懷疑和謹慎,但是謹慎之外還是有敬意的。
劉慧寧:最后一個問題是比較個人化的問題:奧斯丁是英語文學史上獨一無二、怎么都繞不開的名字,也是許多女生愛上英語文學的起點。我從小到大看到的對奧斯丁的評論都包含“雖然……但是格局小,只寫閨房瑣事”這樣的句式。我在學生年代時并未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缺憾,因為對我來說奧斯丁最妙的部分是她的反諷,她的小說讀起來很有趣,但并未覺察到這個評論不恰當的地方;等讀完拉斯的書,我才清楚認識到那些評論本來就是站不住腳的、男性話語的,“如果以維多利亞時期男性的閱歷為標準,維多利亞時期女性的閱歷確實是狹窄的,但如果以那時的女性閱歷為標準,則男性的閱歷也同樣狹窄。”其實我們常常忘記在那個年代,權利有限的女性人口也占一半呀。最近我又稍微翻了翻奧斯丁的小說,這一次我看到的是無法繼承房產、無法工作的女性在那個年代努力生存的堅韌頑強,這當中包含著巨大的生存智慧——比如《理智與情感》一開頭便是女主角一家因父親離世被迫搬離原有居所,尋找便宜的住所——以及在這種嚴酷中仍然懷有的人情。兩位老師對奧斯丁持有怎樣的觀點和情感?剛剛但老師也提到了,說覺得奧斯丁是最偉大的作家。
徐蕾:奧斯丁毫無疑問是最偉大的作家,不但是女性文學傳統中的第一個豐碑式的人物,而且即便是在“老白男”國際批評家布魯姆(Harold Bloom)看來,在文學正典中奧斯丁也是有一席之位的。你剛剛問在男女之間是否存在閱讀標準漸趨一致的傾向,我覺得至少在奧斯丁身上,我們看到不管男性批評家還是女權傳統,都認為奧斯丁的作品是一座豐碑。而關于私人情懷,她的《傲慢與偏見》是在座每一位文學愛好者接觸英國文學的入門之作,這部小說符合很多年輕女性對浪漫愛情的一種憧憬;這個是毫無疑問的,我們都喜歡大團圓的結局,小說里的男女主人公經過各種誤解,最終能夠破除諸多觀念的、身份背景的、家庭的阻礙或隔閡,最后攜手成就了彼此圓滿的人生。《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顯然滿足了我們這種閱讀期待。《理智與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則教會了我們:找到真正心心相印、習性相仿的人,才是婚姻穩定的真理。《曼斯菲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告訴我們,要守得云開見日出,咬定青山不放松,你鐘情的那個人最終一定會鐘情于你。
奧斯丁的小說之所以打動人,首先是因為它講的是愛情和婚姻,我們最初被這個話題吸引,但是仔細去看就會發現,這種愛情往往并不是簡單的男女相吸,里面其實包含著巨大的市場化的、商業化的婚姻價值觀,這個價值觀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格蘭,是非常重要的話語體系,所以才會有了《傲慢與偏見》里第一句、也是最著名的話,“凡是有錢的單身漢必須要有一個老婆”,這句話在《曼斯菲爾德莊園》變成了“可是天底下有錢的單身漢必然沒有漂亮的待字閨中的女性那么多”。奧斯丁一方面在講愛情,但另一方面又在告訴我們愛情離不開現實的基礎,并且很多時候受到現實的裹挾。
但漢松:我為什么喜歡簡·奧斯丁呢?從女權政治上來講,奧斯丁絕不是最正確的,在很多地方上她甚至是落后的、保守的,比如愛瑪那種門當戶對的觀念,在英國鄉村的共同體里,你想有穩定的婚姻家庭,你必須有同樣的三觀、收入才般配。她的故事絕對不可能寫女主人公私奔到法國巴黎得到了真愛,或者是艾瑪這樣一個在宇宙中心的女人,毅然決然、不顧一切世俗偏見,勇敢愛上了農夫;小說主人公還是找了一個年紀差不多的男人,比她大一點,又懂她又溫柔,并且一定還是個多金男。這是一個相當落后的婚姻戀愛觀。可是為什么我們還是喜歡奧斯丁?原因很簡單,不是因為她寫少男少女的戀愛,而是因為她的語言太好了:比如《愛瑪》里的心理活動,那種急躁的個性,她意識到自己錯了以后,那種懊惱的情緒不斷推進。有閱讀能力的話,一定要去看英文的原著,看了就知道她真是出道即王者,她的語言能力、制造包袱的技巧、自然而然的幽默感、把每一個人說話的樣子寫得活靈活現的筆觸,這些能力真的就是天助之才。我以前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節目,就是辯論《愛瑪》和《呼嘯山莊》哪個是更好的英國小說,雙方各出一個代表打擂臺,一人讀一段書,最后投誰是文學之王,結果《愛瑪》勝出。

電影《愛瑪》劇照(2020)
所以文學的價值最終還是要回到文學本身。美國杜克大學有一個文學評論家叫倫特里奇亞,他特別反感用性別、政治階級來劃分文學作品的做法。他在教研究生課的時候就特別懊惱:他讓研究生去讀惠特曼,他們說不讀,因為惠特曼有種族主義思想;讓他們讀康拉德,不行,康拉德也有種族主義思想;讓他們去讀艾略特,不行,艾略特有厭女癥。然后倫特里奇亞就非常憤怒,他說,對,艾略特是有厭女癥,你是沒有厭女癥,可是你能寫得像惠特曼和艾略特這樣好嗎?你除了有政治立場還有什么?所以文學還是要回到文字、審美,回到它本身的東西。每次我讀奧斯丁的作品,我都不會把它們理解成愛情操作手冊,小說的婚姻觀完全不妨礙我去欣賞它的技巧、它的幽默才智。
順便我還要講一句,后殖民批評對奧斯丁是有很多傷害的。我在講西方文論課的時候也給學生說過這個問題。隨著現在所謂的身份政治、差異政治的發展,愛德華·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當中就率先向《曼斯菲爾德莊園》發難:他說這些故事美固美矣,語言很好,可是未免也太歲月靜好了吧?憑什么少男少女在這樣的莊園里面,在鄉間別墅里每天能夠想的事情就只是如何能夠把達西當作自己的舞伴,或者他有2萬的年薪?憑什么你們每天就是在想穿什么衣服去舞會,給誰寫信,誰來求婚,你要跟誰私奔,你為什么每天想的都是這樣的事情?你們難道不想一想在遙遠的西印度群島有許多甘蔗園,這些甘蔗園里有多少黑人奴隸在為英國的老爺少女們去賣命,因為沒有他們的負重前行,哪有你們的歲月靜好?所以薩義德作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指控,說奧斯丁這樣的國寶級作家,故意或無意地對帝國主義問題避而不談,她不談宏大政治,也不談法國大革命,哪怕這些是她同時代的大事件;相反,她只談鄉間的歲月,只談少男少女的情緒。這些事件的缺席,在薩義德看來,是因為跟帝國主義達成共謀,只有英帝國是穩定的,這樣的鄉間文學、生活的風格和交流的方式才能夠延續下去,所以你們的平靜生活,這種鄉村田園詩般的東西其實是以別人的血汗為代價的——這樣一種后殖民的解讀一石激起千層浪,很多代表少數族裔的文學批評自然會給奧斯丁打低分,指責她沒有去關注一個更大的歷史。
除了文學自身的價值之外,我還想提醒大家注意一點就是,很多時候一個東西是否重要,其實取決于我們的價值觀:憑什么認為去反映法國和德國的戰爭,或者是像托爾斯泰去寫拿破侖的入侵這類宏大的事件,就一定比探討一個閨閣中的女性的心路歷程更重要?為什么拿破侖的失敗這件事情,一定就比一個女性為什么在今天會不開心這件事情、或者什么叫女性這個事情更重要?這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天然的尺度,我們將宏大的政治,將所謂的現代性的歷史、政治進步定性為重要的東西,那相應地,我們就貶低了女性的情感、意識和思維,以及女性的其他很多東西。這個當然是有問題的,他直接就追溯到一種對現代性的性別化的解讀。有一本書叫《現代性的性別》,是我參與翻譯的,我覺得這本書其實很多地方就在討論這樣一個問題:所謂的現代性其實是男人的現代性,所謂的現代性、成為一個現代的人,其實就是成為一個現代的男人,他們要到外面的世界去,去侵略、去遠征、去航海、去征服,而女人在家里做的事情自然就是無意義的。所以這又讓我想起了格萊斯佩爾(Susan Glaspell)寫的那個 《瑣事》(Trifles),里面寫到女性的直覺和觀察,包括怎么樣去清理房間,怎么樣縫被子,針腳是什么樣子的,這些在男人看來不值一提的女人氣的事情,其中恰恰隱藏著巨大的秘密,隱藏著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認為價值體系這個東西其實是被社會建構出來的,我并不認為在奧斯丁的小說里面只談論鄉間,就不像談論拿破侖的戰爭一樣重要,它的重要性不會因此減弱。
劉慧寧:我補充一點奧斯丁的婚姻觀。我讀了她的傳記后,特別能理解這樣的心態,因為她家有非常多的孩子,一共八個,她自己沒錢,需要靠爸爸給錢,一生中大部分歲月都靠寫作謀生,但還是沒有賺到錢,甚至還搭出去一點錢,她自己一直和姐姐睡一個房間。所以這是一種非常缺乏自由的狀態,中間大概有10年沒有產出任何作品,因為不得不聽命家長搬家了,搬到巴斯等地,結果又打亂了她寫作的狀態。所以我對奧斯丁的婚姻觀的理解就是,她需要錢去感受到一種穩定感、自由感和安全感。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