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今天這個世界上,還有幾個真東西?
原創 吳琦 單讀
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活在一個透明的世界里——每個人都可以發布信息,然后被所有人看到。表面上看,我們就在技術許諾的“烏托邦”里,人們平等地收發信息,沒人可以再欺瞞誰。但事情并沒有這樣發展,屏幕里仿佛有一個漩渦,最后我們都圍著幾經轉發評論的信息繞圈圈,真相到底是什么,無從知曉,甚至也無人關心,越來越多人只想活在想象的泡沫里。
吳琦為《單讀 26· 全球真實故事集》撰寫的卷首語《真東西》,題目取自亨利·詹姆斯的一篇小說,而他想表達的,也與亨利·詹姆斯的文學觀有相通之處。小說不能脫離“真東西”,電影也是,非虛構寫作便更是如此,但是從 19 世紀到 21 世紀,“所有的形式都在僭越真實”。這正是考驗創作者的時候,在今天,“只有靠近現場,與陌生人交談,觸摸皮膚、物體或海洋的表面,才能使我們免于心虛。”

真東西(The Real Thing)
撰文:吳琦
之前在網上請大家一起選新播客的名字,我臨時加的一個選項被留言吐槽說不知所云。心里一驚,有種想出個謎語但謎面出錯了的失落感。那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一個短篇小說的名字,也是你正在讀的這篇文章的標題。大概兩年前和陳以侃提過一嘴,他當時沒有多說,但露出一個不用你說謎面就已經知道謎底的眼神。有些人的意見享受更高的權重,這么看也不算不公平。播客最后的名字還是來自亨利·詹姆斯,并且更明目張膽地抄襲了他的一個書名。《螺絲在擰緊》。因為年代久遠、版本紛繁,較難確認誰是最初的譯者,更早的譯本還翻譯成《布萊莊園的怪影》《碧廬冤孽》,想來都應該一一致謝。原創性不足,但表現力豐富——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好和陳思安聊天,我說這不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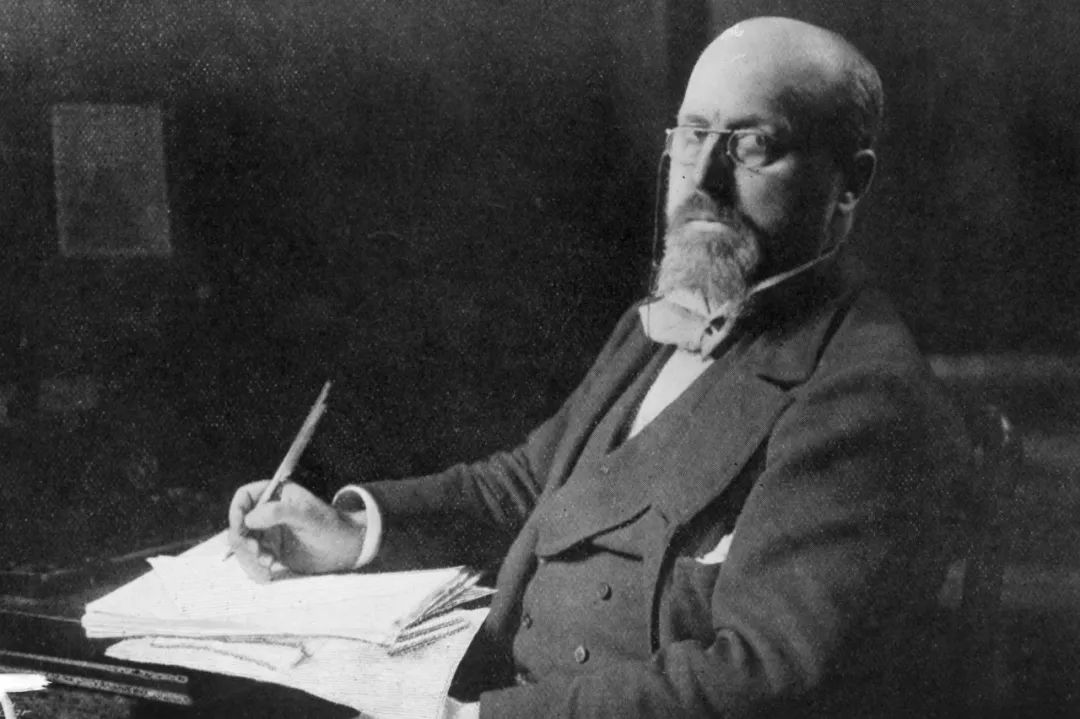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英國、美國小說家。
《真東西》這篇小說表面上是一個有點悲傷的故事。一對原本家境優渥的中年夫妻家道中落,不得不重新出來找工作,經朋友介紹找到一位插畫家,想給他當模特賺錢,他們怯弱但又自信地認為,自己良好的體態和舉止,理應離那些文學作品里假模假式的上等人更近。畫家明顯是個好心人,他的觀察和小說家一樣達到了細致而深刻的程度,很快發現了他們并不適合這份工作,卻主要出于同情留用了他們。他在小說里說,“我正確地判斷,在他們尷尬的處境中,他們密切的夫妻關系是他們主要的安慰,并且這個關系沒有任何弱點。這是一種真正的婚姻,這對躊躇不決的人們是一種鼓舞,對悲觀論者是一個棘手的難題”。這段短暫而幾乎有些溫情的合作關系最后還是走向破滅,畫家以這對夫妻為模特的作品迅速受到朋友的批評,也不被雇主認可,他們在畫面中的效果遠不如那些粗鄙、生動的勞動人民,于是他給了他們一筆錢,從此再也沒有見過。

這種忽然瞥見的沉淪和情誼,很容易打動我,更何況潛藏在故事背后還有一層關于藝術本體的討論。上海譯文出版社編的這本短篇集《黛茜·密勒》,還認真收錄了亨利·詹姆斯闡述他小說理念的那篇文章《小說的藝術》。兩篇都出自巫寧坤的譯筆,形成了美妙的互文關系。詹姆斯在里面談到,虛構小說如何必須反映真實事物,而又在哪些環節重塑了它,作家和畫家的工作在這方面很相似,他們的技藝就像是霧氣凝結成水珠那種轉換過程。這解釋了為什么那對擁有曼妙身姿的夫妻,未必就是最佳的模特,因為創造真實永遠不等于真實本身,而創作者們“對表現的東西較之真東西有一種固有的偏愛:真東西的缺點在于缺少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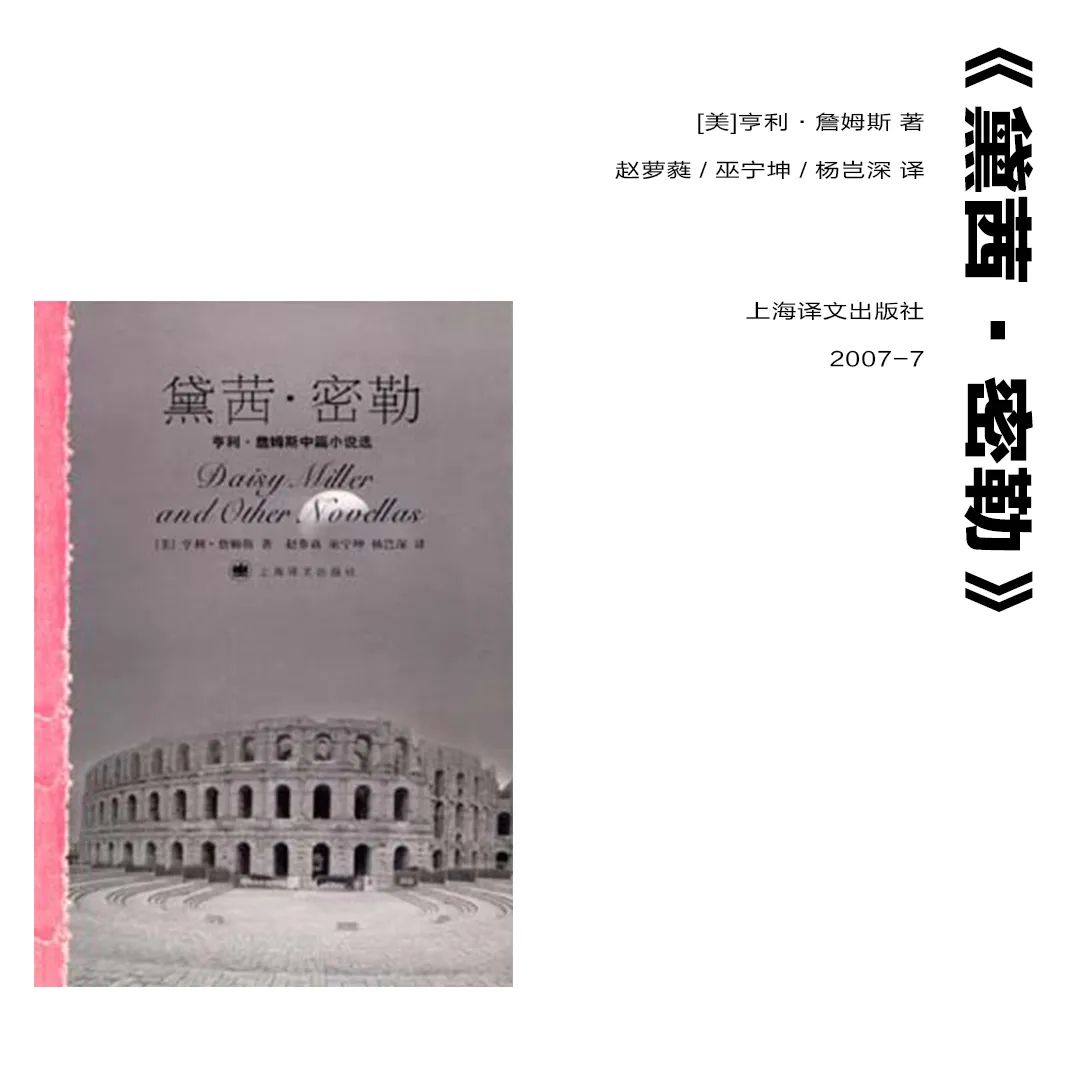
亨利·詹姆斯因為這一點而受到文學史的追認,身上被貼滿“現代小說”、“心理真實”、“意識流先驅”一類的標簽。他把小說最廣泛地定義為“一種個人的、直接的對生活的印象”。在后來人眼里,這的確是和印象派同等強度的叛逆宣言,他們是名副其實的同時代人。從那以后,創作者們獲得一次解放,大膽地把“印象”用作再現活動的基本單元。這讓我想到大學里曾經有一篇被自己斃掉的論文。那是在戴錦華老師的影片精讀課上,我試圖分析賈樟柯導演的《站臺》。我當時似乎是想說,作為年輕的觀眾我未必能夠全部理解賈樟柯鏡頭里的 80 年代青春,但通過那些影像和聲音的碎片,以及經由它們創造出來的情緒、氛圍和印象,也能構成歷史記憶。哪怕這種記憶的強度隨著代際更迭而減弱,也是不幸中的萬幸。最后我還是擔心這種論調是用懶惰的直覺掩蓋分析的短板,于是按照更加周正的邏輯,寫了一篇嚴絲合縫的論文交了上去。因為分數不高,我一直在想如果當時交的是第一篇作業結果會不會好一點。

電影《站臺》劇照
這個不斷碾碎人的心理空間的過程,符合自柏拉圖的“模仿論”以來藝術史發展的一般軌跡。然而這只是詹姆斯文學觀的一半。那篇《小說的藝術》實際上是想和貝桑爵士的一篇文章論戰,針對的恰恰是那種更追求形式感、藝術性的文學觀,因而不斷強調小說不能脫離“真東西”,就像畫家/作家始終沒有被那對夫婦激怒,而幾乎是饒有興致地摹寫他們。
“你不會寫出一部好小說,除非你具有真實感。”接下來我再引用詹姆斯的話,可能會有點篡改,因為這篇文章的初衷不是談論他,也不是談論文學。那不是我的專業。而在 “真實感”這種事情上,人人都有點發言權。如果說 19 世紀小說為“真”,20 世紀電影為“真”,那么到了 21 世紀,真實已經徹底丟棄了所有形式,或者說所有的形式都在僭越真實。用“后真相時代”來命名有點太過冷靜了,仿佛真相的后面還會有什么別的東西等待人類去逾越。在這個意義上,真實感具有末日的意味。而我急于為“真東西”辯護的一個動機,其實就來源于那樣一些落難的人不出意外是確乎存在的。留給創作者的問題不過是,你們是否能夠看見并且予以體會?小說如是,非虛構寫作就更不必提。
我一直記得 2019 年在瑞士參加真實故事獎的活動時,當地市民對中國故事的那種熱情,他們在小城里穿梭,在劇場、美術館和酒吧里等待聆聽記者們采集的故事。我感到自己遠道而來有天然的義務多講一些,可是在很多事情上,我們對實際上發生了什么的確一無所知,無從談起。詹姆斯把經驗解釋成“一種無邊無際的感受性,一種用最纖細的絲線織成的巨大蜘蛛網,懸掛在意識之室里面,抓住每一個從空中落到它織物里的微粒”。而今天整個世界, 都不斷在喪失獲得信息的渠道,以及被告知的權利,第二手、第三手甚至是虛假信息反而成了最成功的遮蔽物,我們也乖乖養成了一種欲言又止、聲東擊西的思維慣性。這時再做什么申明都顯得腐朽,只有靠近現場,與陌生人交談,觸摸皮膚、物體或海洋的表面,才能使我們免于心虛。在這種危急時刻,我們前所未有地需要粗糙的微粒、絲線和蛛網,作為認知的材料,而非藝術的目的。

因而寫作變得越來越困難。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我把之前看過和沒看過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說都翻了出來,摞在書桌上,它們顏色和開本各異,像一堆靜靜的嘛呢石,神圣而脆弱。雖然沒有大師全集那樣統一的莊嚴面貌,但它們的表現力也足夠承擔,人類在能力不足信心有余時所不得不借助的那類儀式、景觀和符號所發揮的效用。然而它們終究不能代替我的手敲擊鍵盤來打字,我們就是這樣不得不在新世紀和機器一起上路,尋回真實的感覺。一個戀人,一道甜品,一顆子彈。據說冷戰已經結束很久了。故事依然在朝最壞的那種情況發展,一個是假的,另一個還是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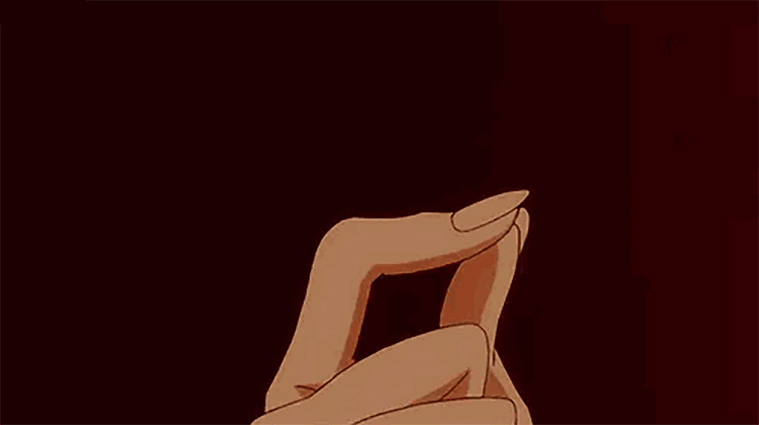
▼讀點“真東西”
原標題:《今天這個世界上,還有幾個真東西?》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